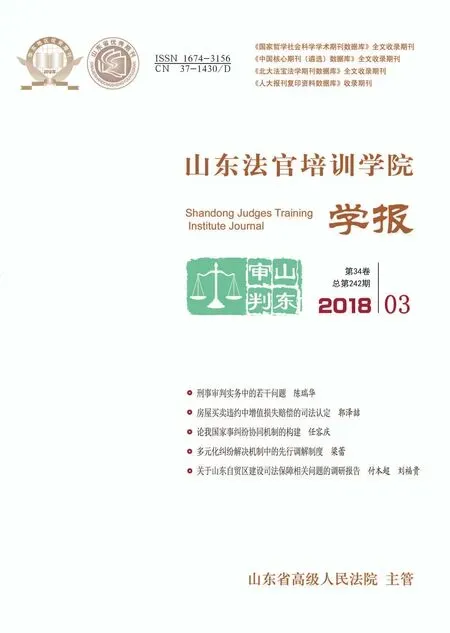棄權制度在保險合同糾紛案件中的適用
高勇 何宜曈
【關注焦點】
保險法中的棄權制度要求當投保方違反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保險人明知自身享有解除權及其他抗辯權,仍以明示或者默示方式放棄上述權利,此后便不可再主張其放棄的權利。由于棄權制度是用來對抗合同解除權和抗辯權,故其適用必須嚴格限定條件,認定保險人的行為構成棄權須具備以下要件:一、有依法成立并生效的保險合同;二、確實發生了保險事故;三、保險人知悉有違法或違約情況的發生;四、權利人已經通過意思表示自愿放棄了其權利;五、棄權的結果不能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或者社會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
被告:某保險公司
郭某在一審中訴稱:郭某所有的魯B069MX號轎車于2016年1月26日在某保險公司處投保機動車商業保險,保險期限自2016年1月28日0時起至2017年1月27日24時止,其中機動車損失保險限額為735392元,共計交納保險費19789.36元。2017年1月5日0時,郭某駕駛投保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與一輛順行的無牌工程車相撞。平度市公安局泰山路派出所作出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郭某對事故負全部責任。事故發生后,郭某向某保險公司報案,隨后,將車輛開至某保險公司指定汽修廠維修,并經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公司評估定損,損失金額為262000元。車輛維修以后,某保險公司拒賠。因此,郭某請求依法判令某保險公司賠償其車輛損失262000元,本案訴訟費由某保險公司承擔。
某保險公司辯稱:郭某在事故發生后,于2017年1月6日上午10點左右才報案,郭某未及時向交警及某保險公司報案,也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保護現場,擅自離開現場,導致交警及某保險公司均未對事故的第一現場進行勘驗和調查,郭某違反《道路安全交通法》第70條及保險合同的相關規定,導致某保險公司對事故的真實性無法查清,對事故發生時駕駛人的身份及駕駛人的駕駛狀態是否合法亦無法查清,因而無法查清事故的成因。因此,根據法律規定及合同約定,某保險公司不應當承擔保險賠償責任。根據《保險法》第22條及本案保險合同條款第15條,郭某未完成舉證責任,應當承擔不利后果。
【一審裁判】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16年1月28日,郭某將其所有的魯B069MX號轎車在某保險公司處投保機動車損失保險及不計免賠,并投保機動車損失保險無法找到第三方特約險,保險期限自2016年1月28日0時起至2017年1月27日24時止,其中機動車損失保險金額為735392元。2017年1月5日下午3時許,郭某電話報警稱,其于2017年1月5日0時許駕駛魯B069MX轎車沿廣州路由南往北行駛,當行駛至廣州路與三城路路口北時與順行在前的一輛無牌工程車相撞,致魯B069MX轎車損壞,工程車未察覺駛離現場。接警后,平度市公安局泰山路派出所民警對車損進行拍照,因無現場,事故責任無法認定。2017年1月6日上午10時許,郭某向某保險公司報案。某保險公司對魯B069MX號轎車作出定損報告,定損價值為262000元。后郭某向某保險公司申請理賠,某保險公司以郭某出險后駕車離開現場為由拒絕賠償。庭審中,某保險公司提交《機動車綜合商業保險條款》一份,其中機動車損失保險第8條規定:事故發生后,駕駛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被保險機動車或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離開事故現場,保險人不負責賠償。第10條第4項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知道保險事故發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及時通知,致使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難以確定的,保險人對無法確定的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同時某保險公司提交郭某簽名的投保單,投保單載明:本人確認收到條款及《機動車綜合商業保險免責事項說明書》,保險人已明確說明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的內容及法律后果。郭某質證時表示并未收到條款,投保單上的簽名也非郭某本人所簽,但某保險公司并未申請筆跡鑒定。
原審法院認為:郭某的車輛在某保險公司處投保機動車損失保險及不計免賠,原某保險公司之間的保險合同合法有效,雙方均應遵照執行保險法的規定和保險合同的約定。本案中,郭某自稱于2017年1月5日0時發生事故,但其未采取任何措施駕車離開現場,于1月5日15時始向公安機關報案、于1月7日10時向某保險公司報案,公安機關因無現場而無法認定事故責任。在此情況下,某保險公司應否賠償郭某的車輛損失?《保險法》第21條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險事故發生后,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及時通知,致使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難以確定的,保險人對無法確定的部分,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保險人通過其他途徑已經及時知道或者應當及時知道保險事故發生的除外。”第22條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按照保險合同請求保險人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時,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與確認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有關的證據和材料。”本案郭某在事故發生后沒有及時向公安部門及保險公司報案、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駕車離開現場,且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導致事故的性質、原因無法確定,根據《保險法》第21條、第22條的規定,某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郭某請求某保險公司賠償車輛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某保險公司的辯解意見成立,予以采納。
據此,原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之規定,判決:駁回郭某對某保險公司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公司的訴訟請求。
【二審裁判】
郭某不服一審判決上訴稱:郭某在事故發生后,因對方工程車未停車駛離現場,其駕駛車輛追趕,當時是霧天,又是深夜,沒有追趕上,為避免事故車輛再次受到撞擊而擴大損失,將車輛開到附近一家公司。事故發生后,郭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受理后進行了調查并拍攝照片,出具了事故證明。第二天,郭某又按照保險公司的要求撥打某保險公司的客服電話報案。后來,按某保險公司的要求,郭某將事故車輛運至該公司指定的濰坊一家修理廠維修,該公司出具了書面定損報告,并加蓋公章。后該公司以車輛未報警駛離事故現場為保險條款的免責事項為由拒絕賠付,并出具了書面拒賠通知。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某保險公司向郭某支付車輛損失費262000元;一、二審訴訟費用由某保險公司負擔。
二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相同。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某保險公司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問題。根據《保險法》第21條規定,本案中,事故發生后,郭某在有條件通知交警部門或者保險公司的情況下,未在第一時間通知交警部門對事故責任進行認定,亦未通知保險公司對事故現場進行勘驗,擅自離開事故現場,導致保險事故發生的性質、原因以及駕駛員的駕駛狀態均難以確定,無法判斷該事故是否為保險事故,郭某的上述行為存在重大過失,無法依據保險合同確定保險公司的保險責任,故對車輛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綜上所述,郭某的上訴請求不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據此,二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解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在保險人明知投保人未向其報案的情況下,仍對被保險的車輛進行定損和維修,事后又拒絕賠付的行為是否構成保險法中的棄權?本案中,保險人在得知被保險人未在第一時間向交警部門報案、也未向保險公司報險,導致無法確定保險事故是否發生的情況下,仍然對事故車輛進行定損,并要求車輛到保險公司指定的維修站進行維修,而在車輛維修完畢后保險人進行索賠時,又以保險合同的免責事由拒絕賠付。訴訟中,被保險人抗辯稱保險人在明知存在拒賠抗辯權的情況下,仍然通過對車輛進行定損并要求涉案車輛到指定地點進行維修的行為放棄拒賠抗辯權,之后再主張拒賠不應得到支持。被保險人的上述抗辯主張是否應被支持?本案是否可以引用保險法中的棄權制度?筆者認為,從立法層面而言,我國《保險法》第16條第3款雖對保險法中的棄權作出了明確規定,但該規定過于籠統,欲將保險法中的棄權制度靈活運用于案件審理中,須在了解棄權制度的理論基礎后分析出棄權制度的構成要件。
一、發現與探究:追溯棄權制度產生的理論基礎
保險法中棄權制度的產生源于對合同效力的認定。合同能否受到法律保護取決于合同的效力,大陸法系中合同的效力在于雙方當事人是否存在訂立合同的合意。而在早期英美法系中,合同的效力是通過雙方在簽訂合同時是否支付合理對價來判定的,無償合同、單方給付、勞務合同皆因其缺少對價而被認定為無效合同。然而,進入20世紀以來,絕對的契約自由被打破,對價理論表現出來的機械、教條、僵化、缺乏彈性等特點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易,對價理論的缺陷日益凸顯。英美法系國家的法院便首先創造了棄權制度。根據當時的棄權制度,存在合同關系時,只要一方有意識的通過放棄自己的權利修改合同,這種放棄行為即使不存在對價,其效力也被認可。棄權制度要求合同當事人一旦放棄了權利,就不能再依據該權利對相對人提出主張和抗辯。隨著棄權制度的不斷完善,為平衡各方當事人利益、保護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權益,英美法系中的保險法也產生了棄權制度,用于防止保險人濫用其合同解除權或者拒賠抗辯權。保險法中的棄權制度是指保險人知悉投保方違反保險法規定或者保險合同約定,及自身享有的解除權及其他抗辯權,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放棄此權利之后也不能主張其放棄的權利。
二、梳理與透析:厘清保險法中棄權制度的構成要件
由于棄權制度可對抗合同解除權和抗辯權的行使,隨意運用該制度不利于保險行業交易的穩定性,故其適用條件必須嚴格加以限定,保險法中的棄權制度的適用必須同時滿足以下要件:
(一)契約基礎:存在依法成立并生效的保險合同。保險合同關系成立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欺詐、錯誤、不實陳述等行為會導致保險人取得抗辯權,保險人可以因此解除保險合同或者拒絕承擔賠償責任。如果保險人自愿放棄上述權利則不能再行主張,棄權制度對抗的是基于保險合同關系衍生出來的抗辯權,所以必須以成立并生效的保險合同為契約基礎。
(二)客觀前提:保險事故客觀存在。保險賠償責任的承擔是以發生保險合同中約定的事由為客觀前提的,若保險事故并未發生,或雖然發生了事故,但并非保險合同中約定的保險責任范圍內的事故,則保險人無需承擔賠償責任,也不存在行使合同抗辯權和解除權的問題,棄權更是無從談起。
(三)主觀要件:保險人知悉有違約情況的發生。即保險人必須知悉投保方有違約情況的發生并意識到自身具有法律賦予或合同約定的某些權利。由于保險人是具有保險專業知識的組織,應對保險人的知悉程度作廣義理解,也就是說保險人只要按照通常注意便能夠知悉投保方違約行為,即可推定為保險人知悉投保方存在違約情形。如果保險人并不實際知悉投保方違反義務,但是有證據表明其如果對其所獲得的信息進行調查后便可知悉,則保險人則可被推定為知悉。
(四)意思表示:權利人已經通過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自愿放棄了其權利。由于棄權制度規定了棄權會對權利人造成權利不得再行使的不利后果,因此棄權的構成必須是權利人真實、自由的意思表示。明示,可以通過口頭或者書面的方式;默示,可以通過行為的方式。
(五)公序良俗:棄權的結果不能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如人身保險合同中,如投保人不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為無效合同,即使保險人又放棄合同無效所產生的利益的意思表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也不能取得該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利益。
本案中,某保險公司與郭某簽訂了保險合同,郭某向保險公司按期繳納保費,雙方之前存在依法成立并生效的保險合同。本案事故發生的第二日,郭某向某保險公司報案,保險公司對涉案車輛作出定損報告(此時涉案車輛并非在事故現場),郭某按照保險公司的要求將車輛送至其指定的修理廠進行維修,后郭某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時,該保險公司又以郭某出險后駕車離開現場為由拒絕賠付。結合上述要件進行分析,某保險公司在事故發生后第二日對車輛進行定損時,應當知悉定損車輛并非在事故發生現場,無法確定是否確實發生了保險事故,但仍對車輛進行定損并對車輛指定維修地點進行維修,某保險公司的該行為系明知被保險人有違約的情況發生,仍然以對車輛進行定損并對車輛指定維修地點進行維修,因定損和維修屬于理賠的前置程序,且會對被保險人會產生時間和金錢的成本,故此情形系保險人以默示的方式自愿放棄了拒賠權。從表面上看,保險人的上述行為貌似可以構成保險法中的棄權,某保險公司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然而,由于被保險人在事故發生后未第一時間通知交警部門對事故責任進行認定,亦未通知保險公司對事故現場進行勘驗,擅自離開事故現場,導致無法判斷該事故是否為保險事故,保險事故發生的性質、原因以及駕駛員的駕駛狀態均難以確定,且交警部門出具的事故認定書中明確載明“因無現場,事故無法認定”,因此被保險人無法舉證證明“確實發生了保險事故”,被保險人不能要求保險人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承擔賠償責任,法院亦無法認定保險人的行為構成棄權,保險人無須承擔賠償責任。
三、延伸與列舉:探討保險棄權制度的適用情形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保險中棄權制度設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合同解除權和抗辯權的肆意行使,其構成要件略顯苛刻。筆者將列舉部分符合保險法中棄權制度構成要件的情形,以便讀者在適用棄權制度時予以參考。
(一)投保人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時,若對保險人所提出的問題未做明確或全面回答,而保險人放棄進一步詢問即同意承保進而簽發保單的情況下,可以推定為保險人已經放棄了進一步詢問的權利。事后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人就不得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為由拒絕賠付。
(二)投保人在與保險人簽訂保險合同后,未在約定期間內支付保險費,足以達到保險人取消保險合同的條件后,保險人仍然接受投保人交付保費的行為視保險人放棄取消合同的權利,保險人事后不得以逾期交納保費為由解除合同。
(三)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明知自己享有拒絕賠付的抗辯權,但仍然向被保險人郵寄定損通知單并要求被保險人對定損通知單認定的損失數額予以核對或說明,因此增加了投保人在時間上和金錢上的負擔,可視為保險人已經放棄了拒付保險金的權利,事后不得在以此為由拒絕賠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