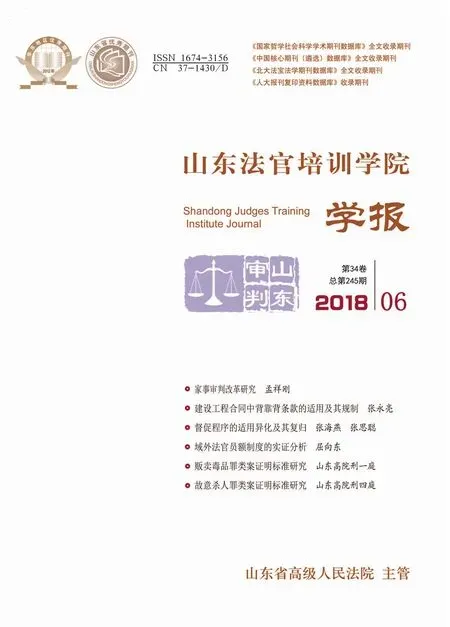民事判決對行政案件的既判力問題探析
——防止民行交叉案件裁判沖突的司法路徑
趙龍
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對同一事實或法律問題的認定存在一定程序的銜接和重合,從而導致民行交叉案件的產生。民行交叉案件為我國司法實踐提出了一系列難題,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民事判決作出后,當事人又提起行政訴訟,該行政訴訟是否受到已有民事判決的約束。對于這一問題,如何防止對同一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問題作出不一致的認定,就要尊重生效裁判的既判效力。①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改進行政審判工作的意見》第二十條。
一、問題的緣起:既判力的司法甄別
案例1:因城市規劃需要,2004年9月,費某居住的房屋被列入拆遷范圍,被拆遷人為費某、陸某(子)。后費某經別人介紹認識徐某,于2007年2月5日登記結婚。2007年4月17日,費某與房屋拆遷部門簽訂了拆遷安置協議書,并于2010年7月12日將拆遷所得安置房登記在陸某名下。2010年8月18日,徐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主張房屋共有權。法院經審理認定,房屋已實際交付,且已登記于陸某名下,遂判決駁回徐某的訴訟請求。后徐某又以房屋登記部門未盡審查責任,導致房屋登記錯誤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房屋登記。法院經審查認為,民事判決確認陸某對于房屋的所有權,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十項規定的不可訴的情形,遂裁定駁回起訴。②(2011)湖吳行初字第25號行政裁定書。
案例2:1998年11月,劉某向張某借款2230.80萬元,以某房地產公司所有的“建國大廈”作抵押擔保,辦理抵押登記,并約定抵押期限。2000年11月,張某以劉某未歸還借款為由提起訴訟,并要求對“建國大廈”享有優先受償權。庭審過程中,房地產公司提交了一份報紙公告,載明:“于1998年12月26日抵押給房地產公司的抵押物,因期限已到,予以注銷。”2002年5月,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房屋管理部門僅以雙方約定抵押期到期為由辦理抵押權注銷登記手續,法律依據不足,并不能免除房地產公司的擔保責任。一審判決之后,房地產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改判房地產公司不承擔責任。后省高院再審維持一審判決。由于“建國大廈”已被處置,2012年4月,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終結一審和再審民事判決的執行。張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附帶國家賠償訴訟,要求確認房屋登記部門對抵押登記行為進行注銷的行為違法,并賠償損失6800萬元。一審法院以本案超過起訴期限為由裁定駁回起訴后,張某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并未超過起訴期限,一審法院以超過起訴期限為由裁定駁回起訴,存在不當。但鑒于行政行為的效力已經由生效民事判決作出認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十項的規定,張某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賠償訴訟,遂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③(2012)浙湖行受終字第1號行政裁定書。
通過上述兩個案例,我們發現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何為生效裁判的羈束效力的認識并不統一,造成司法實踐的困惑。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行交叉案件大量出現,正如上述兩個案例涉及的房屋登記領域,為了解決因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的審查標準不統一而造成民事判決與行政判決產生沖突的問題,法院在不斷探索先民后行、先行后民,抑或行政附帶民事程序處理模式的同時,往往最先遇到民事判決對之后行政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是否產生羈束的問題。而對同一問題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不同做法,嚴重損害了司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二、既判力的適用范圍:適度擴張的審視
(一)“微觀”視域既判力之擴張
所謂既判力,是指生效裁判的羈束力,就其范圍而言,通說一般認為包括主觀、客觀、時間三個方面的內容。對于主觀范圍,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人或者對什么人發生法律效力的問題。④鄧輝輝:《既判力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頁。一般情況下,既判力主觀范圍限于當事人,不及于案外第三人。但在司法實踐中,為徹底解決糾紛,實現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對于當事人的適格問題,一般采取較為寬松的標準,以實現一次性解決糾紛的目的。⑤肖建華:《民事糾紛當事人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頁。由此,既判力的主觀范圍就不僅僅局限于直接參與案件的當事人,在一定條件下,既判力的效力可能擴張為案外第三人。對于時間范圍,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在庭審中予以固定的時間節點。對于該時間點,一般認為是事實審查口頭辯論終結時。⑥[日]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頁。此后出現的新事由,不再納入裁判的范圍。所謂客觀范圍,主要是指之前生效裁判產生遮斷或覆蓋糾紛之范圍,且該范圍內對于糾紛具有終局的作用。⑦林劍鋒:《民事判決既判力客觀范圍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頁。在訴訟過程中,尤其是民事案件,當事人訴爭焦點確定的重要依據就是訴訟標的。⑧段厚生:《民事訴訟標的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因此,訴訟標的在民事訴訟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不僅表現在確定既判力客觀范圍方面,并且也是確定是否存在重復訴訟等問題的重要依據。⑨前引⑥,第22頁。在民事訴訟中,賦予判決主文既判力效力,有條件賦予爭議焦點、裁判理由、事實認定以相對既判力效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后訴訟判決的不一致。
(二)“宏觀”視域既判力之擴張
如果說目前理論界對既判力的研究僅限于各訴訟領域內部,屬于“微觀”層面的話,那么對于交叉案件既判力的研究則屬于“宏觀”層面的探索。然而對于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簡稱行訴解釋)第69條第1款第九項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2018年2月8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廢止,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九項除了將“生效判決”修改為“生效裁判”及增加“調解書”的內容外,基本沿襲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十項的規定。既判力,是前生效判決對之后訴訟的拘束力,以保持前后兩個訴訟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保持統一的法律效力。既判力,其理論來源一般分為制度效力說、程序歸責說、雙重依據說和國家審判權說。主張制度效力說的觀點認為,既判力是基于保障權利安定而設置的,如果不存在既判力制度,生效判決可能隨時被推翻,不利于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穩定。[11]鄧輝輝:《行政裁判與民事判決既判力根據之比較》,載《河北法學》2007年第9期。主張程序歸責說的觀點認為,如果當事人在前訴中獲得程序保障,其就應主動接受之前判決的效力約束,而不能再就同一法律關系提出相同或不同的權利主張,即當事人在程序中享有權利與權益的保障是生效裁判的實質性要件。[12]前引⑥,第481頁。主張雙重根據說的觀點認為,制度性效力和程序保障是既判力產生拘束力得以正當化的條件。主張國家審判權說的觀點認為,法院作出判決依據的是國家的審判權,因此,既判力效力來源于國家審判權。[13]沈達明:《比較民事訴訟法初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訴權和審判權是訴訟的兩個基本因素,而判決的形成則是當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結果。既判力所要把握的就是在當事人權益保障和國家審判權力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但是,無論是制度效力說、程序歸責說,還是二元論的雙重根據說,均無法充分體現既判力制度的本質。相比較而言,國家審判權說更能體現既判力制度的本質。矛盾糾紛的化解,法院作為最終的裁判者,其判決具有權威性,正如國家審判權說所闡釋的理論,法院判決最終體現的是國家強制力,當然具有權威效力。[14]江偉:《中國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頁。因此,基于國家主權和國家司法權的威信,既判力作為訴訟法上的制度,對當事人和法院具有拘束力,而基于國家審判權的統一性,既判力的效力自然就擴張到交叉案件的適用領域。
三、行政行為對民事判決的拘束力:行政行為公定力理論的嵌入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我國構建的是以行政行為合法性和合理性為主要審查內容的行政訴訟體系,而根據《民事訴訟法》第3條的規定,民事訴訟解決的是當事人之間的人身權糾紛和財產權糾紛。基于此,民事判決能否對隨后的行政案件產生既判力的關鍵是民事判決能否在解決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基礎上對行政案件的訴訟標的進行判斷。關于這一問題,實務界和理論界爭議較大:一種觀點認為,行政行為的效力只能由行政訴訟作出認定,民事訴訟對于涉案的行政行為,只能從證據審查的角度予以認定,對于有效的行政行為,采納為有效證據,否則,不能將其作為后續裁判作出的依據。因此,行政行為只能作為證據予以審查,而不宜直接對其效力作出評斷,更不會產生直接認定或否定其效力的法律后果。第二種觀點認為,分開審理,或者合并審理,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解決不同類型的糾紛,因兩者具有一定的關聯,故應允許民事訴訟對行政行為的效力進行審查。[15]王達:《民事訴訟能否審查具體行政行為》,載《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05年第2輯。并且,對于具有重大明顯瑕疵的行為行為進行審查,尤其是在民事審判中,也符合經濟原則和公正原則。[16]蘇西剛、付文華:《民事訴訟中行政附屬問題探析》,載《行政法學研究》2000年第1期。傳統行政法學理論認為,行政行為具有公定力、拘束力、執行力,體現在不同的訴訟過程中則為民事訴訟原則上應承認行政行為的效力,但如果該行政行為存在無效或可撤銷的法定事由,民事訴訟可以直接作出認定。
上述觀點,各有其理論基礎,訴訟的不同分工對于類型化案件的處理具有重要意義,但因不同類型之間的糾紛存在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等特點,行政行為的效力成了不同訴訟程序,尤其是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之間不可回避的實踐難題。這主要基于行政行為的公定力理論,即行政行為,未經復議或訴訟程序撤銷或確認違法,即推定其具有合法有效的法律效力。[17]葉必豐:《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頁。行政行為的公定力理論,民事訴訟原則上要承認行政行為的效力,除非其存在無效或可撤銷的法定事由。[18]許宗力:《行政法對民、刑法的規范效應》,載葛克昌、林明鏘主編《行政法實務與理論》(一),臺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84頁。如果行政行為具有無效或可撤銷的法定事由,民事判決可以直接認定該行政行為無效或可撤銷;如果不具有上述事由,即使存在瑕疵,也不能直接對其效力作出否定性的認定。何種情況屬于行政行為可撤銷或無效?其主要判斷基礎為《行政訴訟法》第70條和第75條。
四、既判力在審判實踐中的具體運用:既判效力的司法界定
(一)訴訟標的的既判力問題
生效判決的主文具有既判力效力并無爭議,但民事判決主文的表現形式往往多種多樣,而有時僅僅從裁判主文本身又難以判斷案件爭議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判決駁回訴訟請求為例,單純駁回訴訟請求的裁判主文,無法識別案件的實體法律關系,因此,就必須結合當事人的訴訟標的。從一定程度上講,裁判主文的既判力,實際上體現的就是對于訴訟標的的判別。[19]耿寶建:《既判力理論的發展及在審判中的運用》,載《法律適用》2004年第2期。在民事訴訟中,對于訴訟標的的認定應結合訴的聲明進行判斷,所謂訴的聲明,就是指當事人請求法院予以支持的基礎法律關系。并且,訴的聲明與訴訟標的存在基本的對應關系。當涉及多個訴訟標的時,既判力效力僅及于生效判決確定的訴訟標的,未包括未作出判斷的訴訟標的。如果民事判決對訴訟標的已經作出實體判斷,而該標的又與行政訴訟的標的具有同一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69條第1款第九項的規定,當事人即使另案提起訴訟,法院也經裁定不予立案,已經立案的,應裁定駁回起訴。而對于訴訟標的同一性的判斷,關鍵是看生效民事判決確定的訴訟標的是否對行政行為的效力作出認定,如果作出認定,其效力當然及于后訴的行政案件,如果只是基于行政行為的拘束力對其確定的事實予以認定,則既判力不及于后訴的行政案件。
(二)爭議焦點的既判力問題
爭議焦點,系因雙方訴爭才會形成,在前訴已經作出評判的情形下,如果后訴予以否定,顯然就會危及當事人之間已經建立的相對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也會危及國家審判的權威。因此,對于爭議焦點的既判力應當予以確認。但爭議焦點畢竟不是裁判主文,對于其與裁判主文的效力認定應有所區別。按照日本學者新唐幸司教授的“爭點效理論”,[20][日]新唐幸司:《新民事訴訟法》,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頁。如果爭議焦點已經在訴訟過程中進行了充分的辯論,并且法院在裁判文書中對于爭議焦點進行了實質性的審理判斷,而不是一種推論,就應當承認其約束后訴的效力。后訴可以不經實體審查直接予以采信、認定,且不得作出相反判斷。需要強調的是,前訴的爭議焦點必須與判決主文緊密相聯,才能賦予其既判力。因為在同一訴訟標的下,可能產生多個爭議焦點,并不是每一個爭議焦點都直接影響判決結果,只有與判決主文緊密相聯,對裁判結果產生直接影響的爭議焦點才具有與裁判主文等同的效力。
(三)裁判理由的既判力問題
一直以來,對于裁判理由是否具有既判力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裁判理由不具有既判力;另一種觀點認為在特定情況下裁判理由具有既判力。從裁判的主文內容看,因司法實踐的需要一般較為簡短,因此,對于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判斷,有時需要結合裁判理由才能作出準確判斷。對于一個裁判而言,裁判理由無疑是其靈魂,如果裁判只是冷冰冰的結論,而沒有中間論證的過程,其透明度又有何體現。[21]沈達明:《比較民事訴訟法初論(下冊)》,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頁。而對于何種情形的裁判理由可以賦予既判力,筆者認為,按照請求權理論,可以將判決理由分為訴請型、要件型、輔助型。從羈束效力上而言,對于訴請型,其裁判理由當然具有既判力;對于要件型,一般認為其裁判理由具有約束力;對于輔助型,因其非構建法律關系的必要性,一般不具有約束力。[22]朱川、周晶:《判決理由既判力的再認識》,載《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第8期。訴請型裁判理由之所以賦予其既判力,主要基于其已經針對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作出了直接判斷,既經過了當事人雙方的充分質辯,也經過了法院的充分審理,法院在作出判斷的時候在證據標準上也已達到了蓋然性或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理當具有排除后訴的既判力。要件型裁判理由,由于請求權基礎的構成要件是訴訟請求成立與否的必要因素,并且,請求權基礎的構成要件成立與否也經過了當事人舉證、質證等過程,是在法律適用的基礎上對請求權構成要件成立與否作出的判斷,應具有約束后訴的效力。輔助型裁判理由,是指支持當事人訴訟請求而作出的判斷,由于輔助型的判斷并非請求權的必要構成要件,往往不宜賦予其約束力。
(四)裁判確認事實的既判力問題
作為生效裁判的重要內容,案件事實的認定與裁判理由和爭議焦點一樣需要進行既判力問題的判斷。法院對于案件事實的查明主要是基于當事人的陳述和舉證,因此,案件事實在一定程序上具有既判力。雖然行政訴訟法中沒有承認前訴確定的事實對后訴具有既判力,法院可以直接采信,但司法解釋對于生效裁判確定事實的既判力卻給予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70條規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或者仲裁機構裁判文書確認的事實,可以作為定案依據。但是如果發現裁判文書或者裁判文書認定的事實有重大問題的,應當中止訴訟,通過法定程序予以糾正后恢復訴訟。上述法條雖然就程序選擇作出規定,但何為“事實有重大問題”?或者,事實是否需要進行區分?上述司法解釋第70條的規定顯然規定過于籠統。如果對于次要事實、非決定性事實也要“中止訴訟”,顯然違背了既判力的本質。因此,應當對裁判認定的事實進行區分,對于決定性的事實,即直接影響案件裁判的事實,應當確認其既判力,而對于次要事實、對案件裁判結果沒有決定性影響的事實,則不應確認其既判力。即對于決定性事實,如果后訴的當事人有相反的證據,后訴應當中止,經過糾正程序后,再行作出裁判。對于次要事實、非決定性事實,即使前訴民事裁判認定錯誤也不會導致實體裁判錯誤的,在后訴行政案件的審理中,一旦前訴的事實被推翻,后訴要根據相關證據規則作出認定而不受前訴的約束。
在民行交叉案件審理模式的討論中,既判力作為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往往容易被人忽視,而法院在甄別生效判決是否具有既判力的過程中,因司法實踐中標準的不統一又產生較大差異,從而造成司法審判中“一個案件”數個判決的現象頻出,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司法權威。解決這一司法難題,需要進一步加強既判力理論研究,明確運用既判力的判斷標準,從而有效化解民行交叉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