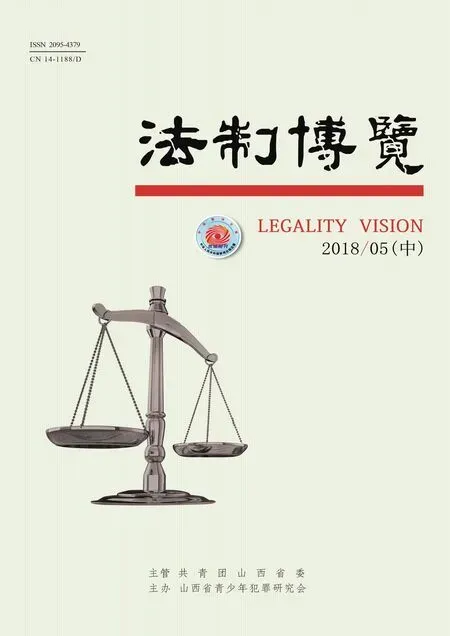論禮法結合對現代依法治國的啟示
王 勉
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一、禮法結合的基本內涵
(一)寓教于刑
“教”是教化,是社會道德教育,中國古代刑罰制度之中蘊含著的人道主義關懷自西周“慎罰”思想始,一直貫穿于中國數千年刑罰演變歷程之中。春秋時期,孔子強調的是“德行教化”,儒家仁愛思想融入刑罰之中,提倡以刑輔德,恤刑慎殺。南北朝時期的統治者吸收“禮治”思想,制定了更寬緩的刑罰規定,如“存留養親”等。到了唐朝則將前朝“慎罰”思想和制度融合,并于《唐律疏議》中集中體現自夏商以來最完善、最成熟的刑罰制度。宋以來“以嚴為本,寬仁濟之”的思想影響下,規定了“寬仁”的量刑原則,元明清各代對凌遲、斬刑做了各種限制,在這一原則的指引下,到了清朝笞刑也改用竹板來行刑。為政以德,寓教于刑,刑教合一共同實現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
(二)禮刑并用
依法為表,通過禮潛移默化的改造人們的精神世界,通過“禮”的仁政,德政的概念渲染法的公平合理,不僅可以減少法律推行的主力,更可以使法占據禮的制高點,增強法律的權威性。法律道德化,禮刑并用,不僅僅是為了阻止惡行,更為了勸導人們積極向善。禮法互補共同推動國家機器和諧有效的運轉是中華法系最鮮明的特征。三綱五常之說在漢武帝時期興起,成為維護社會道德倫理的禮和刑罰的立法原則。以儒家之禮義經典為核心的“春秋決獄”原則指引下統治者實行儒家理論治國,在戰亂頻繁的年代起到了穩定政治局面的重要作用。這些原則充分的將儒家思想和原本法家思想中的刑罰相結合,開啟了我國法律儒家化的進程,是為禮法結合的發端。經義,禮義,人情與法律的結合,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古代中央司法權的濫用。禮主刑輔,禮法互補,綜合為治,以禮為主導,以法為準繩,以法為表征,以禮為內涵。
二、禮法結合對現代依法治國的啟示
(一)春秋決獄原則對我國法官自由心裁權的啟示
享有自由心裁權的法官應有豐富的審案經驗。人類的經驗法則常是相當熟悉且提供知識的重要來源。經驗的傳承有其益處,而且以經驗作為預測也是人類行為的重要特質。經驗法則是其中的大前提,它是構成推理前提的重要部分。經驗法則源于人們日常積累,是經過大量案件之后保留下的經驗,這經驗代表一定范圍的群眾的共同認知,有一定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在自由心裁的時候形成制約,保證了自由心裁的合理性和客觀性。
審理案件時要強調行為的主觀方面,在春秋決獄原則的影響下,法官在行使自由心裁權時,應站在宏觀的角度,充分考慮個案公正和社會公正,要由法官靈活行使審判權,科學執行刑罰,要有理智科學的價值判斷,法官審查判斷證據,要與普通人的理性標準相符合,對證據所作判斷均須有正確性與科學性。首先要求法官進行的一切使用并將其轉化的證據以及這一過程全部依據論理法則進行,這是保證認知過程不會出現偏差的必要條件之一,才能防止自由心裁成為法官手里濫用權力的工具。所謂論理法則指以理論認識之方法,亦即邏輯分析方法。審查判斷事實真偽時,不得邏輯上推論或推理之論理法則。公信力是法官所做的裁判結果必備的特性,必須得到案件當事人和社會大眾的信服與理解。
(二)親親首匿原則對親屬間拒絕作證權的啟示
親屬拒絕作證權的使用范圍,應根據實際的社會狀況人文環境因地制宜的調整。首先親屬拒絕作證權適用主體應該明確。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以及同胞兄弟姐妹都屬于直系親屬,其拒絕作證權應該受到保護。除去適用主體,親屬之間的拒絕作證的證言范圍也應有所限制,秉承著平衡公共利益和家庭倫理關系的目的,只有不利于其親屬證人的證詞,才是應拒絕陳述。而有利于被告人的證言部分,則要根據證人與被告人的親疏遠近關系,考慮是否采信。另外,如果證人已經提供了關于被告人證言,就應合理接受對該證言的質證。這種情形下是不應該行使這種權利的。質證環節是對證人證言的真實性的重要評判方式,此前作證的行為就可以視為對親屬拒絕作證權利的放棄。而質證的回應是證人對已出示證言的負責的必要表現。
[ 參 考 文 獻 ]
[1]李露.中國傳統禮法文化視野下刑罰思想的歷史考察[J].河北法學,2012(10).
[2]李利.試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產生的基礎及所形成的特點[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