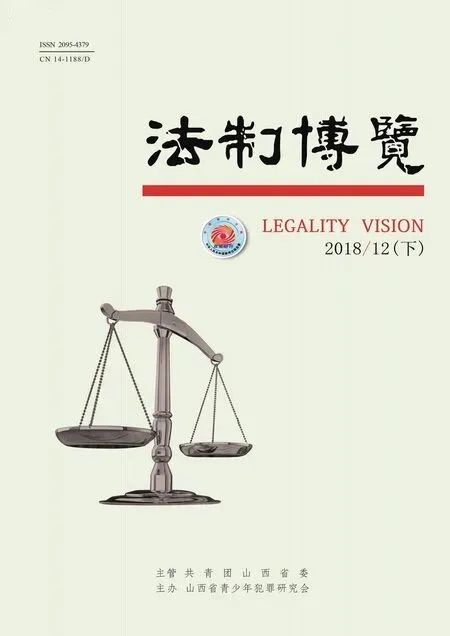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若干思考
董矚宏
內蒙古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內蒙古 通遼 028000
一、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先天缺失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在其“核恐怖理論”的支撐下,似乎是達成了東西方“各退一步式的和解”,實則是掉進了西方“歷史終結論”的陷阱。戈爾巴喬夫提出了營造“全歐共同大廈”的“藍圖”,其構筑是以抹殺意識形態的差別為前提的。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蘇聯開始遵循不同國家“由對抗走向合作”的原則。到1988年6月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戈爾巴喬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為止,蘇聯徹底地放棄了意識形態斗爭,放棄了馬克思主義。
“新思維”提出“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并一步一步從“人類利益高于一切”演化為“人權優先于主權”,最終使“新思維”理論在實踐中走入絕境。[1]這種超階級的國家觀只強調民族矛盾而完全無視階級矛盾,在美國和西方加緊了意識形態攻堅戰的同時,戈爾巴喬夫卻在努力淡化意識形態,不斷地敦促東歐國家加快改革步伐。對實行“民主改革”和“向西方開放”的國家給予支持和贊許,對“改革”不力或者對“改革”持反對態度的國家則進行譴責。
隨著戈爾巴喬夫“民主化、公開性”運動的深入開展,“新思維”否定國際領域存在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頂禮膜拜。其實,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共同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上,“和平演變”的觀點是一致的,布什政府為此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然而,戈爾巴喬夫放棄意識形態斗爭,徹底放棄了自己的輿論陣地,以為美蘇之間在“自由競爭觀念”下的和解就是實現了各讓一步的“中間路線”,其實這正是采用了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爭奪的焦點本來就是“社會歷史有發展必然性”和“社會需要通過自由競爭來達到永恒的真、善、美”誰對誰錯的問題!
二、馬克思主義擁有絕對的真理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不是革命的指令,而是革命道路的探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簡單的、教條化的運用只能讓馬克思主義哲學失去它本身蘊涵的真理性。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理論范式、思維方式,這就使得任何的革命指令都只有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相對意義,但人的思維本身就是形而上學的存在,追求真理的終極確定性是我們無法消解的哲學問題,這就使得我們總是習慣把相對的革命指令絕對化,從而對革命道路的探索產生阻礙,蘇聯式“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之處就在于此。
但是“物質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會因為“理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停滯而停滯,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內在于實踐之中的對現實的描述”,只要人類存在,這種“人”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現實”過程就會不斷向前發展,生存實踐先于理性,這是理性無法超越的一個前提,所以不管我們是否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世界,“物質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會在事物和感性互相激起的現實之中發揮作用,而當我們的主觀世界被“理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武裝起來之后,“理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成了我們改變世界的理論武器,反過來講我們同時也成為了“物質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改變世界的物質武器。
三、人類在當今世界面臨的諸多共同難題需要得到有效應對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30年代在西方國家出現的一種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思潮,它在經濟領域信奉自由放任原則,鼓吹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萬能論”,并且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在政治領域信奉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在意識形態領域信奉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人的“理性選擇”。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就“想象”出了一只看“不見的手”,新自由主義也同樣繼承了這樣一只“神秘的手”,但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出現證明這只手并不是什么萬能的“上帝之手”,這不過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客觀精神的異化”罷了。馬克思說:“謬誤在天國的申辯一經駁倒,它在人間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個人,如果想在天國的幻想的現實性中尋找一種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卻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尋找和應當尋找自己的真正現實性的地方,只去尋找自身的假象,尋找非人了。”[2]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民粹主義盛行,缺乏強有力的政府來應對集體挑戰,西方社會長期推崇的“利己主義”、“個人利益至上”、“個性獨立”已經越發和全人類的長遠利益相違背。人與人之間缺乏溝通,關系冷漠,人們都沉浸在網絡世界中,被資本奴役,被資本創造出的鋪天蓋地的廣告所吸引。與此同時,人類在當今世界面臨著諸多共同問題,但“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體的抽象自由”無疑使得很多如氣候變化問題這樣事關全人類生存發展的全局性問題沒有辦法得到有效應對。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新年賀詞中說:“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