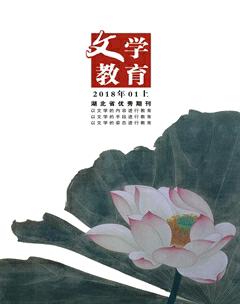評周李立的《蠶頭燕尾》
周李立在小說中所呈現(xiàn)的,正如她評價理查德·耶茨那樣,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小時代”以及“小時代”的痛苦。這種痛苦由于祛除了外部的戰(zhàn)爭、災難、變革,因此不再呈現(xiàn)為“苦難敘事”和“創(chuàng)傷敘事”,而是一種如蟻噬骨、如鯁在喉的小刺癢、小難過。它們不致命,無大礙,卻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提醒著生命在本質上的寥落與衰敗。
因此,她的小說題材大抵都關乎著人生之本然的破碎、殘缺、喪失、消逝,其基調也是灰茫而荒涼的:《去寬窄巷跑步》里,不同年齡的三個女人用自己的方式隱藏著、抹平著生活的罅隙;《跳繩》里,畫家小向的猝死背后隱藏著瑣碎的卑賤與令人驚異的秘密;《空間》里,兩個老戰(zhàn)友之間看似牢靠的關系卻透過家宴隱隱閃現(xiàn)出人性的殘忍與弱點。
在《蠶頭燕尾》里,這樣的主題與基調因涉及到死亡及其帶來的精神疾患而抵達了極致。小說一開篇展現(xiàn)的是一幅老年的陰冷圖景:冷醫(yī)生的老伴“妹妹”中風,身為西醫(yī)的他在退休后不得不重新學習針灸,為老妻治病。他每天耐心地給銀針消毒,給妹妹做康復治療。他知道妻子怕疼,因此不斷地哄她,為她翻身,笨手笨腳地照顧兩個人的起居飲食。這種生活一點也不光鮮亮麗,與我們熟悉的城市生活、現(xiàn)代生活格格不入,但它的真實度卻毋庸置疑。即便我們尚未到達那樣的年齡,卻完全可以憑借經驗知道,它終有一天會將降臨到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換言之,我們未來都是冷醫(yī)生或冷太太。
周李立的敘事是極其耐心而有韌勁兒的。她不厭其煩地用老年生活的細節(jié)一遍遍強化著冷醫(yī)生的狼狽無助,同時也一遍遍強化著他對于妻子的愛與溫情。當他不停地與妻子說話、嗔怪她、安慰她、氣惱她時,這種并不灼烈的老年之愛讓人心軟得想要落淚。但是,作者并非歌頌耄耋之情,其敘事暗藏著機鋒與寒意。故事的轉折來自于妹妹的隸書習字,因為紙邊開始發(fā)黃卷翹,冷醫(yī)生決定將它們裱起來。他把妻子一個人留在家里,自己去了文具店。
有兩個細節(jié)隱隱向讀者推送著不安的微瀾:一個細節(jié)是冷醫(yī)生遇到前同事陸醫(yī)生,告訴他自己和妹妹都挺好,陸醫(yī)生湊近了仔細看他,似乎有所擔憂;另一個細節(jié)是文具店店主說“人不在了”,裱好其字也“是個念想”。冷醫(yī)生對這兩個人都非常生氣,因為他們似乎都不相信妹妹依然在治療之中。而對于冷醫(yī)生來說,妹妹是他的珍寶,他決意要盡力治好她。
事實上,讀及此處,我們仍然會繼續(xù)“迷惑”于作者的敘事“偽裝”,慨嘆冷醫(yī)生的深情和執(zhí)著,而忽略了那個被偶爾提及的成人用品店,是它在最后掀開了“謎底”:冷醫(yī)生在那兒問過仿真娃娃的價錢,后從網上購得,這就是他的“妹妹”,是他在老伴去世后用來安放愛與溫情的存在物。因此,這個日本進口的娃娃身體里滿是銀針,最終承受不住而崩潰。冷醫(yī)生悲憤地告訴陸醫(yī)生,他要去控告賣假冒偽劣產品的“無良商販”。
這個結尾的揭示相當利落,令人深感恐懼。我們恐懼的不是娃娃的崩潰,而是冷醫(yī)生無法直面失去伴侶而產生的精神幻覺,他向著娃娃(妹妹)的那些飽含著自我慰藉與自我欺騙的呢喃,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在老之將至時無法回避的難堪和痛楚。這個表述是周李立小說的共同主題:生命終將寥敗,我們都走在通向寥敗的路上。這種透徹讓小說充滿了平靜而篤定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悲傷或哀憫地重復著這個主題,而是極其平淡,仿佛視之為春河奔騰,夏花盛開,秋葉飄落,冬雪蒞臨,一個自然而然的常態(tài)。她要做的,無非是將這個過程用藝術化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讓我們提前預習或間接感知它并不美妙的質地和滋味。
在我看來,作者藝術化的展現(xiàn)手法是盡力隱藏起精心設計的斧鑿痕跡,以與敘事相契合的意象對小說內容進行呼應和放大:“蠶頭燕尾”,正如其名,正如其意,作者將生命的寥落過程蘊藏在這個文雅古老的命名里,因為它們都有著“飽滿的開頭,與逐漸纖細下去的結尾”,濃墨重彩與輕巧無力并行不悖。這種精致的設計在其他小說中也相當?shù)湫停骸短K》的“繩子”,《骨頭》里的“棒骨”,《愛情的頭發(fā)》里的“頭發(fā)”……這些意象將小說內涵提純?yōu)橐环N突兀的姿勢,提示著殘缺與喪失作為常態(tài)的存在。
如果你和我一樣,經常忘記這種常態(tài)而自得于蠅營狗茍,那么,不妨看看周李立吧。
曹霞,著名文學評論家,現(xiàn)居天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