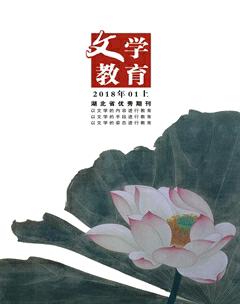淺論廢名詩歌的文化心理背景
內容摘要:廢名的詩常給人難解的印象,事實上難懂的并不是詩,而是其深玄的創作背景。了解其詩必須首先了解廢名其人,本文從創作心理視角切入,探討童年經歷對廢名人格構成及文學旨趣產生的影響,分析廢名敏銳的藝術感知力、學貫東西的知識儲備以及詩情恣肆的創作沖動。通過對廢名詩歌創作心理的分析和創作背景的把控,進一步理解廢名的詩歌創作。
關鍵詞:廢名 詩歌 創作心理 創作背景
一.引言
在20世紀中國文壇,廢名別具一格的詩風使他游離于大眾審美外,因而詩名不盛。劉半農曾在日記中寫道:“廢名,即馮文炳,有短詩數首,無一首可解,而此人乃見賞于豈明,不知何故。”[1]“無一首可解”的評價固然有失偏頗,但廢名之詩難懂是毋庸置疑的。究其原因,廢名常以強烈的主觀感悟作為詩歌創作的依據,并形成了獨有的邏輯言說方式,打破常規思維,給予讀者“陌生化”的審美感受,因而留下了“難解”的印象。
朱光潛說:“廢名先生的詩不容易懂,但是懂了之后,你也許要驚嘆它真好。有些詩可以從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詩非先了解作者不可……他的詩有一個深玄的背景,難懂的是這背景。”[2]這段話可以看作是品讀廢名詩歌的“解詩法”,即必須先了解廢名其人,了解他深玄的創作背景,才能讀懂廢名的詩,品味其中的美感與詩意。
因此,本文從創作心理視角切入,分析廢名的人生經歷及其心理流變,從而更好地把握廢名詩中深玄的背景,更好地理解廢名的詩歌創作。
二.苦難的童年時代:“小孩子我替他畫一個世界”
根據弗洛伊德人格發展理論,童年經歷對人格形成有重要影響。冰心曾說:“不論童年生活是快樂、是悲哀……有許多印象、許多習慣,深固地刻劃在他的人格及氣質上,而且影響他的一生。”[3]事實正是如此,兒時經歷對廢名的人格構成和文學興趣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從“本我”到“超我”的人格構成
1906年,6歲的廢名患上淋巴結核從私塾退學。這在當時是“不治之癥”,但年幼的廢名掙扎著從死神手中逃了出來。篤信佛教的祖母和母親感念五祖菩薩保佑,帶著大病初愈的廢名去了故鄉黃梅縣五祖寺進香。家鄉的佛禪文化就這樣震撼了年幼的廢名,“他放肆地爬上了桌子,兩腿趺坐,雙目微閉,輕擊木魚,一邊小聲地誦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活脫脫一個小和尚!”[4]
在廢名生命之初,因為疾病而產生的對死亡的恐懼和無意識的求生本能讓他走上了求佛信禪的道路,即從“本我”走向了“超我”的人格境界。童年的經歷讓廢名性格內向,不喜交際,偶有厭世。他就如朱光潛所說“不倚門戶,淡泊自守”,也如卞之琳所言“從不趨時媚俗,嘩眾取寵,從不知投機為何物”[5]。他不逢迎,不向世俗世界的成規低頭,而始終生活在儒道釋交融的超我世界里,在理想國中尋求自我價值。
(二)“心悅佛禪”的文學興趣
從心理學涵義上講,文學興趣的最初產生,常常是在一個人的童年甚至幼年時期。[6]信奉佛教的祖母和母親、有“禪宗圣地”之稱的故鄉黃梅縣,種種因素大大影響了廢名之后的思想和文學創作。廢名成年后讀佛經、學佛理,與熊十力等人談佛論道,對佛家文化始終保有濃厚文學興趣,其詩歌也因個中禪意為人稱道。
以《夢之使者》為例,這首詩中廢名為女人寫“善”,為男子寫“美”,為厭世的詩人畫好看的山水,為小孩子畫一個世界。在佛家文化中,“真善美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佛國凈土的象征”[7],廢名將這種境界寄寓在所有人身上;“好看的山水”亦符合佛家崇尚自然的旨趣,性格內向而醉心佛老的廢名正是這樣一位偶有厭世的詩人,需要寄情山水之間;詩中的“世界”也即佛家的“娑婆世界”、“堪忍世界”,它要求眾生忍受“十惡”,承受苦難。
或許《夢之使者》里的女人、男子、厭世的詩人和小孩子都是廢名自己,他將佛家的禪理和所悟的禪思自然地融入詩中,讓讀者也感受到參禪悟道的詩意。可以說,佛禪文化為童年的廢名畫了一個新世界,使他之后的詩歌創作別具一格,自成一派。
三.敏銳的藝術感受力:“我的燈又叫我聽街上敲梆人”
(一)敏銳豐富的藝術知覺
藝術知覺是一種審美知覺,有著強烈的主觀性、豐富性、敏捷性、細膩性和深刻性。[8]對于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來說,敏銳的藝術感受力是尤為重要的。廢名雖對儒、道、釋頗有研究,帶有莊禪趣味和玄學色彩的作品也已成了他詩歌的標簽,但事實上廢名關注現實的詩作也不容忽視,他常常從平凡的生活中品味出不平凡的詩意來,而這類詩歌恰好是其敏銳藝術知覺的體現。
如《洋車夫的兒子》一篇,這是廢名早期較寫實的作品,記錄了一對父子簡短的對話。詩只有短短幾句,對話也稀松平常。然而詩人本能的藝術知覺讓廢名把日常的見聞變成了飽含深意的小詩。這首詩中,廢名深入了兒童純真的內心世界,這里沒有尊卑貴賤,也沒有貧富懸殊。社會的殘酷與黑暗,底層勞動人民謀生的艱辛都在這爛漫的童心前隱匿了。
詩人用兒童的口吻輕輕說出“只要一個銅子”,給了不平等的舊社會沉重一擊。詩歌主題廢名不置一詞,卻不言自明,引得讀者深省。可見,擁有敏感藝術知覺和豐富藝術創造力的廢名,與詩歌這種抒情的藝術形式是很相配的。
(二)學貫東西的知識儲備
廢名自幼在故鄉書塾學習,從師讀《三字經》、《百家姓》等經典作品,正規的書塾教育為廢名打下了扎實的傳統文化基礎。24歲時,廢名升入北大英國文學系讀書,對莎士比亞、哈代、契訶夫、塞萬提斯等多名西方作家及其作品有了深入研究。而自辛亥革命爆發以來,廢名緊跟時代潮流,接觸最前沿的科學民主思想,關心革命和文學運動,誓將畢生精力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再加上他從小受到的佛家文化熏陶,可以說他是真正博曉古今、學貫中西之人。
從廢名的詩歌作品來看,不同于同時代的詩人,西方文化對廢名的影響似乎是內化的,在北大外文系學習的經歷成了廢名反觀東方文化的窗口。他的詩歌固然受到了波特萊爾、艾略特等人的影響,但更顯著的還是底蘊深厚而古老神秘的東方文化——是中國才情橫溢的溫庭筠、李商隱,是印度拈花微笑的佛教禪宗。endprint
無論是《妝臺》中不可有悲哀的“妝臺”還是《掐花》里照徹一溪哀意的“月亮”,抑或是《自惜》里供我偷生的“鏡”,廢名的詩常常有一種古典詩詞的哀愁,他的意象選取也構成了“鏡花水月”的古典意境。
再看《海》中蓮的“出水妙善”,《星》里似幻似真的“春花秋月”,《燈》里頓悟的“拈花一笑”,廢名以工筆寫禪心,用禪宗式的直覺思維打破了人們慣用的邏輯思維,讓讀者嘆服其神秘宏大,也有感于其詩歌難以言傳的詩意。
(三)詩情恣肆的創作沖動
文學創作者大多有過創作沖動,柏拉圖稱之為“靈感的迷狂”,果戈理則叫它“甜蜜的戰栗”。廢名也有過類似的迷狂與戰栗,當詩意襲來時“仿佛池塘生春草”勢不可擋,有時甚至“只有一兩分鐘便寫好”。[9]這種突如其來的靈感與廢名深厚的積累是密不可分的。
以《燈》為例,這首詩一氣呵成、展現了廢名詩情恣肆的靈感和才氣,更展現出他深厚的知識背景。詩的前四句寫實,詩人深夜讀《道德經》,與一盞孤燈相晤一室,參透了道家吉兇悔吝的人生哲學。第五句由道入佛,進入了“貓不捕魚”、物我相忘、拈花微笑的境界。而第八句從貓又聯想到了去年冬夜的“小耗子走路”、“夜販的叫賣聲”和“年青人的詩句”,然后重新回到魚——“魚乃水之花”。最后,燈光寫了一首詩,但我卻不讀他的寂寞。“我的燈又叫我聽街上敲梆人”,一個“又”字帶出了許多個與孤燈相晤一室的寂寞夜晚,分不清是“燈”的寂寞,還是“我”的寂寞。
從其內容看,這種兜轉的思緒、自由的聯想,馳騁的詩情不正是廢名欣賞的溫庭筠嗎?像廢名說的,“溫詞無論一句里的一個字,一篇里的一兩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個幻想,上天下地,東跳西跳,而他卻寫得文從字順,最合繩墨不過。”[10]廢名的詩也是如此。從其結構看,全詩在漫無邊際的想象中展開,沒有邏輯線索可尋。廢名談及自己的詩歌時說過:“我的詩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不寫而還是詩的……”[11]
這種以絕對自由的意識流動制造詩意的方法,正是西方意識流手法的內化體現。再加上佛老文化帶來的禪宗頓悟與哲學玄思,讓廢名的詩歌言有盡而意無窮。
可見,廢名思路跳躍、難解難懂的詩,是東西方多種文化背景作用下的產物。如朱光潛所言,難懂的不是詩,而是復雜的創作心理和深玄的寫作背景。
四.結語
總而言之,廢名多舛的童年經歷,輾轉的人生歷程讓他走上了信佛參禪的道路,影響了他的人格構成和文學旨趣;其敏銳的藝術知覺,跨越古今、融貫東西的文化底蘊,以及勃發的創作沖動則為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它們共同構成了廢名自成一脈的詩風,陌生化的詩感及自由的詩意。如周作人所言:“廢名君是詩人。”[12]
注 釋
[1]劉半農:《新文學史料·劉半農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1期.
[2]朱光潛:《文學雜志·編輯后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卷第2期.
[3]冰心:《我的童年》,黃河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頁.
[4]郭濟訪:《夢的真實與美——廢名》,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5]卞之琳:《馮文炳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6]見魯樞元:《創作心理研究》,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頁.
[7]慧廣:《生命的真相》,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頁.
[8]魯樞元:《創作心理研究》,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頁.
[9]馮文炳:《談新詩·<妝臺>及其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10]馮文炳:《已往的詩文學與新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11]馮文炳:《談新詩(妝臺)及其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12]周作人:《<桃園>跋》,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版.
(作者介紹:張嫣然,武漢大學文學院2015級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