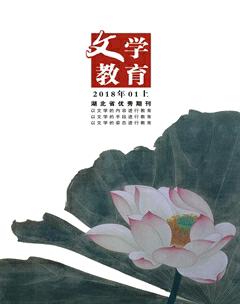湖南文學作品的湖湘文化背景及文化精神探索
易蕾
內容摘要:對湖南文學作品的湖湘文化背景及文化精神進行分析。具體是從愛國精神、政治抱負、個體魅力以及學者化追求幾方面闡述湖南文學的精神文化氣質的基礎上,從流寓文化、理學文化與紅色文化三方面解析湖南文學作品的湖湘文化背景,對湖南文學與湖湘文化精神兩者間的關聯性進行摸索。希望湖南文學作品能夠蓬勃發展。
關鍵詞:湖南文學作品 精神文化氣質 湖湘文化背景 文化精神
湖南文學為中國文學體系重要組成成分之一,與他類地域文化相比較,湖南文學從思想與藝術上均別具特色,該種個性化風貌都和湖湘文化精神相關聯,湖湘文化精神對湖南文學的精神風貌和藝術風貌均會形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湖南文學和湖湘文化精神間的關系體現出繁雜化與多樣性等特征,這也是湖南文學作品思想內涵與藝術彰顯出來的動力。本文以湖南文學作品的湖湘文化背景及文化精神為論點,做出如下論述內容。
一.湖南文學的精神文化氣質外在體現
一是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一文化氣質在先秦兩漢時期就有所體現,屈原是典型的愛國主義者,借用炙熱的愛國情懷書寫了楚辭《離騷》,將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懷充分的顯露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屈原的作品成為湖南文學愛國主義精神的楷模。近代中國也處于一個動蕩不安的局勢中,湖南眾多知識分子又一次奔赴在時代的前沿,迸發出救亡圖強的憤慨。
二是政治抱負。湖南文學對政治局勢發展狀況給予極大的關注的發展情況,解析政治層面上收獲與缺如,能夠傳遞出群眾生存發展相關的信息,表達出學者們對國家政治運行趨勢以及社會發展情況高度關注的情感,從某種層面上講者強化了湖南文學體系內容。著名政論文有《過秦論》、《陳政事疏》、《祭戰馬文》與七言古詩《伐棘篇》等作品。
三是充實的人格魅力。湖南文學創作品中,很多彰顯出個體樂觀向上的心態,對艱難險阻不屈服、奮勇直前的價值觀念,體現出極可敬可畏的主體人格精神。例如“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出自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充分的將一個革命者視死如歸、維護真理的樂觀主義精神全面的呈現出來。
四是彰顯出學者化的向往與崇尚。這是湖南文學創作主體精神高度的體現方式。湖南文學創作主體的學者化特征隨著歲月的累積而日益濃烈,其最大的特征是協助湖南文學主體呈現出高尚的思想境界與扎實的文化功底。例如王夫之、張九鉞、孫起棟、歐陽輅均是大學問家的代表人物。
二.湖南文學的湖湘文化背景
一是流寓文化。過去流寓在湖南省地段的創作者數目是較為龐大的,他們將自己的思想情感與創作風格融入進文學藝術作品中,從而使讀者有“見字如見人”的感覺,領域作家的藝術審美理念,對他們萌生出崇尚與追隨之感,從而使湖南文學體系愈發充實。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中,湖南本土的文學體現出滯后性特征,為一些流放或落魄文人寓居于湖湘,點綴了該處文學的輝光。例如屈原二次被貶以后,泛舟經由洞庭,自由的穿行在辰陽山內,在湘江澤畔吟唱,作《懷沙》后投進淚羅江中。屈原把生命的絕響和辭賦的絕筆留置在湖湘,也使楚辭文化在這片沃土上根深蒂固。自屈原以后,又有一些文人墨客流寓在湖南的三湘四水間,可能是抑郁不得志,也可能是游玩至湖湘。李白與杜甫于流離失所的情景中均經由過胡湘,留下令后人絕唱的詩篇。柳宗元也曾書寫過《永州八記》、《天對》等絕世篇章。上述文人墨客均帶動著中國文明史發展進程,為詩學與美學創造了一個有一個巔峰,也彰顯出文學家生命大化的人格特征與藝術理念。
二是理學文化。理學最大的特征就是把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與個人生命信仰以及追求整合在一起,從而打造出結構更加完整、內容更加充實的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同時使該體系具備較高的邏輯性、抽象性和真理化。強化了理學具的自主意識,構建了理性大于權勢,道義高于了治統的政治理念,在限制君權,使我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間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支撐。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將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取而代之,可以被視為我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三是紅色文化。具體是指中國共產黨帶領下的中國革命與構建進程中產生的革命理論、革命經驗與革命精神,最終匯聚成的革命傳統。在革命戰爭年代,由中國共產黨人、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一并構建極具中國文化特征,飽含豐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歷史文化蘊意。在紅色故鄉中成長了很多杰出的“紅色作家”。縱觀現代文學史,湘籍作家在全國所占比重極高,在文學上獲得的成就也是極為顯著的。
三.湖南文學與湖湘文化精神的關系
(一)秉持“經世致用”的原則
盡管如此,湖南文學也具備融情于湖湘山水的閑情逸志。例如王夫之在《楚辭通釋·序例》有“楚,澤國也。其南沉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崇嵌戌削之幽苑,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的語句。對上述語句的內涵進行剖析,在湘楚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湖南本土作家在對土地風貌描寫的同時將個人理想整合其中,多數是將自體的悠閑情調傳遞出來。例如南宋詩人王以寧經歷了“靖康之變”以后,所作詩句體現出愛國情懷。還有部分作家因為社會政治面貌波動性較大,不愿在亂世中茍活,也可能是由于仕途坎坷而過上了田園生活。
(二)湖南文學大膽創造
在五四新文化時期湖南文學優良一定創新,在毛澤東、徐特立、黎錦熙等前輩的宣傳與帶動下,營造了較為濃郁的文化氣氛,出現了一批暢飲我國現代文學史的知名作家、文學理論家,他們對我國文學事業發展起到引領與導向作用,主要以田漢、歐陽予倩、成仿吾、沈從文、丁玲、周立波、張天翼、謝冰瑩等人物為代表,上述文學創作者在自己所在文學領域獲得一定成就,為該領域可持續發展做出一分貢獻的同時,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所持有的地位也是不可動搖的,并且對建國后的湖南文學創作風格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建國后的40年的時代中。前期出現“文革”,湖南文學初步構建了蓬勃發展的情景。他的繼任者康濯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也是極為顯著的。在這樣的情景中,在湖南文學土壤中未央、周健明、、任光椿等具有一定實力中青年作家相繼出現,他們寫出了一些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作品,逐漸形成了湖南作家群獨有的思想風格和藝術特色。這個階段的后期,亦即從“文革”到1989年,湖南文學事業發展步履艱難,湖南省眾多作家承受了復雜的人生考驗,繼而在不懈奮斗中創造了湖南文壇又一個美滿的春天。湖南文學體系的發展,始終是以創新為動力的,但是文學作品在創新過程中,一定要尊重差異性與多樣性,即按照藝術發展規律而運行,只有這樣才能夠為文學風格創新目標的達成創設更為寬闊的環境。湖南文化在創新發展的過程中,卻不忘尊重創作主體的思維觀念,在真正獨立而清醒的探究精神輔助下去達成一個有一個目標,獲得一定成就。創作者擁有特殊的價值觀念是創作力量的源泉,湖南文學作家在對創作形式與風格創新的過程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念為指導思想,積極在作品創作期間把主體和主體、個體和社會、現實和理想整合在一起,以防創作的抽象性以及概念真實性缺失。文學創新始終要以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為基點。對文學作品采用這樣的創作思想,文學的獨創思維,不但是對故事類型和表達形式的優化,同時也是對自我文學水平的挑戰與提升,不復制別人以及自己過去的創作形式。endprint
(三)湖南文學創作方法以現實主義為主導
對湖南本土籍文學家來說,從漢代到唐朝,著名人物寥寥無幾。伴隨著理學的創建,尤其是湘學的創建,湖南文學傳承了歷史傳統的同時,也具備新的特征,湖南文學的創作就有了明確的文藝理論進行指引,采用了“文以載道”以及“經世致用”的文學創造理念,對現實社會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藝術上以客觀寫實為主導。以現實主義手法進行作品創作,優勢在眾多方面體現出來,這主要是因為現實主義沖破了理想化的局限性,而提倡細密觀察事物的形態表征,參照上述說辭,可以將寫實主義理解成涵蓋不同文明時期藝術創作理念的整合體。
湖南文學創作方式始終以現實主義為主導,浪漫主義創作色彩卻沒有被完全淹沒,并且在中國文學創作進程中湘楚文學的浪漫色彩是極為濃烈化的也。屈原《離騷》為是經典,聯想空間寬闊,象征性整體性體現出來,是對主人公清高、鏈接品質的有效寫照,可以被視為打開中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先河。故此,屈原著有湖南“文學之鼻祖”制成。但是在屈原楚辭之后到清朝末年時段,湖南文學的浪漫主義創作方式整體上分析是較為罕見的,李東陽、張九鈾的部分詩詞將浪漫主義色彩彰顯出來。例如李東陽《南行稿》中的《引丈江行》作品在創作過程中整合了浪漫主義思想,闡述了長江的險絕雄奇與氣象萬千,并傳遞出長江的神奇和偉岸,浪漫主義色彩鮮活而濃郁。
通過全文論述的內容,認識到湖南文學作品在湖湘文化體系中所占據的地位,并對湖南文學與湖湘文化精神有更為深入的認識:一是秉持“經世致用”的原則;二是湖南文學大膽創造,也體現較為守舊思想;三是湖南文學創作方法以現實主義為主,體現出楚文學特有的浪漫主義。湖南文學經歷不同時期,在不同創作風格群體的帶動下,推向至一個有一個光輝時段,在鄉間文學品格的帶動下,相信湖南文學將會獲得廣袤的發展空間,在我國文學史上創造更大的成就。
參考文獻
[1]吳杰.在批評中彰顯中國精神——2015年湖南文學評論綜述[J].創作與評論,2016,06:42-49.
[2]向點思.從“外部研究”走向“內外結合”——新時期以來湖南高校所編文學理論教材簡評[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5,3104:153-155.
[3]吳杰.打撈文學批評的批判精神——2016年湖南文學評論綜述[J].創作與評論,2017,06:57-64.
[4]鄭學.鄉邦世族與晚清詩學傳承——以湘社為例[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101:217-222+183.
[5]許又聲.用青春書寫中國夢的湖南篇章[J].新湘評論,2015,16:4-6.
(作者單位:岳陽廣播電視大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