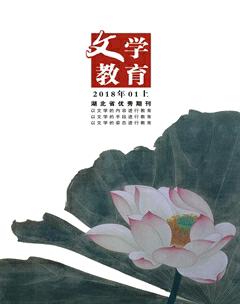劉恒稱寫作也是用文字表演
2018-01-22 21:56:52
文學教育 2018年1期
關鍵詞:生活
由劉恒任編劇的話劇《窩頭會館》日前在京首演,劉恒在接受采訪時說:“不論是寫小說、寫劇本、寫電影劇本、寫話劇劇本,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寫給最愛的人的情書。所有文字都滲透著我的愛。”從這個角度看,寫作與生活無異,遺憾和歡欣里,功不唐捐;苦苦求索又全情投入的創作時刻,恰似對生命的書寫。《窩頭會館》當年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話劇,顯得有點“特別”。劇中迂回地通過對解放前北平破舊院落底層人物點滴生活的描寫,洞察和折射一個舊時代的崩潰。“寫電視劇是瓦匠砌磚頭壘墻,寫電影劇本是木匠打家具,寫話劇是石匠雕塑像。一個比一個細膩,或許一個也比一個難。”在“雕塑像”過程中,劉恒一方面從歷史資料中吸取營養,另一方面調動個人生活經驗。在他看來,《窩頭會館》不僅是向生活致敬,也是向遙遠的過去和近在眼前的現實致敬,向北京人藝的獨特風格致敬。《窩頭會館》的三幕戲劇結構,讓人不自覺地聯想起《龍須溝》和《茶館》,苑國鐘式的走投無路和自我調侃像極了老掌柜王利發的背時倒運,有著共同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審美意味。然而,這種致敬并非克隆經典和自我禁錮,“我希望能在這部劇里用自己的方式對這種風格給予新的開拓和展示”。endprint
猜你喜歡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2018年1期)2018-02-22 09:00:43
黨的生活(黑龍江)(2017年12期)2017-12-23 17:01:20
求學·文科版(2017年10期)2017-12-21 11:55:48
求學·理科版(2017年10期)2017-12-19 13:42:05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07:16:27
少年博覽·小學高年級(2016年12期)2017-01-16 12:48:35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爆笑show(2016年3期)2016-06-17 18:33:39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