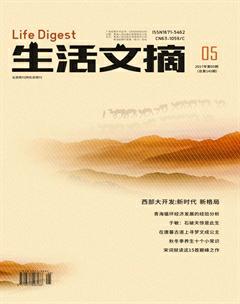尋找漢江新源
漢江源頭不在陜西寧強而在陜西太白,你一定會感到驚訝!這一顛覆性的結論與古人和現代人認定的漢江源大相徑庭,不少人會產生迷茫和不解。兩千余年前,古人認為漢江源在嶓冢山漾水,現代人則認定是玉帶河,今人又論在太白。新河源何故北移百余公里呢?事實上河源理論的發展完善,現代測量技術的進步,地理信息系統的現代化,把過去認為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讓河源地理更準確,成為趨勢成為可能。
一、質疑前人河源
河源,顧名思義,就是河流的源頭,是河流第一滴水,產生第一縷涓流出發的地方。隨著社會和經濟進步,人類認識河流規律被進一步掌握并不斷準確,這幾乎是世界認識河流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國外是這樣,中國也不例外。中國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在幾千年中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提升,河源位置多次發生變化,總體趨勢是向上游移動,并不斷使河源位置更準確,漢江作為長江的第一大支流也同樣如此。
成書于唐虞之際,據說是大禹、伯益而著的《山海經》中說:“漢水巖附魚之山,常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陽而蛇衛之。”附魚在何處,現代人至今不知其確切位置。《尚書·禹貢》中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水”。這是最早關于漢水源頭的記載。“漾”和“漢”都是河(流)之名,一個漾水,一個是漢水。嶓冢山的漾水,史籍記載有二處。一處在甘肅天水市齊壽山,此漾水為西漢水,它是嘉陵江的源頭之一。另一個漾水是陜西寧強嶓冢山下,曾稱為古漢水的源頭。古人對漢水源頭在何處,幾乎爭論了2000多年,直到唐宋時期才有了比較一致的認識,即漢中嶓冢山為漢江源頭。當代最權威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持此說法。南宋時期,著名愛國詩人陸游在川陜抗金戰爭期間,多次在駐地周邊考察,留下了嶓冢之山高插云,“漢江溜溜日東去”。“嶓冢山頭是漢源,故祠寂寞掩朱門”的詩句。現在人對漢江源的認定發生了變化,2009年出版的《中國河湖大典·長江卷·下》表述:漢江有北、中、南三個源頭,北源為沮水,中源為漾水河,南源為玉帶河,何處為漢江正源呢?古今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古人把位于秦嶺與米倉山之間的漾水稱為中源,認為是正源。由國家長江委編纂的《長江志》,按河流唯遠原則,把發源于陜西鳳縣紫柏山西部的沮水認定為正源。1942年,寧強人提出玉帶河為漢江正源。1979年出版的《辭海》的表述為:北源玉帶河出陜西省西南部寧強縣,東流到勉縣和褒河匯合后稱為漢江,玉帶河河源在寧強縣陽平關鎮曹家垻村。
史籍記載的漢江河源和當代關于漢江河源的記載表述和結論,按現代河源理論中干流唯長、水量唯大、河流順暢、海拔唯高等原則,并不完全符合。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但按現代河源重新審視河源,應當是當代水文,水利等科學家和水利工作者的責任和不二選擇。于是陜西省寶雞市水利、水文工作者,從21世紀初,特別是國務院發出“全國水利普查”通知后,就把漢江河源調查當作自己分內的業務。把目光盯在符合“四唯,唯大(水量),唯遠(長度),唯順(河流順暢),唯高(海拔)”條件的秦嶺南坡褒河源頭的地區,開展了縝密的普查和調查。
二、中秦嶺西段新漢源區
秦嶺是中華龍脈,橫跨甘肅、陜西、河南、四川、湖北、安徽等省。地理學上把秦嶺分為西、中、東三部分。嘉陵江干流以西為西秦嶺,嘉陵江以東到華山為中秦嶺,華山以東至大別山為東秦嶺。按照“四唯”褒河源符合作為漢江源頭的基本要求。褒河流域在中秦嶺地帶,河源在鳳縣、太白兩縣交界相鄰區域。現代地理科學技術已相當發達成熟,現代航拍和地理信息系統可以把河流水系記述得細如發絲般準確,把河流走向,海拔高度,河流水量等反映得確確切切,借用現代化的地理信息系統,準確定位漢江河源不應該成為問題。中秦嶺西的代王山,海拔2598米,是歷史上稱為大散嶺的一部分。代王山秦嶺主脊南坡東峪溝涼水泉是嘉陵江的正源。代王山秦嶺北麓是渭河支流清姜河的源頭神沙河,代王山的秦嶺主脊的中曲河,是褒河流域最西的河,與嘉陵江流域相鄰,它是褒河的西源。秦嶺主脊南文公廟海拔2317米處以下,是上河(紅巖河上游也稱虢川河),此河幾乎正北向南流到塘口村后成為紅巖河上游一段也稱虢川河,它是褒河的中源。太白縣城東南,海拔3476米的鰲山南麓,海拔3000米左右處,孕育了另一條褒河的源頭——太白河。太白河為西南走向,它是褒河的東源。這三條褒河源頭的河流,在江口鎮前匯入傳統觀念上的褒河。
利用手頭的水文資料和從朋友那里索要來的水利普查資料,可初步分析褒河源頭的水文狀況,并確認褒河源就是漢江源。褒河干流長195千米,比古漢源北源沮水干流長65千米;比南源玉帶河長99千米,比中源漾水河長123千米,從流域面積分析:褒河源流域面積3991平方千米,比漾水流域面積大245平方千米,比玉帶河流域面積大3181平方千米,比漾水河流域面積大3415平方千米。把這三條河總流域面積加起來為2962平方千米,褒河流域面積仍大1029平方千米。從年總徑流量來分析,褒河平均年經流量14.7億立方米,比沮水多6.4億立方米,比玉帶河多11.1立方米,比漾水河多12.1立方米。原漢江河源的三條河流年總徑流量14.5億立方米,褒河略多一些。
從河源高度來看,新河源在2100~3000米之間,均高于原來的河源高程。
從以上分析,寶雞市水利工作者S君提出,中秦嶺南麓的鳳縣、太白交界處的幾條河流,作為漢江新源區,符合現代河流源頭確定的基本原則,應當作為漢江新源來考慮,也就是自然地理。而歷史上曾作為源頭的古漢源、玉帶河、沮水可作為歷史文化河源。這一研究考察成果,為漢江新源尋找開啟了一扇可借鑒的門窗。這一研究成果被《陜西水利》2013年第4期發表,《陜西河流觀察》2014年第1期發表。研究成果被寶雞市政府評為2013~2014年自然科學獎。
三、首席科學家認定的漢江源
2013年夏季的一天,中科院遙感數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員河流首席專家劉少創帶隊,實地考察了漢江古漢源,中源嶓冢山石牛洞,南源玉帶河,北源沮水。這次考察漢江源是劉少創等重測全球江河龐大項目的一部分。當考察隊到達沮水源頭時,發現此河已淪為一條季節河。長江水利委員會編撰的《長江志》中,把發源于陜西鳳縣柴柏山西部的沮水作為漢江北源,并認為是正源。按河源確定幾乎是約定俗成的規定,季節河是不能作為河源的。2003年由地貌學家組成的考察隊,在確定“中國漢江生態文化漂流”起點時,基本否定了嶓冢山石牛洞為古漢源的說法,他們把玉帶河作為生態文化漂流點,并在玉帶河畔立碑“漢江源”之碑。劉少創等考察了玉帶河,漾水石牛洞等唐宋以來和現代人們認為的漢江源后,按照河流確定的“四唯”原則,移師秦嶺山脊太白縣塘口以北的褒河。劉少創的考察隊朔褒河而上,來到太白縣嘴頭鎮塘口村,過上河林場繼續北上,在秦嶺主脊南側,手掌狀的山地上,找到了眼泉水。泉水旁是濕地一片,運用具有長度量測功能的遙感圖像處理系統,利用衛星遙感影像進行長度測量后確定,源頭坐標為東經107度22分30秒,北緯34度09分38秒,海拔2150米,考察認為褒河源頭就是漢江新源頭。劉少創對漢江長度重新進行了測算,以新源頭為起點,新漢源以古漢源為起點的河長108千米,比沮水為正源的河長20千米,比玉帶河為正源的河長41千米。按照這個新數據漢江全長1570千米,其中褒河長208千米,褒河以下長1362千米。新河源確定后,部分河段的主次關系發生變化,原來作為主干的那一部分變成支流,原褒河河床變為主干的一部分。漢江新源頭這一結論刊登在2014年9月14日《十堰晚報》上。endprint
四、再踏塘口漢江新源
去新漢江源的必經之路是塘口。塘口距太白縣城東約八公里地。秦嶺主脊向南延伸到紅巖河(褒河上游)從鰲山腳下流過,太白縣嘴頭(虢川)與桃川兩鎮之間有一個五里坡,古稱衙嶺,地理上的衙嶺“分渭漢”,指的就是這里是渭水的石頭河與漢水的褒河分界處就在此嶺。塘口村東是衙嶺的一部分也是渭河流域(石頭河)與長漢流域(褒河)在太白縣境內的分水嶺。衙者,舊時指官府辦事的機關,衙嶺是辦事機關的分界線,不知此衙嶺到底東側是官府辦事機關還是西側,如今衙嶺修公路時在此鑿出了一個埡口。埡口石砌墻體上雕塑兩條飛舞的大龍,一個是黃色,一個是白色,其意為黃河和長江流域。紅巖河上河是衙嶺西的第二個河谷,第一個河谷地圖上沒有標注其名,它是海拔2243米的處發源的一條河。河兩岸有草灘、蒿谷堆、東溝等村莊。第二條河谷是塘口的上河,上河的最北端是秦嶺主脊,此段海拔2317米。從河流長度,河源地區海拔與高度來看,上河略勝一籌。塘口的上河,河流順暢得幾乎向北向南一條直線。在由北向南流進中,出塘口遇到鰲山北麓的阻擋,瀟灑得一個華麗轉身,入虢川河成為紅巖河的主干。
塘口位于虢川河的右岸,兩山間約近400米寬。下寬上窄的喇叭形河谷由南向北逐漸縮窄。8公里河谷,進入上河的河源區了。塘口河谷土地肥沃,晝夜溫差大,很適合于種植蔬菜。無污染、無公害的蔬菜品種多且品質好,產品被銷往全國各地,寶雞、西安等地的超市中,不乏其生產的蔬菜。蔬菜產業的發展,使塘口村近年幾乎不種糧食作物了。依靠蔬菜生產的收益,農村的土坯房變成一、二層的磚混結構樓房。不少家庭有汽車等。塘口村已成為富裕文明的秦嶺山村。塘口河谷中,過去有兩個行政村,一個塘口村,一個上河村,現在兩村合一,統稱塘口村。塘口村向北依次是榮家店、西巷口、上河村、上河林場等約8個村民小組。4年前,我們來此地考察褒河源時,這里的通村公路才修了一半約4公里,現在已修到上河村林場。上河河谷兩側,綠蔭碧郁蔥綠,青山蒼翠,芳草茵茵,上河水緩緩南流,河兩岸蔬菜地綠油油一片。收獲拉菜的車流在河谷中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塘口以上的河段是水利工作者常去的河流之一,2016年七、八月間,兩次來考察。7月18日,一年中三伏天,一年中最熱的時段。悶熱的天空飄起厚厚的云層。寶雞市散文家協會組織作家去太白采風,S君這次卻離開采風團去一趟塘口,走四年前的探源之路——上河再走褒河源。8月13日,是個周末,S君與四位熱心河源的同行們又去漢源頭從秦嶺主脊迷糊頂,去“綏陽小谷”從漢江褒河源到渭水伐魚河兩河源頭間的穿越。
7月18日,中午13時后,天上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秦嶺籠罩在煙霧之中。水泥鋪就的山間小路上漫上了一層薄薄的水流,路成了集雨面,雨水簇擁著向低洼的地方流去,上河水流頓時豐滿了起來。上河林場的白副場長,聽說我們要去探漢江源很是熱情。他告訴我們,2014年九月份,北京中科院的專家們來尋找漢江源,當時他不在場里,后來知道此事。對上河林場城內能被確定為新漢江源,他是很高興的。守護著這片青山綠水,其實是深山藏寶呀!當我們請他推薦一位向導進源頭時,他不加思索的推薦了塘口八組的余富。
余富我們是打過交道的熟人,四年前在上河林場,就是他給我們介紹了源頭情況,領我們進山一段。余富曾是林場請的當地農民工,十多年來就在林場工作。現在他在上河的家中,經營幾畝蔬菜田,是養30多牛的牧場主。3個兒子都大了,不讓老頭子進山吃苦了,他只好辭掉林場的工作,雖說是回到家里幫孩子們干些零星小活兒,但卻掙起了大錢,年收入20余萬元。白副場長領我們到余富家,家中門開著,庭院里停著一輛拉貨車,一輛小汽車,室內收音機響著,就是沒有余富和他家中的人。老白與余富的兒子熟,接通電話,問余富在哪里。原來余富這幾天幫村外的人收蔬菜裝車去了,不在家中。與余富聯系上了,聽說請他做向導,進一趟山,他很樂意去。余富說,我還可以順路看看自家的牛群。和余富溝通好了,明天一早把余富從打工的拐里村接到上河林場,一起去上河探源。
18日的雨下,19日凌晨停了。早晨起來雖然云層還很厚,但沒有落雨滴,我們懸著的心放下了。不下雨,就可以進源頭了。昨天的雨很大,今天雖然雨停了,但道路濕滑強行,雨淋在草木上露水很大,走山的路肯定不好走。去縣防汛辦,找幾套雨靴、雨衣穿了起來,去拐里村接上余富,和Z君等一起向源頭出發了。
上河的植被很好,下了一天的雨,上河的水大了,卻還清澈。河道兩側一米多高的蒿草,把河床緊緊地圍屏著,河畔被昨日降雨洗滌過的草木,蔬菜等綠茵茵的,河水在綠草的簇擁下,嘩嘩向南流淌著。余富做向導,走到山路前頭,在放牛人和采藥人走的小路前行。過去村上的人都住在上河的下游塘口附近,人們進山去放牛,耕田都是向北走,走上坡路,所以就把向北走的河叫上河。上河在林場以北,第一條河流叫車長河,發源于秦嶺南麓,從左岸匯入主干河流。從上河林北行約500多米,右岸,左岸兩條河流成“Y”字形。右岸的河流出自百草溝,當地人稱其百草河。從上河左岸與主干匯合,當地人把主干上河稱作西溝河。沿西溝上行約1公里多,上河主干(此段稱西溝)右岸是匯流的金長河,因有人在河里采過金子,就叫作金長河。流水的山谷叫金洞溝,從金洞溝流出來的水,匯入西溝河,形成上河的主干。一條圍欄擋住了前行的路,行人只能越圍欄而行。老余告訴我們,這是上河村的人為自己的牛群不亂跑而設置的圍欄。圍欄后是一個寬敞的山地草甸,放牧著余富的30多頭牛。老余的幾十頭牛就在這里牧放著,一個星期老余上來檢查一次,其余時間,牛自由的活動,餓了吃吃草,渴了喝源頭水,夜晚牛群擠在一起休息。秋末冬初,老余把牛收回圈里養著,或追肥作為肉牛出售。河谷的水在草甸里亂流著,一會兒在草甸中間,一會兒又流到兩邊的山崖旁。放牛人踏出的小路,在不高的草甸間延伸,像一條土黃色的蛇,在綠草間探著頭兒。過了這片草地兩邊的山又窄了起來,向一塊靠攏,河水在山間流淌。
向北再行1.5公里左右,一座小廟掩映在青翠的山林中,一處啞口緩坡上的廟叫文公廟,高不過2米,長不過2米,寬1米左右,不如農村富戶人家的雞舍。廟雖其貌不揚,卻都是全部石質材料砌成、墻石、房檐、屋面,清一色的花崗巖石材,而且雕刻精細。兩側的山墻石材上,雕刻的花瓶花卉的樣式大方而別具一格,工藝精湛。老余說,這廟少說也有200多年了,進山的人都在這里敬拜它。仔細端詳,小廟內有一瓷燒的小神像,如孩童玩具般大小,誰人給穿著紅色的衣服? 一個小香爐上,香插在香爐中,看來剛剛有人敬拜過。文公廟是紀念唐代大家韓愈,韓愈是唐代政治家、文化人,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對皇帝迎奉舍利大加抨擊,因多次痛斥佛不可信而遭貶,受盡顛沛流之苦。韓愈作為政治家、詩人、鐘情山水,熱愛大自然。太白山多韓愈父子廟,少佛家寺院,形成道強佛弱的宗教格局,可能與人們尊重韓愈有關。endprint
告別文公廟繼續向北前行約1公里,山間的草甸上有稀疏的灌叢,灌叢被溪水圍繞,流過一片濕地,向導余富前去雪找中科院劉少創等發現的水泉,卻沒有找到。4年過去了,泉水周圍的環境變了,泉水湮沒了,也有可能,也許我們并沒有找準位置。用4G手機測地理坐標,也因山中無信號而沒有結果,泉沒有找到,嘩嘩的水聲卻響滿寂靜的山坳。我們繼續遂水流而上,稀疏灌叢前是一塊形如魚體的山坳略帶微坡的山間空地,空地中長滿水艾草有沒人之高。高高的水艾草長得齊刷刷的,一片翠綠,叫不上名字的草本植物開著黃色的花朵,點綴在一片翠綠的山坳中,翠綠之中的黃色花兒在秦嶺主脊的南坡草地上盛開著,讓夏日的秦嶺更顯得俊秀。秦嶺主脊在這一段海拔并不很高,地圖上標注2300多米。主脊南坡的山崖石頭像一條條北方漢子與周邊的棵棵松樹相依偎,護衛著源頭的這片濕地。可能是進秦嶺主脊的人少,原來被行人踩出的小路,被小艾草擠占得幾乎尋不見路徑。一陣風吹來,搖曳得艾草隨風擺動,方可尋見曾經的小路。密匝的草讓穿越這片草地多了不少困難,草上的水珠打濕了衣服,高溫高濕下行人被水浸透,人們不得不脫掉雨衣輕裝前行。余富走在前面帶路,他高興的喊叫著,前面就是秦嶺大果梁(主脊),河源到了。
離開滿河川的水艾草,跨過西溝河上河,向西北方向行2公里,來到一個秦嶺主脊南坡,去當地人叫迷糊頂的地方,是8月13日再上源頭,找最早的源之水是主要。一片林帶,幾個水泉汩汩的流著水,這就是褒河源即新漢江源頭的第一縷清涼。我們幾個尋源之人,敬畏地蹲在泉邊,用手鞠著泉水,如饑似渴的飲了起來。頭源的水真甜。喝到漢江源頭的水,一路艱辛隨之被驅散了。
五、綏陽小谷新跨越
巍巍秦嶺是中華龍脊,龍脊兩側是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渭河在秦嶺北麓的廣袤原野上奔流,匯入到黃河的懷抱。漢江、嘉陵江等從秦嶺南麓的出發,投入到長江的懷抱。從古到今,人們穿梭在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之間,跨越秦嶺就成了家常便飯。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上,在人類尚處在幼年時代,跨越秦嶺,行駛在渭水的漢水間就成為人們的一種奢望,也是政治家圖謀國家統一, 是老百姓謀求安居樂業福祉的一種行動。人類在兩河間奔走就成為一種愿景,成為一種美好的期望。
歷史上從褒河流域的漢江,進入關中,再奪取長安曾是三國時諸葛亮謀劃的一個大的戰略,從現代人的分析研究當時人們的跨越,走的這條路就是褒河這條線。從太白塘口北上,翻越秦嶺,先取魏軍在陳倉的大本營,再圖首都長安。此謀略計劃在蜀漢建興六年(228)年的八、九月份被提起,其背景為當年春諸葛亮由祁山出兵伐魏失利,于初夏由箕谷沿褒斜道退回漢中,并命趙云燒毀棧道。八月魏明帝率兵,分兩路伐吳,鑒于吳蜀聯盟的戰略關系,擔任左將軍的諸葛瑾向諸葛亮求救。諸葛亮由于魏兵在祁山重防,褒斜道無法修通,所以做出了出兵綏陽小谷進攻陳倉牽制魏軍東進的計劃。史料記載,諸葛亮出兵綏陽小谷只是個計劃,并未實施。而當年冬由陳倉古道出散關圍攻陳倉,也由于魏國守將郝昭的知兵善戰漢兵失利不得不退兵漢中。雖然“綏陽小谷”奇襲的謀略并未實施,卻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從漢水流域到達渭河流域的關中的捷徑。也是后來的兵家研究的一個課題。如今大批驢友穿梭在太白塘口與伐魚河,十八盤之間,走的就是諸葛亮提到的綏陽小谷。
如今不少人從塘口北上,翻越秦嶺主脊,進入渭河流域的伐魚河。爬秦嶺主脊的迷糊頂上,北望渭河如條黃色的長龍在秦川大把而蜿蜒,寶雞陳倉隱約可見。塘口以此上河兩岸河谷寬敞,秦嶺主脊兩側十余公里山高路險行走困難,如果今后經濟發達了,要選擇太白進入渭河平原選一條最短的路線,綏陽小谷是最好的一條捷徑,是最好的跨流域穿越路經。人們期待,三國時的綏陽小谷,現代人不僅是徒步穿越,而是公路、高速公路等現代交通工具的代步穿越。這一歷史的穿越,會在不遠的將來實現的。
河流是大地血脈,水源是河流文化的起啟點。人類文明幾千年,與河流結下了難解之緣。人類認識河流和它的源頭是一個不斷漸進的過程。世界十大河流,幾乎有一半多都存在河流變更,被人們重新認識新河源的歷史過程,漢江源2千多年間,河源地幾多變化,這是歷史的進步,是科學技術和人類認識河流河源的進步;漢江河源的新解,但愿不是尾聲而是新的開始,人類和自然界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發展和前進的。
作者簡介:常崇信,陜西省作協會員、中國水利作協會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