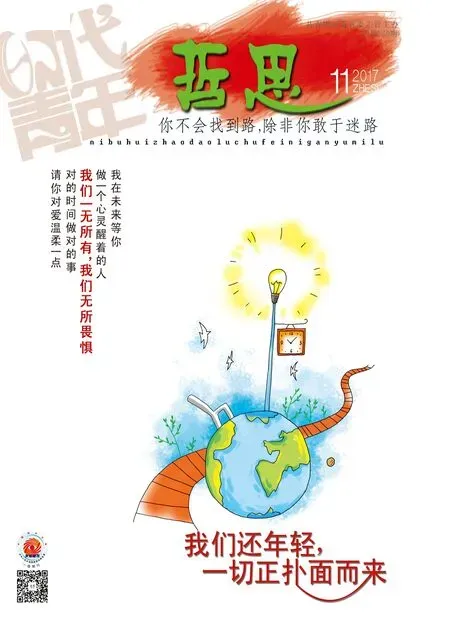你要驕傲地老去
◎阿 赟

上幼兒園的那段時間,我是跟著姥姥一起住的。每天放學,背著小書包走過兩條巷子回家。打開門,姥姥就會招呼著:“洗手洗手,來喝碗湯。”一碗熱騰騰的西洋菜排骨湯擺在我面前,“太燙,涼一會兒。”她囑咐著。
湯上面泛著油花,用勺子切斷相鄰兩個油花的邊緣,它們就會融到一起,形成一個更大一點兒的油泡。還沒等我讓一個大泡統一湯面的時候,姥姥就會說:“別攪了,可以喝啦。”湯里的排骨,燉得很爛,骨頭被抽掉只剩肉,西洋菜水嫩清香,一碗湯下去,整個人都暖了起來。
這是我在冬天里,會回想的溫暖記憶之一。姥姥廚藝精湛,會在家里弄小點心、熬湯、發明新菜式,只要我營養充足身體健康,她就高興。
姥姥當了一輩子的語文老師,生活體面,優雅驕傲。她教我打牌,也一定要寓教于樂,例如“釣魚”,手中若有牌可與牌池中的牌湊成整十,便可吃掉那張牌,最后計算總分,這讓我學會了一百以內的加減法。晚上跟她睡覺,倘若我睡不著,她提議數數,她數單數,我數雙數,看誰先出錯。我討厭上幼兒園,中班干脆休學一年,姥姥也愣是在這一年里,教會我拼音和書寫,常用字也認了大半。
“太無聊了,我們來學個習吧。”姥姥就是這樣的人,不讓光陰虛度,每一天都要有用。她一直追求優秀,對學生和兒女都要求嚴格,也常跟姥爺黑臉,但對我這個長孫女尤為溺愛,像是把攢了大半輩子的柔情都施展到了我身上。于是對我來說,完成練習之后的吃吃喝喝,便成了最大的期待。蓮藕排骨湯、玉米馬蹄瘦肉湯、淮山枸杞燉雞湯……姥姥廚房的魔力,滋養了體弱多病的我。
后來姥爺生病只能靠透析維生,有6年時間,姥姥堅毅地照顧他。其間她自己被類風濕折磨,肩頸疼痛,也照樣做家務煮飯。閑坐下來,她就靠在紅木沙發椅背上,雙手側平舉,抓住椅背拉伸。她說,人老了筋骨萎縮,可能現在就是在萎縮才這么痛,要與它對拉!后來她的類風濕也好了,不知道是針灸膏藥起了作用,還是她的拉伸起了作用。姥爺去世之后,她每天做操、拉伸、對墻打乒乓球,見到我便拍著胸脯得意地說:“姥姥還是保持著158cm!沒有縮!”
可能她有一部分性格,通過食物傳給了我。要強、自尊、不服氣,外界的壓力不足為患,總可以想到辦法解決。
她努力地使自己生活充實,晨練、烹飪、斷舍離,盡力避免問題產生。
不過終究有她解決不了的事。去年她正意氣風發地住在大舅家幫忙料理家務,突然得了帶狀皰疹,落個后遺癥神經痛。曠日持久的肋間疼痛折磨著她,饒是她有鍛煉的底子,也是個80歲的老人了。她又不肯遵醫囑吃止痛藥,怕傷肝腎,眾人勸說均無果。
一開始大家還會認真地安慰,但是后來啊,大家就覺得沒有那么嚴重了。姥姥實在太靈敏,即便疼,她還是清醒又機智。大舅在客廳嘟囔一句“體育頻道是哪個臺”,躺在臥室的姥姥馬上高聲報出“25”。我們在客廳聊什么八卦,她在臥室里支著耳朵聽,不一會兒就起來加入討論,聲如洪鐘,斬釘截鐵。所以我們覺得她就是需要轉移注意力,需要操別人的心,如果大家都躺倒她就會堅強地戰斗了。
我經常去看她,她見到我就會眼前一亮,忙著招呼我洗手吃東西,瞬間忘記疼痛。我向她匯報工作,陪她聊天,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她青少年時代熠熠生輝,說來也是演過白毛女的女同學,是站在舞臺上被四鄉八里趕來的村民圍觀的,別提多光榮!她桃李滿天下,她年年評先進,而這一切,都坍縮成眼前這個白發蒼蒼的老人。
想到自己成長的經歷,我意識到這可能是家族遺傳。那般驕傲,被生活扇了耳光要不遺余力地打回去,有說想通就想通的果斷。
她拉著我的手,求助般地說:“姥姥沒用了啊。”“姥姥,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們看了看云,日光高懸,云白天青。“我教你煲湯吧。”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