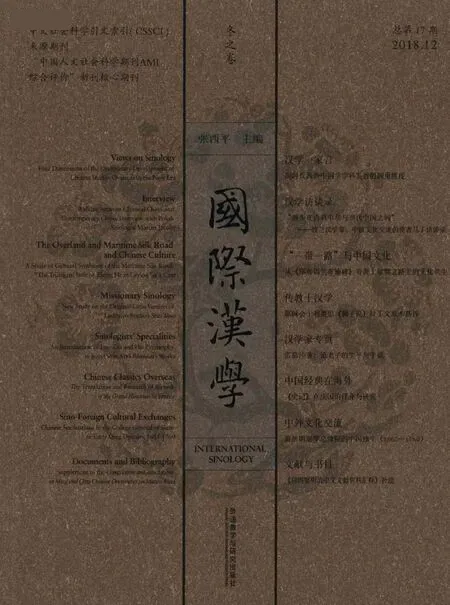編后記: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料新進展
“史學就是史料學”,傅斯年這句話一時成為史學界之宗風,史家奉行不輟,這樣的學術目標反映了史學的科學追求,當時傅斯年提出的背景,如王爾敏先生所說,“顯然它是反映時代思潮的一個信仰,這個命義的廣大背景,是民國初年以來的思潮主流泛科學主義”。后現代史學揭示出任何歷史都是由史家所撰寫,任何史料都是由史家所解釋,而史家之立場、價值判斷自然會影響其對史料的判斷。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就是這一史觀的說明。如果說“史學就是史料學”所代表的科學主義傾向會使歷史研究走向機械式的史料堆積,喪失對歷史整體和本質的把握,那么,后現代史學將歷史的解釋推向語言的表達,最終使歷史消失在個人語言和文字的分析之中,也同樣會使歷史研究迷失方向。
歷史作為人類活動的記載,既反映了人類活動的真實過程,所謂“六經皆史”是也,同時也表達了史家之追求,這是歷史二重性。如英國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所說,史學家“一邊塑造事實以適應解釋,一邊又塑造解釋以適應事實。要說哪一件重,哪一件輕是很不可能的”。
《國際漢學》自創刊以來,以漢學史研究為主旨,歷史研究是其基本的特色,通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宗教史、國別漢學史、中國典籍翻譯史、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影響史,來揭示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流播以及與各種文化的相遇與交融。
由于海外漢學史研究在史料上涉及雙邊性和多邊性,史料收集與文獻翻譯整理成為漢學研究的基礎。本刊一直將原始文獻的翻譯和整理作為重要特色,各類外文文獻的翻譯一直是我們的傳統,這與國內絕大多數學術期刊不刊登譯文完全不同。本期從法文翻譯的法國來華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書信、法國首位漢學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的《論老子的生平與學說》都是首次公布其中譯文及學術價值,而白晉以中文寫下的《易學外篇》長期藏于梵蒂岡圖書館,這次點校整理發表定會引起學界重視。特別是本期以五萬余字的篇幅刊出湯開建先生的《〈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補遺》,史料涉及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所代表的西學在整個東亞的傳播和影響,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具有重要價值。
在全球化的時代,單一的歷史史料必須放在文明互動的歷史脈絡中加以分析和考察。藏在斯里蘭卡的《鄭和錫蘭布施碑》,中外學術界多有研究,但萬明的研究視野更為開闊,把這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文獻放在大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從而得出新的結論,這也是歷史學家賦予歷史事實新的價值的體現。
本卷開篇在“漢學一家言”中所刊出的青年學者吳原元的《新時代海外中國學學科發展的四重維度》一文,更是揭示出海外漢學史(中國學史)研究的復雜性,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者不僅要有駕馭兩種甚至多種語言歷史文獻的能力,還要具有多種文化視野與學術修養,立足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展開學術對話與交流,這是對學者思想能力的挑戰。
宗教學家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說過一句名言,只懂得一種宗教的人,其實什么宗教都不懂。我們將其擴展,可以說只在中國學術范圍內研究中國文化,其實無法揭示出中華文化的本質和特征,海外漢學史研究的意義正在于此。但這樣的研究需要堅實的歷史研究和深刻的思想維度,歷史學的這兩個維度必須時刻銘記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