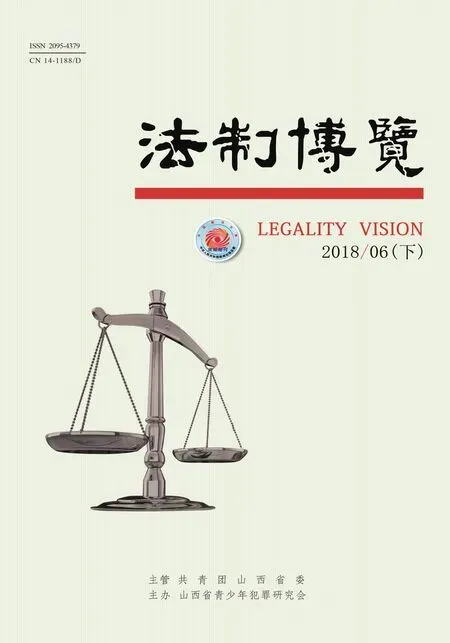職務侵占罪的客觀行為如何認定
——以一起案例為視角
張文娟
衢州市人民檢察院,浙江 衢州 324000
一、案情簡介
朱某系某房開公司售樓部營業員。2017年7月某日,朱某在本公司售樓部與徐某夫妻簽訂了《商品房認購協議》,徐某夫妻繳納了5萬元購房定金。后朱某為騙取徐某夫妻首期購房款,于7月下旬私刻了本公司公章和財務專用章一枚,偽造了收款收據兩張(面值為4萬元和150.9848萬元),并用撿來的林某身份證在工商銀行開設賬戶。2017年8月某日,朱某以交納首付款和簽署正式購房合同為由將徐某夫婦騙至售樓部,簽署了私刻公章的《商品房買賣合同》。被害人徐某當日將154.9848萬元匯入朱某提供的工商銀行林某賬戶,朱某出具了偽造的收款收據兩張。后朱某將154.9848萬元取現揮霍一空。
二、分歧意見
對于朱某的行為如何認定,存在兩種分歧:
(一)朱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朱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偽造公章、偽造賬戶、騙取他人財物,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朱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
朱某身為售樓部業務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用私刻公章、偽造賬戶發票的手段,將單位財務占為己有,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
三、本文評析
本文同意第二種觀點。朱某的行為應按職務侵占罪處理。
(一)本案主體適格
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對本罪主體理解,一般認為這里的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人員是指非國有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人員,國有企業、公司的人員不構成本罪主體。①本案中朱某系某房開公司售樓部業務員其不屬于國有企業、公司人員,其主體身份符合職務侵占罪所要求的主體資格。
(二)朱某職務侵占罪客觀行為的認定
1.朱某的行為侵犯了房開公司的財物所有權
職務侵占罪的客體,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財務所有權。該罪的犯罪對象,是單位所有的各種財物,包括有體物和無體物;已在單位控制中的財物和應歸單位收入的財物。被害人毛某在2017年電匯入朱某提供的工商銀行“林某”帳戶的154.9848萬元,是房開公司應得收入。匯入“林某”帳戶的154.9848萬元系受害人毛某的購房款,房開公司在收到購房款后有義務向毛某提供住房,因此匯入“林某”帳戶的154.9848萬元應歸房開公司的收入。
2.職務侵占罪中非法占有的手段應作擴大解釋
職務侵占罪中的職務,從語言學角度講指,“工作中所規定擔任的事情”②,侵占行為,按照刑法271條解釋是指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位己有”。
有學者認為《刑法》271條在職務侵占的罪狀中只規定了非法占有的己有行為,而未規定其他行為,因而只能將非法占有理解為純粹的侵占,而不包括盜竊、詐騙等其他方法。③這樣解釋的結果是,對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竊取、騙取本單位財物的行為,只能認定為盜竊,詐騙罪。那么本案中,朱某利用其房開公司工作人員的身份,采用虛構事實、偽造公章、帳戶的行為,騙取他人財物只能構成合同詐騙罪。
事實上,《刑法》271條第1款并未作這種將“將代為保管的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限制解釋。因為緊接著272條第2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貪污罪定罪處罰。而貪污罪的客觀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因而,《刑法》271條第1款規定的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也應包括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單位財產的行為。從立法角度上看,修訂后的1997年刑法,縮小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因而過去屬于貪污罪的那部分行為有必要從貪污罪中分離出去,歸入職務侵占罪中。貪污的手段也必然會成為侵占的手段。④
綜上,我們認為職務侵占罪的侵占方式有:
①侵吞,刑法271條第1款的限制性解釋,即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自己合法占有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
②竊取,即通常所說的“監守自盜”的行為。如倉庫保管員竊取自己所保管的財物的行為。
③騙取,指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辦法,非法占有公司、企業財物的行為。
④其他手段,指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采用侵吞、竊取、騙取以外的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的行為。如與他人惡意串通利用合同侵占本單位財物等。
在本案中朱某通過虛構事實、偽造公章、帳戶的行為,騙取了本應屬于房開公司住房款的被害人毛某所繳納的154.9848萬元人民幣。朱某的這種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用詐騙方式取得單位財產的行為是上述職務侵占罪侵占方式的第三種,可以認定為職務侵占罪。⑤
3.“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含義闡述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構成職務侵占罪的必要條件,因此有必要對其做出一定解釋。國內不少學者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解釋為,“行為人利用自己在管理本單位經營、生產過程中所進行的領導、指導、監督的職權。”⑥國內通用的教科書上也做了類似的解釋,“這里的職務上的便利,是指本人的職權范圍內,或因執行職務而產生的主管、經手、管理本單位財物的便利。”⑦這樣的理解就將利用勞務上的便利侵占本單位財物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從職務侵占罪主體中排除掉了,從而縮小了職務侵占罪主體的范圍。
在趙秉志先生主編的《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中談到,“只有根據刑法規定的主體情況,才能正確認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究竟是否包括利用勞務上的便利”。⑧《刑法》271條第1款明確規定了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人員”,而非將其僅僅限定為從事公務的人員如董事、經理等人,那么從事勞務的職工也應是職務侵占罪的主體。其實無論公務還是勞務,都屬于職務的范圍。而這些非國企單位中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利用公務之便實施的犯罪還是利用勞務之便實施的犯罪,都對公司本身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因此沒有理由不將利用勞務實施的犯罪納入職務侵占罪所懲治的范疇,既然如此,職務侵占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應同時包括利用公務上的便利和利用勞務上的便利。
而本案中的朱某,實際上也是利用了其在勞務上的便利。作為房開公司的業務員,朱某不可能擁有對本單位財物擁有“領導、指導、監督”的權力,他只能利用勞務上的關系,將徐某夫妻騙至公司售樓部,利用印有私刻公章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騙取本應屬于公司財物的售樓款。
(三)定“職務侵占罪”的缺憾
在本案中朱某僅僅侵占了房開公司的應有房款154.9848萬元,定職務侵占罪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朱某最后獲刑十年。問題是如果朱某利用職務的便利多次騙取業主付給房開公司的房款,數額特別巨大,達數百萬元。如果在定職務侵占,將面臨罪刑不相稱,因為職務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15年,而合同詐騙最高為無期徒刑。這樣以來對竊取、騙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的行為以職務侵占罪論處會導致與盜竊罪、詐騙罪等罪刑的不均衡。
對法律與現實的彌合,只能寄希望于立法者的真知灼見了。
[ 注 釋 ]
①問題是如國有汽車公司售票員、國有企業中的售貨員等利用自己經手單位貨物或貸款的便利條件而侵占本單位財物的,由于其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一般身份,而不能定貪污罪.而按照上述對職務侵占罪主體的一般理解,其又不是非國有企業工作人員,似乎又不能按職務侵占定罪.實際上這種行為是其利用勞務之便實施的侵占行為,是符合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的,應定職務侵占罪.理由如下:刑法271條(職務侵占罪)第1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貪污罪中的“利用職務便利”的內涵與外延均不相同.職務侵占罪中的“利用職務便利”既包括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也包括利用勞務上的便利.而后者僅指利用公務上的便利.因此對于上述國有公司、企業或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勞務而非公務的人員利用勞務上的便利侵占本單位財物的,應定職務侵占罪.對于職務侵占罪主體更詳細的法理闡述,可參閱,陳興良:《刑法疏議》[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443-445).張明楷先生也同樣認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中并未從事公務的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可以成為職務侵占罪的行為主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746.
②《現代漢語大辭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483.
③張翔飛.論職務侵占罪的幾個問題[J].現代法學,1997(4).
④有學者指出,“如果說侵占行為不包括竊取、騙取等其他手段,那么對公司、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來說,侵占本單位財物定貪污罪,竊取、騙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的則定其他罪,這不但與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的貪污罪犯罪構成相背離,也違反了定罪原則的一般性,對非國家工作人員來說也是這樣。”郭立新,黃明儒主編.刑法分則適用典型疑難問題新解新釋[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410.
⑤在高銘暄主編的《刑法》教科書中,也有和本文類似的觀點,“關于侵占單位財物的手段,法條并未作明確規定.應說明的是,本罪名所有‘侵占’一詞與《刑法》270條侵占罪中的的侵占一詞,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含義.后者是狹義的,即僅指非法占有本人業已合法持有的財物:而前者是廣義的,即非法占有的意思,并不以合法持有為前提.侵占手段包括多種:利用職務之便竊取財物;以涂改賬目、偽造單據等方法騙取財物;因執行職務而經手財物,應上交的不上交,加以侵吞,等等.”高銘暄主編.刑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23.
⑥張翔飛.論職務侵占罪的幾個問題[J].現代法學,1997(4).
⑦高銘暄主編.刑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23.
⑧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六集)[M].北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