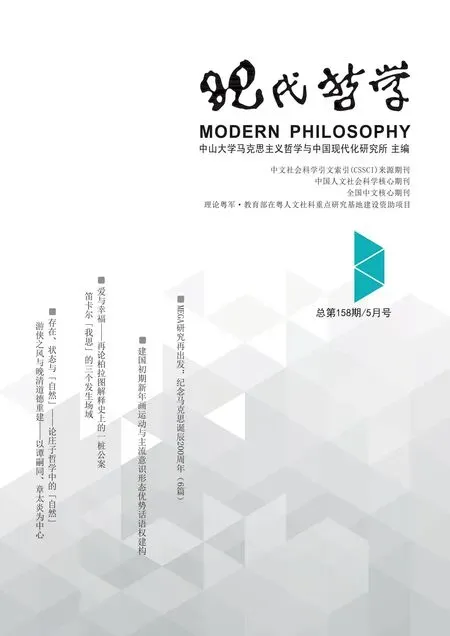論“實在與反阻”的意義
——從狄爾泰與舍勒關于實在性問題的共識與爭論出發
王嘉新
自近代哲學以降,實在性問題(Realit?tsproblem)就是知識論中最為核心且棘手的問題。用胡塞爾的術語表達,在自然態度下,人們不言自明地默認異己的實物以及外部世界的實在性。然而,一旦進入哲學的理論反思中,外部世界的實在性馬上就會變成最為令人疑惑的問題。這一疑難被康德不無夸張地稱作“哲學和普遍人類理性的丑聞”*康德說:“唯心論盡可以就形而上學的根本目的而言仍然被看作是無辜的(事實上它并非如此),然而哲學和人類普遍理性的丑聞依然存在,即不得不僅僅在信念上假定在我們之外的物(我們畢竟從他們那里為我們的內感官獲得了認識的全部材料)的實在,并且,如果有人忽然想到要懷疑這種實在,我們沒有任何足夠的證據能夠反駁他。”([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B XXXIX ,第27頁。譯文略有改動。)。不過,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這個“丑聞”的確促使人們持續地對實在性問題進行反思與研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語哲學中,伴隨著心理學和生理學研究的深入,哲學家們不斷嘗試給這一問題新的哲學解答。*例如,青年時代的海德格爾在1911年曾撰寫名為《近現代哲學中的實在性問題》(Das Realit?tsproblem in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的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綜述。在這篇文章中,海德格爾引述了哲學家奧斯瓦爾特·屈爾佩(O.Külpe)的話:“實在性問題位于……未來那種哲學的臨界處。”([德]海德格爾:《早期著作》,張柯、馬小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5頁。)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狄爾泰對于外部世界實在性的反思。狄爾泰從其生命哲學的基本立場出發,以當時最新的生理心理學研究成果為基礎,論證了實在性在生命體驗中的起源,試圖把關于實在性的討論從笛卡爾主義傳統下對理智活動的單一強調中解放出來。更進一步,狄爾泰的這一理論嘗試對現象學重新理解實在性的努力產生了巨大影響。馬克斯·舍勒首先意識到狄爾泰這一工作的巨大意義,并且在其晚期的手稿《唯心論與實在論》中,對狄爾泰的思考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和回應。舍勒早年的哲學生涯與狄爾泰密不可分。在1895-1896年間,舍勒在柏林密集地參加了狄爾泰的講座。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通過對狄爾泰的批評與反思,舍勒才真正獲得通達其晚期重要概念“實在”的論述能力。下文將首先展示狄爾泰和舍勒的相同之處與分歧。基于此,舍勒晚期的“實在”概念才能被理解。只有理解了這里的“實在”概念,我們才能有根據地主張,舍勒晚期思考蘊含著一種以實在性理論為內容的“基礎存在論”,以及在什么意義上舍勒關于實在的學說潛在地構成了海德格爾版本的基礎存在論的競爭對手。*賽普指出,一方面舍勒和海德格爾的共同策略是指出過去的“唯心論和實在論”之爭背后忽視的問題,另一方面舍勒并不同意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對他的批評,因而《唯心論與實在論》一文包含著回應海德格爾的此在存在論的意圖。根本上說,舍勒的“基礎存在論”的核心概念是“生命”,并不預設被遺忘了的“存在問題”,或者說并不預設某種存在者與存在之間的解釋學循環。(H. R. Sepp, über die Grenze. Prolegomena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Transkulturellen, Nordhausen: Traugott Bautz 2014, S. 209.) 同時參閱:[捷克]漢斯·萊納·塞普:《阻力與操心——舍勒對海德格爾的回應以及一種新此在現象學可能性》,張柯譯,《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一、狄爾泰的立場
狄爾泰關于外部世界實在性的思考,集中體現在他于1890年撰寫的長文《如何解決我們對于外部世界實在性的信念的起源及其合理性的問題》中。顯而易見,狄爾泰對實在性的討論并不指向實在性一般,而是明確地把對外部世界實在性的信念作為研究對象。在康德那里,只是訴諸于信念來辯護實在性本身就意味著人類理性的某種失敗。在狄爾泰這里,解決實在性問題的思路轉換為:對外部世界實在性的論證,既無需貶斥信念,也無需尋求信念之外的理性功能,對實在性的辯護恰恰在于尋找這種信念本身的根據。在狄爾泰看來,信念并不意味著非理性的,相反,信念本身有其在人類意識經驗中的合理性根據。
在這篇長文中,狄爾泰首先批評了當時的普遍的思維定式,即把“實在和真實僅僅理解為服務于理性功能的概念程式”(die Realit?t oder Wirklichkeit nur begriffsm?βige Formeln für Verstandesfunktionen)*W. Dilthey, Beitr?ge zur L?sung der Frage vom Ursprung unseres Glaubens an die Realit?t der Auβenwelt und seinem Rech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V, Teubner: Leipzig/Berlin 1924, S. 92, 94. (以下凡引《狄爾泰全集》,均僅給出該全集的簡稱“GS ”、卷數和頁碼。)。這里,狄爾泰的對話者是赫爾曼·馮·赫爾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后者認為,外部世界的實在性應該被還原為感覺材料之間的某種思想關聯(gedanklicher Zusammenhang),并且這種思想關聯(Denkzusammenhang)應當從自然科學的經驗研究中獲得理解。對于赫爾姆霍茨來說,這里的“思想”(Denken)無異于根據因果律(Kausalgesetz)發生的無意識的推導(unbewusste Schlüsse)。這種因果律,作為外部世界實在性的根本保證,在赫爾姆霍茨看來應表現為一種先天給定的超驗法則。狄爾泰對赫爾姆霍茨的這一觀點并不滿意,因為這種超驗法則與思想的推導聯系在一起,有其自身無法剝離的理智主義預設。在狄爾泰看來,赫爾姆霍茨在晚年偶有提及的意愿沖動(Willensimpuls)才是突破外部世界實在性問題的關鍵所在。與赫爾姆霍茨相反,狄爾泰不尋求通過建立感覺材料和思想之間的關聯,解釋外部世界的實在性,而是試圖通過分析感覺材料與意愿的內在聯系,揭示我們對外部世界信念的來源。在這點上,狄爾泰面對的首先是笛卡爾主義,或者說理智主義傳統的強勢地位:“自笛卡爾以來,大多數的解釋者認為,意愿既不能壓制感覺材料,也不能凸顯感覺材料,更不能掌控感覺材料。這些解釋者們以感覺材料的這個特點為根據,認定并且在理論上踐行了感覺材料并不依賴于意愿這一觀點。”*Ibid., S. 95.對此,狄爾泰并未直接予以否定,而是指出:基于對感覺材料不依賴于意愿的堅持,而忽視或者否認感覺材料和意愿的根本性關聯,會使人們錯失理解實在性信念的根本要素的機會。針對這種理智主義的成見,狄爾泰寫到:“我不從思想關聯出發,而是從在沖動、意愿和情緒中被給予的生命整體出發,解釋人對外部世界的信念。”*Ibid., S. 95.
這里,狄爾泰很明顯地展示了他的知識論立場與他對生命整體的研究綱領之間的深刻關聯。與理智主義進路純粹關注作為功能性的思想不同,狄爾泰試圖在人的生命的體驗(Erleben)中尋找實在性的起源。而且,邏輯與思想本身只有在“在體驗中敞開的生命”(das im Erlebnis sich erschlieβenden Leben)中才能得到理解。與此相應,狄爾泰主張必須充分發掘了感覺(Empfindung)的認識論價值,才能恰當解答實在性問題。對于狄爾泰來說,實在性問題不單純是思想的問題,而是生命本身的問題。*Vgl. H-U. Lessing, Wilhelm Dilthey. Eine Einführung, UTB: Stuttgart 2011, S. 65.
問題是,實在性是如何在體驗當中產生的?狄爾泰認為,對于實在性的信念首先必定預設了人的內在(Innensein)和外在(Auβensein)之分。這一區分無需通過意識的某種功能實現的,其本身就是意識的性質。在他看來,對于這一性質的進一步解釋要回到人的反阻經驗(Widerstandserfahrung)。這種經驗產生于意愿的兩種不可分割的狀態:第一種狀態是意識中的意愿的沖動,第二種狀態是對這種沖動的抑制(Hemmung)。這兩種狀態盡管不可分離,但是在狄爾泰看來,他們之間的關系是非對稱的,而且是間接的。
首先,意愿的沖動是自發從內在而生的,狄爾泰把它稱作“意向”(Intention)。狄爾泰認為意愿的沖動可以回溯到沖動的集合(das Bündel von Trieben)中。因此,認識主體就是憑其意愿的沖動驅動意向的個體,而對于這個意愿的抑制隨即產生,并且伴隨著與之無法分離的情緒體驗。在這個機制之下,意愿的兩種狀態是不對稱的依存關系。在狄爾泰看來,對于外部世界實在性的信念,恰好在于通過對意向的抑阻產生的主體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實在性關聯。
其次,意愿的沖動和對意向的抑阻從功能的角度來看,必須通過感覺材料的中介。狄爾泰認為,“在沖動的意識和對意向的阻礙的意識之間的中間環節,這個中間環節存在于按壓感覺那里,并且總是在那里。因此,我們對于外部世界的意識只是經過中介的。人們不應該通過任何夸張的方式試圖輕松地解釋對于外部世界的信念,諸如訴諸于意愿的直接的反阻經驗,或者索性訴諸于對直接給予存在的心理學虛構”*W. Dilthey, GS Bd. V, S. 103. 加黑強調出自筆者。。這里,狄爾泰首先把反阻經驗落實在了具體的按壓感受(Druckempfindung)上,這與當時經驗科學的進展是密不可分的。*狄爾泰積極參與了當時心理學的研究。在關于心理學和人類學講座中,狄爾泰梳理了當時實驗心理學的關于按壓感受的研究。(Vgl. W. Dilthey, GS Bd. XXI, S. 211-215.)對于按壓感受作為中間環節的強調,目的在于批評那種把外部世界存在當作是直接未經中介的被給予的觀點。在狄爾泰看來,這種觀點既無法在哲學上得到論證,也無法在經驗科學的研究中獲得支持。基于對按壓感的哲學反思,狄爾泰把反阻經驗理解為意識中的可被經驗之物。人和外部世界的實在性關聯,就存在于感覺聯結(Empfindungsaggregat)中。這種意識感覺聯結就是意愿沖動和反阻體驗的聯結點。因此,狄爾泰把我們對于外部世界的直接的實在性信念還原到了意識中的間接的反阻體驗上。
二、舍勒對狄爾泰的繼承與批評
上文對狄爾泰關于實在性論證的勾勒,為我們提供了進入馬克斯·舍勒的實在性理論的基本語境。舍勒早年受狄爾泰生命哲學影響頗深。具體到外部世界實在性的問題,我們更能清楚地發現這兩位思想家之間的思想關聯。在舍勒看來,狄爾泰本身置身在一個偉大的豐富的思想傳統中,這個傳統主張“實在是在反阻的體驗當中給出自身的”*M. Scheler, Sp?te Schriften, Gesamte Werke, Bd. IX, Bouvier: Bonn 1995, S. 210. (以下凡引《馬克斯·舍勒全集》,均僅給出該全集的簡稱“GW”、卷數和頁碼。)。狄爾泰的巨大貢獻在于,他重新使這一思想在當時的哲學討論中復活,并且在生理心理學知識的進展中使之更為豐富。而舍勒晚期著作中對實在性問題的回答,正是建立在對狄爾泰思考的繼承與批評之上。舍勒繼承了狄爾泰開辟的這一問題的基本論域,以及從反阻體驗出發尋找關于外部世界實在性根源的基本路徑,但是批評狄爾泰對于反阻體驗的哲學解讀。正如漢斯-萊納·賽普的概括,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在反阻體驗中經驗到的實在物,或者說實在本身,是經由意識而獲得原初把握的,還是有其本己的體驗路徑?”*H. R. Sepp, über die Grenze. Prolegomena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Transkulturellen, Nordhausen: Traugott Bautz, 2014, S. 204.在舍勒看來,盡管狄爾泰正確地強調了本能型的行為在實在聯結產生中的原初作用,但是他卻同時把這種行為限制在本能意識(Triebbewusstsein)的范圍之內。狄爾泰把實在經驗歸于意識,總是相對于意識來解釋對象的實在性。在《唯心論與實在論》一文中,舍勒正是圍繞這一基本點展開對狄爾泰理論的批評。
與狄爾泰一致,舍勒也把“實在”定位在沖動(Impuls)和反阻的關系中,然而舍勒并不接受狄爾泰把這一關系理解為經由“感覺材料”中介的關系,而是力圖復活在狄爾泰那里被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的“直接性的反阻經驗”。舍勒明確地表示:“這種被狄爾泰拒絕的‘直接的反阻經驗’恰恰是持存著的。”*M. Scheler, GW Bd. IX, S. 212.舍勒通過對狄爾泰“按壓感覺”(Druckempfindung)概念的批評來闡釋直接性的反阻關系。狄爾泰把“按壓感覺”看作是位于指尖的一個死的感受。在舍勒看來,如果按壓感覺僅僅是在皮膚表面的一個死的感官體驗,那么它實際上同狄爾泰想要通過這一按壓感覺建立起來的反阻經驗是矛盾的。如果我們把按壓感覺理解成為和具體的感官聯系在一起的一種感官感覺,那么按壓感中的反阻體驗就不可能形成對出于本能系統(Triebsystem)的意向的阻礙。在舍勒看來,與其說反阻體驗來自于作為感官感覺的按壓感,毋寧說所謂的“按壓感”是反阻經驗的伴隨現象(如果它不是一種錯誤的概念虛構的話),前者因后者而可能,兩者應該嚴格地加以區分。這里,舍勒當然需要解釋為什么反阻體驗完全不同于按壓感。
舍勒的這一論斷依賴于當時最新的生理心理學對負重或者拖拽體驗的研究結論。人們發現在負重或者拖拽的行為中,人的用力體驗的強度和肌肉的緊張體驗的強度并沒有嚴格的相關性。顯然,反阻體驗關聯的是人的力量投入的感受(Krafteinsatz des emfindenen), 而肌肉緊張程度則是感官感覺。舍勒認為,這一經驗研究揭示的反阻體驗和感官感覺的區別,足以證明狄爾泰把人的反阻體驗等同于作為感官感受的按壓感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M. Scheler, GW Bd. IX, S. 212.。舍勒批評道:“真正的反阻體驗絕不是表面的感官經驗,而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我們的沖動(Dr?ngen)與追求(Streben)的經驗。”*Ibid., S. 210-212.因此,舍勒把反阻經驗界定為體驗中居于核心的一個特別緯度。反阻體驗的這種中心性特征,也使得我們不能把它和周圍的感官體驗混同起來,無論這種感官體驗是緊張感還是按壓感。在這個意義上,力量投入實際上并不是由按壓感所帶來的。相反,感覺著的人作為力量投入著的源泉奠基著所有在各種感官中呈現的感覺(Empfindungen)。
上文呈現了舍勒就當時的生理心理學語境對狄爾泰的批評。下面需要從純粹概念分析的角度再次去審視舍勒對狄爾泰的“按壓體驗”(Drucksempfindung)的批評。在狄爾泰看來,運動沖動(Bewegungsimpuls)是由意愿或者意志行為驅動的。僅僅有意愿帶來的沖動當然不足以產生反阻體驗,反阻體驗還需要對意愿沖動的阻礙(Hemmung)。狄爾泰認為這個阻礙是我們一種有意識的經驗,并且“按壓體驗的組件”必須作為阻礙意識的前件同時被給予,才能保證沖動和阻礙在體驗中一體兩面地同時出現。狄爾泰根據不同感官把感覺區分為各種感覺類型,例如皮膚上的觸感、皮下組織的感覺、肌肉收縮的感覺、關節處的運動感覺等。狄爾泰把反阻感覺(Widerstandsempfindung)當作這些感覺的高一級概念來使用。反阻體驗發生在整個沖動體驗的系統中,因而與之相應的類按壓體驗(Druckhafte)也無差別地在各種感覺類型當中存有。*Vgl. W. Dilthey, GS Bd. V, S. 103-104.在狄爾泰看來,在內關節的部位存在的不僅僅是運動感受,還有按壓的感受。
與狄爾泰不同,舍勒想要闡明的是“無中介的反阻體驗”。盡管我們看到狄爾泰肯定了反阻體驗作為所有感覺類型不可或缺的一個面向,但是在舍勒看來,狄爾泰的反思恰恰遮蔽了真正的無中介的反阻經驗。舍勒認為,這種無中介的反阻關聯的是力量投入(Kraftseinsatz)。如同負重或者拖拽的例子中所證明的,力量投入并不能定位在任何具體的感受組件中,因而對力量投入的反阻也不包括在四周的感受中。舍勒的核心命題是:在狄爾泰那里反阻經驗并不是真正的反阻體驗,反阻經驗被理解為意識中的屬于感覺組件的內容,而這并不是原初綻出的反阻體驗。
舍勒觀點的革命性在于翻轉了反阻與意識的關系。舍勒認為綻出的反阻是意識產生的基礎,正是在反阻中的返照(Reflex)使得意識成為可能,而不是相反。因此,想要真正抓住沖動與反阻這一對構成實在(Realsein)的關系,必須把研究從意識概念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相反,在狄爾泰那里,意識不僅作為我們思考實在問題的出發點,還是我們反思實在問題的邊界。狄爾泰在《描述與分析的心理學概念》一文中寫道:“意識無法反觀自身的背后,思想處在[和意識]的關系中,思想從意識中來并且依賴意識,這個關系是我們永遠無法丟棄的前提。”*W. Dilthey, GS Bd. V, S. 194.狄爾泰意圖在意識中找到外部世界實在性的根據,因為哲學地反思實在性作為思想本身受到意識概念的限制,舍勒則篤定實在性問題的解決一定在意識之外,實在性早在意識的內在經驗成形之前就已經起作用了。
舍勒看來,投入(Anstrengend) 、發力(Krafteinsetzend)是從本能的生命中心生發的。從生命中心出發的本能沖動當然不會在意識領域缺席。然而,在舍勒看來,狄爾泰把它錯認為意愿(Wollen)。在狄爾泰那里,保證主體外部世界存在的反阻關聯的是有意識的意愿。意愿、感覺與沖動構成了生命結構的三重奏。舍勒從根本上質疑狄爾泰的三重生命結構的合理性。舍勒認為這里狄爾泰又犯了一個錯誤:“狄爾泰把反阻稱為意愿的經驗,明顯他想到的更多是有意識的意愿的中心,后者不是屬于我們任意的自發的生命中心的本能沖動,而是來自意識中心的意愿。”*M. Scheler, GW Bd. IX, S. 214.從舍勒的觀點看,實在性的要素是從對活躍自發的、完全非任意的生命沖動的反阻中產生的,而不是從對有意識的意愿的反阻中產生的。*M. Scheler, GW Bd. IX, S. 214.更進一步,狄爾泰認為,意愿關系到的是任意的運動沖動。對外部世界實在性的意識來自于對這種運動沖動的阻礙(Hemmung)。那種對非任意的運動關聯到的是本能沖動,對后者的討論出現在狄爾泰思考的邊緣地帶。而狄爾泰分析的中心點在于認知主體的實在性經驗。在腳注的位置,狄爾泰提到,在生命的初始階段,運動當然不是任意的。胚胎階段的生命進行的是某種非任意的活動;在新生兒那里,我們也能看到出于饑渴的非任意的吮吸運動。我們可以說在生命初始階段的非任意運動中起作用的是一些特殊的本能沖動,后者和有意識的意愿是不同的。遺憾的是,狄爾泰并沒有進一步地對這兩種本能沖動和意愿沖動做出進一步研究。恰好在這點,舍勒指出,三重生命結構中的沖動和意愿的區別在嬰兒的吮吸運動中坍塌了。
舍勒的立場是,本能和意愿的關系應該被顛倒過來。在狄爾泰意義上的,意愿沖動作為驅動力是有問題的。如果說在成熟的意識主體那里,運動意向是從意愿沖動而來,那么毋寧說這種“意愿沖動早已和本能沖動融為一體了”*Ibid., S. 215.。在舍勒看來,精神的意愿來自于對本能沖動的阻礙或者去阻礙。意愿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精神活動的結果,他是通過對本能沖動的否定產生的。因此,作為一種高級的精神性活動,意愿不是永續性的,而是不常有的行為(Seltenheitsakt);與此相反,我們的實在性體驗卻是持續著的。因此,對于意愿的反阻在舍勒看來是無法理解的。反阻作為實在性體驗之錨只能扎在本能沖動和外在世界的環節中。我們最基本的實在信念的根基不在于個人意愿的層面,而在于更深的人的非任意的本能生命的層面。
從整體上說,舍勒認為狄爾泰把實在性問題單面地理解為“外部世界的實在問題”也是不合適的。在舍勒看來,外部世界不能被理解為實在物的總體。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在外部世界中呈現出來的對象都是實在的,外部世界同樣包括有許多非實在對象,如彩虹、影子、鏡像等。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考慮內在世界的心靈對象問題,不能認為意識中發生過的內容和心靈的存在沒有實在性。舍勒關心的“實在”(Realsein)不僅是外在對象的實在性,同時也包含我們心靈世界的實在性。在舍勒看來,“實在”不只關涉到外部環境的實在,而是關于所有可能的存在領域的實在,實在是我們全部經驗的根本性緯度。*Ibid., S. 215.因而,舍勒認為,狄爾泰并沒有把實在性問題的核心意義揭示出來,具體地說,狄爾泰錯失的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整體性的“實在性”。
換句話說,舍勒關心的是實在性的“實在”,而狄爾泰追問的毋寧說是主體的“實-有”(Realit?t-Haben)問題。在舍勒看來,實有屬于一個特別的場域(Sph?re),即在意識中被給予的外部世界;而“實在”無差別地在所有場域以及可能的場域中在,即“實在一般”(Realit?t überhaupt)。*“場域”概念的分析和整理,參見M. Frings, Life time: Max Scheler’s Philosophy of Time, Springer: Dordrecht/London, 2011, p. 80.后者作為舍勒的根本關注點,顯然與狄爾泰通過反阻經驗來解釋的“實-有”不同。“實在”毋寧說是前意識的直接的生命沖動與世界關聯。反阻在舍勒看來是整體性(Totalit?t)的反阻,是世界的反阻(Weltwiderstand)。*M. Scheler, GW Bd. V, S. 217-18.
三、小結及進一步思考
基于上面對狄爾泰與舍勒關于實在性爭論的觀察,我們目前可以得到兩個階段性的結論。第一,就實在性問題而言,狄爾泰和舍勒的分歧在于,作為實在性來源的反阻體驗如何被理解,它究竟源自處于中心的生命沖動,還是源自經由感覺過程中介的意愿生命。第二,狄爾泰和舍勒共同之處在于,兩者都強調實在性來源于人的生命進程,并且都從“沖動”和“反阻”這對概念出發來解釋人的實在性信念。無論狄爾泰對外部世界實在性的研究,還是舍勒對實在性一般的強調,其共同立場都是拒絕把實在理解為(康德式的)純粹理智的設定活動(Setzungst?tigkeit)。二者的共同立場可以成為我們反思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于實在性問題理解的重要的參照。對狄爾泰和舍勒關于實在性爭論的再考察,旨在重新把作為實在性的反阻重新帶入到現象學語境中。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我們看到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都把經驗的這一緯度排除在現象學的考察之外。
拋開胡塞爾不談,舍勒這里提出的“實在”概念,可以被看作在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之外定義人的“實際性”(Faktizit?t)的獨立嘗試。如果可以被理解為基礎存在論,舍勒的實在性理論將是海德格爾基礎存在論的強勁對手。海德格爾顯然沒有理解舍勒“作為實在的反阻”對于意識和生命的成在(Werden)的核心意義。海德格爾在1925年的講課稿《時間概念史導論》中處理了狄爾泰-舍勒對于反阻經驗的討論,然而并不充分。海德格爾并不否認反阻現象本身的經驗的一部分,但是認為反阻現象顯然不是最原初的生命結構的實際性。他認為,恰恰是在“煩”和“意蘊”中展開的世界的世界性使得反阻成為可能;而舍勒那里的反阻或者說意愿行為,關聯的是一種在手物。*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Sommersemester 1925), GA 20,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302-303.顯然在海德格爾的思路里,在手的(Vorhandensein)之所以能夠作為在手的凸顯出來,是在更原初的上手(Zuhandensein)的在場的基礎上,或者說在“煩與意蘊”敞開的世界性中。因此,反阻充其量是個“現象特征(ph?nomenaler Charakter), 這一特征是以世界為前提的”*Ibid., S. 304.。實在物以及外部世界的實在性應當還原到此在在世存在的世界性。后來,在《存在與時間》第§43節海德格爾幾乎重復了他在《時間概念史導論》的觀點。
就海德格爾的觀點,有三點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一,上手的概念與在手概念的區分,以及海德格爾由此試圖建立起來的實踐對于理論的優先性,本身存在著很大的理論爭議。*例如,蒲浩思認為,海德格爾的“上手”概念以及與此相應的此在的“巡視著的操心”(die umsichtige Besorge)實質上是一種帶有實踐性質的意向活動,巡視(Umsicht)本身包含著最小的無可逃脫的認識性要素(盡管還不是判斷式的認識活動),因此,“上手”概念表達的純粹的實踐性是不可能的。(參見 G. Prauss, Erkennen und Handeln i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 1977, S. 27-41.)在本文的論域中,如果上手本身就包含著無可消除的認識要素,那么“上手”又如何能夠支持由此而來的對反阻概念拒斥。第二,即便海德格爾是對的,人類此在與世界的關系就其最原初處確實是上手的關系,即一種原初的目的導向的“實踐”活動,那么在舍勒的視角下,上手關系也必然地包含著“沖動和反阻”這一最基本層次。舍勒也完全可以同意,我們在工具性的“實踐”活動中,“上手”先于由于目的未實現產生(意向未獲得充實)的“對象化”活動,先于由此而產生的帶有反思性特征的對象意識,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上手”可以先于反阻。第三,最令人吃驚的是,在海德格爾的眼里,舍勒和狄爾泰的觀點并無不同,舍勒用來解釋實在性的“反阻”經驗是和對象性活動和判斷活動聯系在一起的。顯然,海德格爾對于我們上文展示的舍勒與狄爾泰的根本分歧缺乏了解。因而,他對狄爾泰和舍勒觀點的捆綁式處理很難站得住腳。本文已經充分地展示了,舍勒的“實在”概念試圖揭示的是意識中的前意識的世界關聯。在實在的基礎上,意識才通過反身的關系產生,意識毋寧說是“由世界的反阻的受難的結果”(Das Erleiden des Widerstandes der Welt)*M. Scheler, GW Bd. IX, S. 43. 對這一點的詳細闡述,參見M. Frings, Life time: Max Scheler’s Philosophy of Time, Springer: Dordrecht/London 2011, p. 82.。因此,“沖動-反阻”是先于對象性關系(主體-客體關系)的,因而絕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在手”的關系。海德格爾批評舍勒把反阻經驗作為原始生命和世界之間的關系是基于其完全錯誤的“生物學傾向”(biologische Orientierung)*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Sommersemester 1925), GA 20,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305.。恐怕這也包含著他對舍勒哲學的深刻誤解。舍勒對實在的思考顯然是借助生物學研究成果的哲學思考,但不是仰生物學鼻息的。“實在”與“反阻”的關系是生物學無法定義的。正是通過辯護這些生物學無法理解的生命經驗,舍勒為一種基于“實在”概念的基礎存在論贏得了可能。舍勒對于人類此在“實際性”的界定恢復了費希特對于“實在即反阻”的觀點,其討論的實在高于具體科學對于實在的局部討論,并且為后者提供了存在論基礎;同時這種討論本身又處于和具體科學(感官生理學)的關聯中,無法脫離后者被理解。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