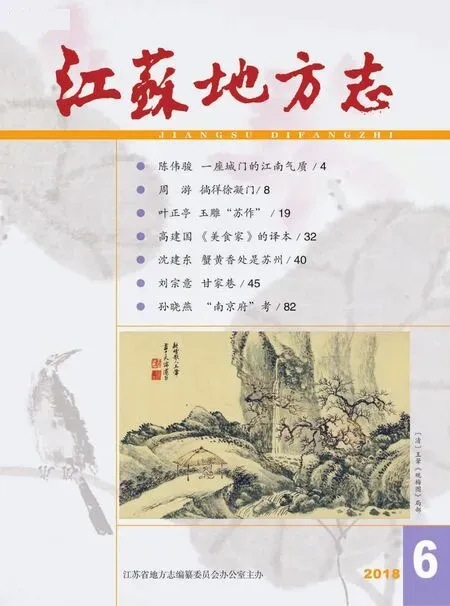一座城門的江南氣質(zhì)
◎ 陳偉駿
古時,蘇州東南面的城門外,澤國一片,水田無垠,宋人云“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過于蘇州”。蘇州水田的最美處在城東,土壤肥沃,水流暢通,適宜種植稻谷和水生作物,曰“葑田”。通向城門的一條清溪,兩旁遍植葑草,故曰“葑溪”。因此,那城門也就隨了此物,叫了“葑門”。用植物來冠一座城門之名,在蘇州是唯一的,全國也不多見。
“葑”是叫法之一,這種大型水生植物也被稱作“雕胡”,但歷史上叫得最響的名稱是“菰”,菰米位列古代六谷之中,也曾經(jīng)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主糧。
一粒菰米相當于四、五粒稻谷的長度。細長,黑亮。此物優(yōu)點明顯:黏而不膩,爽而不干,清香可口。但缺點也十分明顯:容易脫落、吹不得、碰不得,更致命的是菰的株體容易被黑粉菌感染。而一染病,植株就膨脹便結(jié)不了實。菰的這種特性令蘇州的先民們痛苦不堪。漸漸地,菰米也成了“雞肋”。
黑粉菌進入菰草的主莖,使其膨脹,但假如孢子粉不多,黑粉菌也黑不了主莖,也無太大的傷害,反倒使得主莖變得細嫩、潔白。剝開后,可以看到形狀和竹筍差不多的一段株體,故有人將之戲稱為茭筍,俗稱茭白。原來本該是防病才對,哪料到,后來大家卻巴望菰草得病越多越好,因為發(fā)病率越高,茭白長得越多。漸漸地,菰米的收成反倒變得不是十分重要了。
西晉時,吳人張翰在京城洛陽擔任高官,但因害怕卷入“宮斗”,托詞思念家鄉(xiāng)菰菜、莼羹和鱸魚的滋味,棄官回鄉(xiāng)。“純鱸之思”經(jīng)歷代的文人傳頌而成了舉國皆知的典故,入了成語詞典。菰、莼、鱸三種食材也因此享譽九州。
由此可見,蘇州歷史上將一城門冠以“葑”,也就是“菰”,也是恰如其分的。這既是對周邊環(huán)境的寫實,同時也是兼顧了歷史文化。
但令人驚訝的是,老蘇州壓根兒就不把這座城門叫作“葑門”,而把它喚作“?門”。
“?”這個字雖然在大多數(shù)字典和字庫中都已經(jīng)找不到了,但這個物種卻仍然活生生地生活在長江里,那就是江豚。
江豚喜歡“躍水”,經(jīng)常成群躍出水面,亮灰色,非常顯眼。
古時,無論是長江岸線還是東海岸線離開蘇州城都比今天近得多,又沒有閘口的阻攔,每年時令一到,成群的“?”,也就是江豚,會追隨著咸淡水洄游魚群,從長江口經(jīng)吳淞江隨濤而入,環(huán)游于葑門附近,其體形碩大,騰躍于水面上,形成蘇城一景。
看過此場面的人均言終生難忘。“?門”一詞從此不脛而走,經(jīng)世世代代蘇州人的口口相傳,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了“葑門”。
“?門”處于幾路水道的匯集之處,又是內(nèi)城水道的出口之一,有機物和浮游生物富集,是各種魚類的匯集之處。
順吳淞江而來的江船、海船入不了內(nèi)河的都在“?門”泊岸,漸漸地“?門”外形成了一個商賈集散地,最后成了一個永久性的“?門橫街”。江、海、湖、河各類鮮貨紛紛涌入,橫街的魚市特別有名。每天一大清早,吳地特有的魚娘們扎著三角包頭,系著作裙,帶著秤和竹器家什,紛紛到魚行批貨。她們肩擔臂挎,散入葑門內(nèi)的大街小巷,把那些魚腥蝦蟹販賣到千家萬戶,讓人們體會到自己所居住的是一座不愁魚吃的東方水城。
話又說回來,書面語“葑門”也是恰如其分的,城門外黃天蕩以及往東往南的廣大區(qū)域均為湖塘和水田。此地域盛產(chǎn)慈姑、荸薺、藕、菱、芡實、水芹和茭白七種水菜,莼菜主要產(chǎn)自洞庭東山,船載而來,匯入后,“水八鮮”就齊了。葑門橫街歷來是蘇州最大的水生蔬菜集散地。水生蔬菜的深加工也在此進行,比如:慈姑片的氽制和芡實的剝制。不僅如此,糯、粳、秈三類稻米以及它們的深加工制成品,蜜糕、湯團、粽子、粢飯、糖粥、酒釀、炒米粉等琳瑯滿目地陳列在米行和糕團點里。此時,用草字頭的“葑門”才是最恰當?shù)摹?/p>
古人云:“佳品盡為吳地有,一年四季賣時新。”蘇州人歷來講究“吃時鮮”,葑門橫街菜市為此提供了可靠的物質(zhì)保障。
葑門既是生活的,也是文化的。舊時,每年農(nóng)歷六月二十四,蘇州人傾城而出,涌往葑門外。據(jù)顧祿的《清嘉錄》云:“是日為荷花生日。舊俗,畫船簫鼓,競于葑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沈朝初的詞《憶江南》的描述更絕,沒提葑門一字,但懂的人心里一看便明白,“蘇州好,廿四賞荷花。黃石彩橋停畫鹢,水晶冰窨劈西瓜。痛飲對流霞。”因為詞中的黃石橋就是葑溪自湖口從東往西入城前的第一座石質(zhì)圓洞門拱橋。一路前行,依次經(jīng)過紅板橋、徐公橋、安利橋。這些橋和兩岸的民居以及它們在水中的倒影,和著霧氣和炊煙,伴隨著沿岸茶館兼書場傳出的琵琶和弦子聲,伴著拖得很長卻委婉優(yōu)雅的吳儂軟語唱詞“窈啊窕啊淑女杜啊十啊娘啊啊啊……”混合著市場里人聲鼎沸的嘈雜聲,點綴著幾條悠悠慢行的櫓搖船,被金黃的晨曦一染,構成了一幅典型的江南水鄉(xiāng)的生動畫卷。
葑溪過了安利橋后入了水城門,入城后的葑溪,除了并入內(nèi)城河外,分成了三路水,并各有其名,但叫人拍案叫絕的是無論哪一路水畔居住的人都習慣把自己門前的那路水稱為“葑溪”,都以“葑”為榮。當然,道理是有的,這幾路水均會合于葑門水城門下并和城外的葑溪一脈相承。
三路水中的其中西北路一脈水沿盛家?guī)Лh(huán)繞到天賜莊。
清末,西風東漸,美國傳教士們在當?shù)赜凶R之士的點撥下,選中天賜莊興辦了一批學校和醫(yī)院。如:東吳大學、東吳附中、景海女師、景海附小、博習醫(yī)院和博習護校。不知不覺中,葑門地界成了傳統(tǒng)中國文化和西洋現(xiàn)代文明交流融通的前沿地帶。
之所以有人會建議把學校集中設立在葑門天賜莊,是因為天賜莊在文星閣方塔附近,塔中供文星像,塔前建桂香殿,能助人文之勝。據(jù)歷史記載,自塔建立后,果然人才輩出,科甲蟬聯(lián)。清代康熙、雍正年間,葑門大街彭定求、彭啟豐祖孫“會狀連中”震動全城,兩人均連中會元和狀元。人們把彭家能破“富貴不過三代”的魔咒和離彭宅不遠的文星閣聯(lián)系起來,認為這是“文星鐘靈之驗”。彭家也被譽為“葑門第一家”。然而,與其說是文星顯靈,還不如說是彭家的家風使然。彭家對子孫讀書、做人的要求極為嚴格。彭家的門風和他們所辦的彭氏小學影響了整個葑門地區(qū)的民風。
東吳大學、景海女子師范學校、博習衛(wèi)生學校加上早年蘇蘇女學的女學生們也是葑門大街小巷的一道風景,她們是新派江南女子的代言人。蘇州女子的美本來就是有口皆碑的,要不然曹雪芹在《紅樓夢》里不會把林黛玉設計為蘇州人,曹雪芹眼光犀利,對人的刻畫入木三分,在中路葑溪旁蘇州織造府生活過一段時期的他對蘇州女子的神韻是了如指掌的。但葑門內(nèi)青年女學生所展現(xiàn)的那種新時代蘇州女性氣息不同于傳統(tǒng)的美,顯得更為獨特。因為縱然女子都可以被贊為天生麗質(zhì),但從羞羞答答的小家碧玉跨越到氣定神寧的大家閨秀,要靠氣質(zhì)和氣度。俗話說,“腹有詩書氣自華”,而“養(yǎng)氣”只有靠讀書。
葑門的南路水流入了南園區(qū)域,南園和其相對應的北園是古代蘇州城市規(guī)劃的留白,全國少見。用意是留著一大片城墻內(nèi)的地用作農(nóng)耕,一旦被圍城,城內(nèi)糧食和蔬菜尚可以自給。葑溪的水滋潤了南園的田地。南園是讓人們不出城就能品味到江南田園風光的好地方。每年春天看南園的菜花是市民踏春的傳統(tǒng)項目。這一特色使得士大夫書卷氣濃厚的葑門之雅帶上了三分俗。但這城內(nèi)的江南田野風光被唐寅用一幅《葑田行犢圖》一渲染,這份俗又成了雅。竟然一時間大家覺得像圖中的牧牛翁一樣,坐著一頭水牛,慢慢地行走在濃蔭如蓋的古松下,徜徉在秧苗初綠、亮如明鏡的水田邊,聽著此起彼伏的蛙鳴聲,是一種酥到骨頭里的輕松。誰敢說蘇州城內(nèi)可以沒有江南田園風光呢?南園葑溪畔的大云庵是唐寅、文徵明、祝枝山、沈周等文人讀書作畫之地,哪料到最后也改了俗名“結(jié)草庵”。今天當年的庵院已經(jīng)蕩然無存,但庵前的七孔石橋和一棵全城最大的白皮松仍然矗立在原地。
葑溪之水也是方圓幾里范圍內(nèi)私家園林之魂。各園以傍上葑字為榮,有葑溪草堂、葑溪別墅等。葑溪別墅為蘇州織造府的官邸,曹雪芹兒時曾久住。但葑溪最靚麗的一筆是讓滄浪亭借了它最后一段寬闊水面構筑了園外之景。借助葑溪,滄浪亭成了全城唯一的不入園,您就能賞到景色的江南古典園林。一般園林筑起高墻把滿園春色關起來,最多一枝紅杏出墻式的露艷。但滄浪亭卻反其道而行之,筑高阜、建復廊,前者讓全園的點睛之作“滄浪亭”的飛檐翹角和一片由櫸、樸、樟、松等合抱古木所組成的樹林凸顯在園外可以欣賞得到的位置,后者讓單調(diào)的圍墻變成了一連串花窗,窗后也透著隱隱約約的花木。復廊下臨水的石砌駁岸全部用了天然黃石和太湖石混搭構筑。復廊的東西兩首分別建有一座臨水亭、一座面水軒。還沒有入園,您一站到葑溪邊,園林之美如一幅水彩畫就已經(jīng)呈現(xiàn)在您眼前了。
葑門的城樓和城門已分別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被拆除了。但“葑門”作為地名概念還是被廣泛運用于蘇城的各種地名標識中,更為重要的是它已經(jīng)根植于蘇州人的心坎里,化作一種精神財富,在他們的心里“葑”字某種意義上代表著這座城市物產(chǎn)的豐饒和文化的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