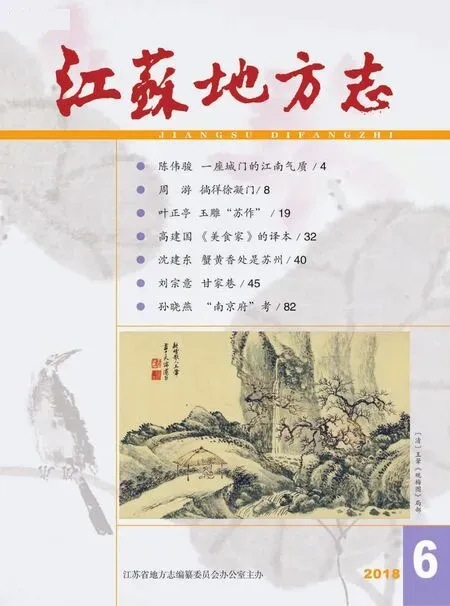重刊《〔嘉靖〕興化縣志》序
◎ 陳麟德
方志即詳細記載一地的地理、沿革、風俗、教育、物產、人物、名勝、古跡以及詩文、著作等,備載古今各種事物的百科全書。如興化為楚將昭陽采邑,舊隸海陵,至楊吳置縣,乃遷、固之作及《國策》《五代史》所未載,而邑乘載之。倘無邑乘,后人焉知昭陽之食采,楊吳之置縣!明代隆慶首輔李春芳,《明史》雖有傳,然《辭源》《辭海》至今未列李春芳條目,故未能名滿天下,耳熟能詳。甚至連皇皇大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均將其誤載為福建興化,可見方志不可須臾或缺。
歷朝歷代無不以修史纂志為要務,前人的經驗之談是:“修史之難,無出于志。”(鄭樵《通志·總序》)難就難在收集資料殊為不易,資料的豐富翔實決定了方志的學術性與可信程度,編纂者還必須系載筆高手。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先生云:“志之重要,在于資料。整理成書,可供參考。曰志曰史,名稱不拘。利在厚生,即是珍寶。”厚生者即以民為本,使人民生活充裕。故博雅君子為官一方,必先入境問俗,查詢志書佳惡,久廢者則倡修之。興化陳氏五進士之一的陳以恂,康熙時宰平遙,即主修《平遙邑志》。興邑之令,若明之胡順華、歐陽東鳳,清之張可立、梁園棣皆視修志為遠大要務,不遺余力,親執其勞。編纂邑志,功莫大焉。可以“焜耀往古,昭示來茲”,“考古今之異同,鑒世道之升降”(李清《〔康熙〕興化縣志·序》);可以“知古、知今、知利、知弊”(梁園棣《〔咸豐〕重修興化縣志·敘》);可以充分發揮“資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就興化而言,宋、元方志皆不存,亦未見任何記載。明高榖《題興化邑志初稿》,詩中提及興化地理、物產、秩官、名宦、寺觀、掌故、古跡云云,可知邑志初稿之大略。“纂修承國典,編輯會民風”,“方輿稽未盡,史筆載無窮,賴爾關西裔,重來究始終”。可見高文義公曾參與其事,隱逸王均實傳中也提到《高文義公志稿》。應該說,高榖編纂之《興化邑志初稿》為發軔之作。惜乎久佚,無從得見。
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縣胡順華主修《縣志》,后稱《胡志》,為現存世最早之興化《縣志》。胡字賓甫,湖廣武陵進士,居興五年,深得民心,后升南京兵部主事。胡令敦請縉紳胡時可、諸生陸西星、贛州府致仕推官潘應詔等共襄此事,參與纂修。《胡志》仿《大明一統志》體式勉成四卷,設十六門。書中有關門目記述之后,往往附以奏疏等歷史文獻,以示足征。人物顯微兼志,其有事跡昭著于時者,必表而出之;對未蓋棺者,據事直書,不妄加品評,僅于科貢類中記其官爵,此為同時期志書中鮮有之舉。全志記述雖不盡周詳,但于明代中期之前興化基本狀況,保存了不少寶貴的歷史資料,可以說粗具輪廓,然冗、缺、訛、失在所難免。蓋因胡順華守興時,倭寇猖獗,疲于巡城、御賊、筑垣,倉促成書,約五萬字,內容過簡,以致“碌落錯陳”(歐陽東鳳《〔萬歷〕興化縣新志·序》),亟待修訂。故三十年后,歐陽東鳳編出《新志》,以示在《胡志》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耳。
興化雖為蕞爾小邑,僻處淮海一隅,然人文不乏,文苑昌隆。有明一代,竟出三宰輔:歷永、洪、宣、正、景“五朝元老”高穀,“狀元宰相”、隆慶首輔李春芳,崇禎季年次輔吳甡。豈止宰輔顯宦,文苑巨擘也應運而生。施耐庵、宗臣、陸西星、李清、李鱓、鄭板橋、劉熙載等。聯翩而至,璀璨奪目,熠熠生輝。至于賢令茂宰,造福水鄉,自宋而迄明清,代不乏人。且不必說宋代先憂后樂的范文正公,也不必說元代繼修捍海堰的詹士龍,單說明清兩代的胡順華、歐陽東鳳、劉士璟、張可立、魏源、梁園棣就璨然可觀矣。再加上邑乘纂修者不乏學苑泰斗,一代宗師,因而琳瑯滿目,蔚為大觀,為后人留下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韓愈《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竊以為,來興從政者,不妨于懸魚、瘞鹿之暇,從中吸取愛民惠政的經驗。學者論文,可目之為信史而以為據。市史志檔案辦為弘揚興化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彰顯文化興化的魅力,特點校并注釋《嘉靖興化縣志》,歷時三載,五易其稿,其力也勉,其功也鉅,付梓在邇,略陳片言,弁諸卷首,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