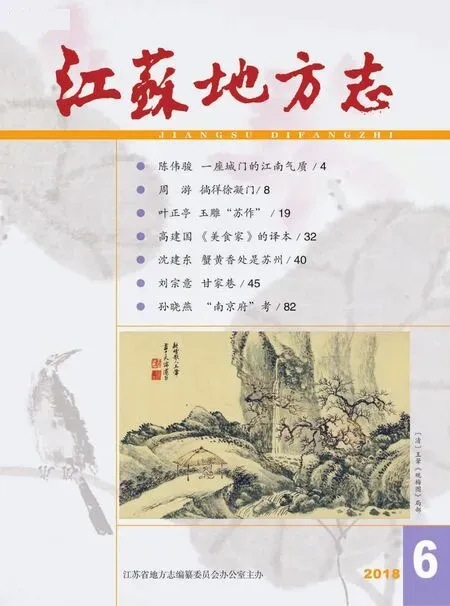常熟地方志所載相關商周故事小議
◎熊賢品
常熟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的文化較為興盛。其風景優美的虞山、巫咸墓、尚湖,一些地方志的記載中,上述兩處風景地還和一些商周故事相關,并被概括為“虞山三賢”,比如《常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詞典》記載,尚湖與姜子牙有關,“相傳商末姜尚避紂王暴政曾隱居垂釣于此而得名”,而虞山上“商周以來的名人墓冢,有商初巫咸墓、商末仲雍墓”等。但常熟地區離中原較遠,上述地方志的記載不免讓人存疑:何以一些主要活動于中原地區的商周人物,會出現在常熟地方志的記載之中,并留下一些相關傳說故事?現在就這些問題略作小議。
一、虞山
常熟城北的“虞山”,風景絕佳,又名烏目山、臥牛山,而古稱則有“海隅山”“海巫山”等,相關記載,如唐蕭德言《括地志》作“海禺山”,宋鄭虎臣《吳都文粹》:“縣依山之陽,是為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虞仲治此也。”清代徐崧、張大純《百城煙水》:“虞山,在縣治西北一里。《吳地志》《祥符圖經》并曰‘海禺’,《吳郡志》曰‘海虞’,《續志》曰‘海巫’……以為‘海禺’者,謂山臨海之隅。以為‘海虞’者,謂虞仲常隱此山。‘海巫’者,以商相巫咸與其子賢嘗居之,后葬于此。《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居’,蓋吳越時已名虞山矣。”
上述文獻都將“虞山”和“虞仲”相聯系,認為“虞山”其名源自“虞仲”。但問題在于,從虞山之名來看,首先是它有眾多別稱,并且目前還不能確定之這些名稱出現的先后順序,由此,僅僅用“虞仲”之名,來解釋“虞山”的由來,應當是不夠的。同時,經過學界多年研究,關于《史記》等記載的“太伯奔吳”一事,目前多持否定意見,一般認為所奔之地“吳”,并非今江蘇之地,“太伯奔吳”也并非直接奔襲到江蘇地區。由此,將“虞山”之名和“虞仲”相互聯系,只是一種傳說而已,并不可信。
二、巫咸墓
“巫咸”是先秦典籍中常見的人物,相關記載,如《尚書·君奭》:“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呂氏春秋·勿躬》:“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楚辭》:“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注為“巫咸,古神巫也”。《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賢。”
值得注意的是,常熟虞山還有和巫咸有關的遺址,如巫咸祠、巫咸墓、巫相崗等。據《常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詞典》記載,當地并傳說虞山北端之商相村,為巫咸父子之故里。
通過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從漢代開始,陸續出現將巫咸墓和常熟虞山相聯系的記載,如《論衡·言毒》記載巫咸“生于江南”,這里將巫咸和江南相聯系。而從《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第三》開始,則將其地理進一步明確:“虞山者,巫咸所出也……巫咸出自虞山,虞山在吳縣北,相距百五里。”此后這一說法為很多文獻所傳承,如梁《招真治碑記》:“海虞縣境有虞山,巫咸之所出也,咸居虞之小山。”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殷賢臣也……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巫賢,吳人。今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冢及巫賢冢。”北宋《祥符圖經續記》:“虞山者,巫咸所居。”南宋《吳郡志·古跡》:“虞山今為海巫山,山即巫咸之所出。海虞即常熟也。”此外,宋代常熟縣令陳映《續提名記》載:“常熟邑中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泰)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才所表上閭,其風俗之美,由可概見。”明嘉靖《常熟縣志》:“巫咸墓在虞山上,其子巫賢也葬其側。”
此外,還有關于“巫咸宅”的傳說,如清徐崧、張大純之《百城煙水》:“巫咸宅,《舊志》云:在婁縣山下。據今有人士考證,原婁縣,即昆山。昆山,只有馬鞍山,而無巫咸宅。巫咸宅當在常熟縣虞山無疑。”
據文獻記載,一些論著,如《江蘇通史·先秦卷》等都將“巫咸”作為吳人,進而,有的論著在討論商代人口流動的時候,將巫咸作為由吳越流動至中原的例證。
但是問題在于,上述文獻的記載并不一定可信。首先,關于巫咸墓的所在,我們目前很難明確。比如依據早期文獻的記載,在山西地區也有關于巫咸相關遺跡,《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巫咸山在南。”《水經注》記載鹽水(運城鹽池)西北流經巫咸山北。《大明一統志》:“巫咸頂在夏縣南五里,《隋書》名巫咸山,相傳殷巫咸曾隱此。”這就說明巫咸墓記載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而且進一步來講,縱然文獻中有山西、江蘇兩種巫咸遺跡的傳說,但是如果沒有相關的考古發現資料,還是難以確定巫咸墓記載的可靠性。其次,我們從早期的地名變遷來看,會常常發現有“地名南遷”的現象,比如在晉南地區稍早的年代有隨、鄂,而在湖北地區稍晚的年代也有隨、鄂,學者推測這應當和遷徙有關;又比如關于舜之葬地,《孟子》中明確記載為山西地區,而從《史記》開始,則與湖南地區相互聯系。又比如根據新出的一些秦簡資料,作為地名的“蒼梧”,也有一個南遷的現象。據此,我們可以發現,早期存在“地名南遷”的現象,而這也應當是從漢代開始,處于南方的常熟地區出現“巫咸墓”的背景,只是關于其具體過程,目前還難以完整復原。從這個角度而言,關于常熟地區巫咸故事,可見是一種后出演繹。前輩學者呂思勉在《先秦史》中曾指出,常熟巫咸之傳說“亦出后來附會”,我們認為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和呂先生稍有不同的是,他認為常熟地區巫咸故事的出現,是由于先秦時期吳、越南遷所致。我們則認為這一故事出現的時期,年代不會這么早,應當不早于戰國晚期,而很有可能是在戰國晚期至漢初。
三、尚湖
尚湖,據《常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詞典》記載,又名照山湖、常湖、西湖、山前湖,其中多數名稱的由來,都和地理有關。另外,目前在常熟地區的文化介紹中,都把它和姜尚聯系,將之作為文化旅游的一個重要方面,力圖通過姜尚文化符號的打造,來提升尚湖旅游。
將常熟尚湖與姜子牙相聯系,目前所見比較早的文獻,為唐代陸廣微《吳地記》:“(常熟)縣北二里有海隅山,仲雍、周章并葬山東嶺上……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回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此后這一說法得到沿用,如宋代《吳郡圖經續記》:“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去海近,或是。”《吳郡志》也有類似記載:“石寶在常熟海隅山。石寶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南宋龔明之《吳中紀聞》:“常熟虞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至清代徐崧、張大純《百城煙水》,其中對尚湖有如下記載:“長十五里,廣九里。旁邑水溢而出,亦匯于湖。虞山臨于湖上,其濱饒葭葦蒲荷,魚鳥翔躍,民居櫛比,率業魚稻。柳港映帶,景最佳勝,又名西湖,以擬余杭之西湖。或日太公嘗釣于此,故日尚湖。”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尚湖和姜尚有關的傳說,最早似出現于唐代。而這一時代相較姜尚的時期,是極為遙遠的,因此相關故事應當存疑。
文獻關于姜尚“漁釣”的故事,記載較多,如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第二》:“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圣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由此,很容易看出,在較早的姜尚“漁釣”的故事中,其故事發生地是在中原地區,而非遠離中原的吳越之地。從史料的年代角度而言,將虞山和姜尚相聯系的“姜尚漁釣尚湖”之說,是晚出之說,因此可靠性應存疑。
綜上,我們通過文獻梳理,發現“虞山三賢”的故事,大都出于后世的附會,其實并不可靠。不過,常熟本身有悠久的歷史文化,而虞山、尚湖的風景也都歷代口耳相傳,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不會由此而受到影響。本文也希望在指出“虞山三賢”故事一些不足時,也更能由此為當地相關部門提供一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