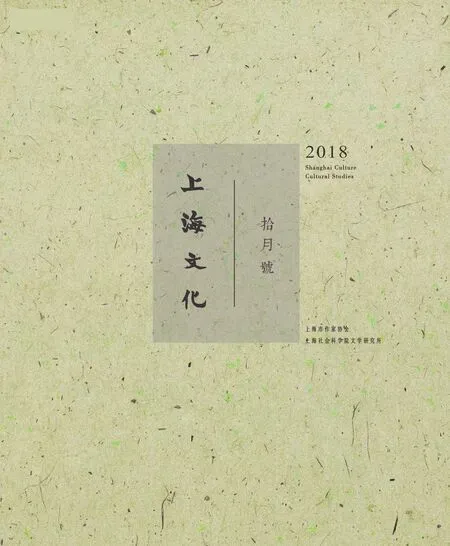當代藝術:關心人的境況,提升人的境界
——馬軻訪談錄
馬 軻 王春杰 夏 存(執筆)
夏存(以下簡稱夏):馬軻老師,非常高興采訪到您。現在在中國當代畫壇上,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來之前看了許多有關您的評論和報道,其中有的評論甚至把您稱為是“畫家中的畫家”“一個繪畫文化夾縫里的沉思者與冒險者”,所以首先我們想請您談談,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評論,以及您是如何評價自己的?
馬軻(以下簡稱馬):一個畫家畫了半輩子,能夠被人們認可,這總歸是一件好事,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認識自己。我覺得我的畫被認可,是因為我在具象和抽象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表達了真實的自己。我的繪畫創作處在一種積極的不穩定狀態。繪畫說到底既使我痛苦,也讓我歡樂。當我俯就既有的概念、常規和慣性,俯就權力和利益時,繪畫往往令我痛苦不堪。當我擺脫種種束縛,在稍縱即逝的形象與當下建立某種隱喻的關聯——也就是繪畫成就的瞬間,我會歡欣鼓舞,躊躇滿志,繪畫能夠使我感受到人性的尊嚴與個體的崇高,恍若重生一般。對這種瞬間的渴望是我繪畫的內在動力。
王春杰(以下簡稱王):說得好。記得去年(2017年)你們在北京舉辦《涉險的快感》三人展,展覽“序言”中的一句話,給我印象很深,說您是“關乎‘立人’與‘自由’的現實命題”“渴望沖決自我、走向個體精神與繪畫本體的雙重自覺”,聽您剛才這么說,對這段話的理解就更深入了。您的作品體現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包含了后現代的許多思考,很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聽說在國外反響也非常好。最近有去國外開辦展覽的計劃嗎?
馬:今年4月我在德國慕尼黑做了個展,這一陣子也有其他的畫廊來我這里,看以后有沒有合作的意向。不過都還在籌劃中。我在德國的個展作品都是新完成的。有意思的是,在那里居然還碰到許多“粉絲”。這讓我很詫異,他們喜歡我的畫,使我很感動;不過反過來想想也是一樣的,我們有時候對德國乃至歐洲的藝術家也如數家珍,甚至比德國人自己還清楚。
王:這也說明真正的藝術不受時空的限制,它有一種超越地域、文化甚至時代的穿透力、震撼力。這些年您在繪畫上的追求,是否也與這樣的目標有關?
馬:當然我希望自己的藝術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文化的產物,也希望得到更多的認可。但在平時的繪畫實踐中,我也沒想這么多,這么遠。從我個人而言,首先是繪畫所表現出來的一種人的狀態和境界。我喜歡唐代詩人韋莊的詩“大羅天上月朦朧,騎馬上虛空”。詩句當年的實際含義被歷史沉淀后,留給今天的便是那種“上虛空”的境界,這是一種從束縛到自由空間,從有限到無限的人生體驗。因為虛空和天空還不一樣,是一種什么都不存在的狀態,即“無”,它看不見也摸不到,僅僅存在在意識里的空間,“上虛空”讓人感覺有一種超脫現實的釋然。這很難翻譯。我用“wandering in the sky”來替代,意思是在天空中徘徊、游蕩。這樣翻譯完全不能表現“上虛空”那種主動的空間轉換,更不能讓人體會到上了虛空以后那種超然的清澈感。繪畫如果與“上虛空”的人生體驗聯系在一起,我想也就是把繪畫當作生命來看待了。
夏:您說的繪畫與人生境界的問題,包含了當下繪畫藝術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嚴肅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當代畫的當代性究竟是什么?很明顯,生活在當代的每位畫家他們的作品并不都具有當代性,有些甚至與當代性背道而馳。
馬:是的,當代性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是更表現為當代人對于繪畫理念、繪畫本體的認知和體驗。我認為對人、對自己的認知是繪畫緣起的根本動力。繪畫作品不僅是用來看的,也促人思考,是超越日常生活的感受。對我來說,繪畫的發展就如同自己的命運,包括作為人的尊嚴和價值,人的自身的困境。繪畫的價值來源于個人存在的獨特經驗。我畫畫這么多年,對我非常好的好處就是我沒有停止對人的思考,這是我的藝術源頭。意識到繪畫的發生、發展不是表面的藝術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信息知識的問題,而更是對自身概念的破壞和重建所迸發出來的能量使然。
夏:在當前消費主義盛行、追名逐利成為時尚的情況下,您恪守繪畫的本真意義,自覺規避時尚主流,這需要勇氣,也需要毅力和識見。在您看來,藝術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是一個怎樣的關系?
馬:藝術的歷史是一個虛擬時空里建造的知識體系。但是,更真切的認知卻來自自身的經歷和生存經驗。當我們仔細回顧美術史里的每一個事件,追根到底都是當時的人變了,社會變了,藝術自然變了。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這就像手機從蘋果1到蘋果10,有了1,才有2才有3……這是一個無法簡省的過程。這個過程在西方繪畫史上是這樣的,比如我要畫一個桃子,在西方傳統的觀念里,眼前這個桃子的顏色、大小、位置都是上帝規定的,我們所要做的事就是無限接近這個規定,去模擬它,于是模仿理論、透視技術什么的都出來了。但突然有一天,有人說上帝死了,之前所有的規定都作廢了,人的束縛一下子就沒有了,高更、塞尚再也不去模擬對象,之后的立體主義藝術家就開始徹底拋棄具體形象,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繪畫觀念的大爆發,西方現代藝術就是人被解放出來的結果。當然這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面,便是由于沒有了上帝,人怎樣認識自己便成為一個問題,各種見解可謂五花八門,各行其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所說的,沒有了上帝,人可以為所欲為。于是尼采就創造了超人來接替上帝,而薩特則以存在、哈貝馬斯則以交往理性界定人。這無疑造成了人的新的困境。于是在西方現代藝術的名稱之下各種派別琳瑯滿目、各種探索層出不窮,以至于最后出現以解構現代藝術為目的的后現代藝術:統一整體不再是追求的目標,人們的欲望更加碎片化。你說它是繁榮也好,是雜蕪也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們都是人的存在境況的反映,人的概念首先發生了變化,它必然導致新的藝術形式的出現,借此表達新的藝術愿望。這也就是現代繪畫或現代藝術的邏輯所在。
王:您把人的境況的改變看作現代藝術的邏輯,這真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按照這個邏輯看今天中國當代藝術,存在的問題還很多。您覺得在今天我們應該怎樣來思考人的問題?
馬: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找回人最本真的東西。今天我們好像被過度程式化了,藝術本來是很簡單的東西,它和大自然的生命密切相關,當藝術被各種條條框框限制,被規范化以后,我們會忘記它最本來的樣子。我可以說說我的親身經歷。20世紀90年代我曾有機會去過非洲東部一個國家支教,這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叫厄立特里亞,它曾經是意大利和英國的殖民地。那個國家只有一所大學,我在那里教美術。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國,可能歐美國家的孩子十五六歲就已經游遍了全世界,但我直到二十幾歲才頭一次出國。這是一次完全不一樣的體驗。那里的文化還處在比較原始的狀態,但他們都很陽光,生活得都很自由,無拘無束,表現在藝術上,充滿熱情,散發出生命原初的蓬勃氣息。音樂在非洲人的眼里就是很自然的東西,只要有聲音響起,舞蹈就自然跟著出來。他們的舞蹈相當奔放,充滿著性的暗示和鼓舞,這是本能的東西。反觀我們所謂的文明人,盡管物質水準遠遠高于他們,但是在精神上卻顯得矯揉造作,扭扭捏捏,甚至陰暗猥瑣,丟失許多人的本真的東西。我們的文化也是這樣,越到近代,越顯得蒼白無力,特別像明清以來的文人畫,我覺得那些作品太做作,畫中滿是仙山仙水,奇花異草,是神仙的世界。文人大多媚錢媚權,缺乏理想,畫出來的東西就非常弱,看不到人的本能力量。但有意思的是,如果再往前推演,宋代的山水、唐代的人物則完全不同。再往前看看先秦的藝術,商代的藝術,完全又是另一個面貌,那時候的作品充滿力量和爆發力,非常強悍。我們的文化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文明,也是因為這種強悍的東西。所以我的畫想表現那種純粹的力量,這不僅僅是表面的形式,而且是能夠刺入人心的那種震撼。我們過去的畫就是太漂亮了,太精巧了,卻沒有關于人的純粹直接的表達。
夏:我理解您所說的太漂亮、太精巧,就是指專講究畫法技巧,以技法取勝的那種。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講技法裝飾顯然就是文勝質,就會造成整個作品很虛偽(史),不真誠不純粹,理想的狀態就是文質彬彬。您怎樣看待繪畫技法在當代藝術中的位置?您自己作畫時會考慮技法的因素嗎?
馬:繪畫作為一種視覺藝術,當然離不開技法。但作為一個畫家來講,不是你的技術,更重要的是人,是你的思想震撼了人,感動了人。技法只是表現你思想、情懷的手段。技法多了,情懷就沒有了,就像你說的是文勝質,就失去了繪畫最本質的東西。技法是可以通過反復訓練獲得的。工藝性繪畫基本上是這個邏輯,不需要思考。這就是為什么一些技法精熟、思想蒼白、游離于時代之外的畫家得不到藝術圈的認可,甚至還經常遭到質疑的原因。而思想需要激情,是一種涉險,一種創造。
王:但是我們看您的作品,您的畫常常大塊平涂形成色彩的強烈對比,畫面富有很多凹凸的肌理效果,加上構圖凝練和形象簡約,一切都顯示您的畫也包含著很高的技法。您通常在作畫之前會刻意安排這些嗎?
馬:沒有,完全沒有。這些效果都是隨機產生的,我通常會把我畫壞的地方涂掉,繼續畫新的東西,而這些筆觸或者刮刀的痕跡可能是上一遍畫的時候留下的,有時候有了新的感覺,往往反倒是不擇手段。這種“類表現性”手法往往由表達的緊迫性導致,但不管怎樣,技法在創作中一定服從于創作主體的意圖和精神,不能本末倒置。可惜今天我們的大部分美術教育還是把繪畫技法的訓練或者說一種工藝流程的思維方式放在過于重要的位置。比如剛開始學畫的時候,最講究步驟,掌握某一類的畫法。這完全是工藝品的邏輯。中國繪畫也有這樣的邏輯,皴法、筆墨、線條等,我們總是思考前人怎么畫畫,努力地學習他們。這樣的藝術更像西方文藝復興以前的藝術,它不是以發現為目的。
夏:這就涉及中國的美術教育的體制問題。學校是培養人的,但落實到教育中,卻沒有把學生從“立人”的意義上去教育,這就很難成就一個藝術家。
馬:確實是這樣。以我的經歷為例,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我從學校學了些什么?花大量的時間學習英語,學了政治經濟學,讀了研究生,學會畫各種類型的畫,但是這些都無法掩蓋我作為人的一種貧乏、簡陋。這和學了什么專業無關,我們無力建立人和人之間的新關系,在和別人交流時會無意識地迸發出那種被訓練出來的體制特色——去控制,或者取悅別人。不會溝通,只要有一種新的事物放在面前,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排斥,這種思維太可怕了。根本原因就是我們自身太脆弱,無法容納外來的沖擊,一旦這種橫向的比較有所變化,整個縱向的體系就會崩塌。在我看來這點如果沒有改變,文化還會一直這樣落后下去。
夏:說到中西文化的交流,流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認為,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不同的文化樣式,所以我們中國文化在“用”的層面學學西方還可以,但在“體”的層面上還是要堅持中國的老規矩,萬萬不可向西方學習。這不知是否與您剛才所說排斥心態有關?
馬:“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中國碰到強大的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應對策略。但我擔心這個觀念在我們現代化的過程中把最重要的“人”的現代化屏蔽了。現在我們在對外開放中物質層面的現代化發展很快,有了地鐵、高樓、網絡,但是在對“人”的認識上還遠遠沒有跟上。世界文明的發展此起彼伏,沒有一個地方的文化會永遠領先。伊拉克曾經有兩河流域的優秀文化,埃及曾經創造了人類最燦爛的文明,而以美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為主體的西方文化是今天的世界主流文化。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一勞永逸的,就好比東西方文化既是共存又是競爭的關系,仿佛人的兩只腳,是交替前行的,西方文化的昌盛逼迫東方文化也要有所超越。
王:最后,我想請您用幾句話說說您對中國當代藝術寄予怎樣的期望?
馬:我希望我的同代人里能出現大的思想家,說出我個人感覺到、意識到卻無法表達的感受。我也希望我的同行創作出令人震驚的形象,來顯示我們這一代人的尊嚴。我在歐洲看到保羅·克利(Paul Klee)的展覽,雖然我個人并不喜歡他的作品,但你看到藝術家用一生的時間來探索各種藝術的表現形式,尋找各種發展方向,完成了從傳統的視覺形象現代化轉換的使命,把人類形象思維從過去帶向創造性的未來。他早年的作品,和晚年相比能清晰地看見這條脈絡,不愧是偉大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