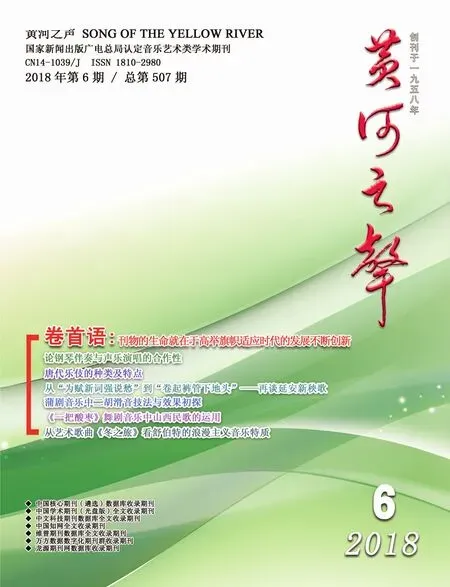論曹操的音樂觀
劉晟欣
(河南大學藝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音樂可以觸碰到人類心靈最深處的地方,是文學藝術的延伸。自古以來帝王多熱愛音樂,曹操這位是世之梟雄也對音樂頗為青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記載:“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旦達夕。”表明曹操對音樂不僅是喜愛也頗有迷戀的意味。在那個時代,不論是曹操,諸葛孔明或是周瑜,他們都表現出對音樂無限的向往,反映了漢朝的士人們受傳統儒家教育下對禮樂的重視。
音樂觀,是對音樂的理解感受產生對音樂的看法和觀點。曹操的音樂觀表現在四個方面:
曹操對樂人的態度是及其愛惜的。《三國演義》里描述曹孟德嫉賢妒能,但從他對待蔡文姬的態度上看,曹操實際上是一個及其愛惜人才的人。蔡文姬善于詩詞歌賦,通曉音律,但一生波折。她年輕時遠嫁匈奴離開故國,與親人分別,是曹操派大將將文姬接回中原才使文姬重歸故土。據《后漢書·董祀妻列傳》中記載:“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后來,蔡文姬丈夫犯了死罪,文姬前去找曹丞相求情,《后漢書》中記載“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可見,蔡文姬在曹操心中的地位之高,能在沒有任何預約的情況下公然打斷曹操宴飲,并且曹操很樂意為來的賓客介紹這位女子,在那個君君臣臣服父子子,男尊女卑的年代實屬難得。
為了推動音樂文學的發展,曹操在建安十五年于鄴城建造了一座十丈高,周圍有一百二十間殿堂的銅雀臺作為文藝創作的基地。西漢時在樂府工作的樂工有千人之多,分工明確,但到了漢哀帝時期,由于社會經濟迅速衰退,樂府被撤銷,只剩下三百余人劃歸專管雅樂的大樂署,無數藝人流落民間。曹操在鄴城建立的銅雀臺彌補了這個漏洞,廣納人才,吸收了一大批極有天賦的樂舞藝人,群星璀璨,人才濟濟,集聚鄴城。比如蔡文姬、董祀等人,他們常常隨曹操一同出征,每到之處就地采風尋找創作素材,使漢末以來的音樂文化從衰落走向復蘇。
曹操在歷史上被定義為軍事家或政治家,實際上他還是一位音樂家,有很多流傳于世的優秀作品。漢代的音樂特征是將音樂寄托與文學之中,音樂與詩歌不分家,三國魏晉開始音樂與詩歌漸漸分離,曹操的音樂造詣體現在為古曲賦詞上。《宋書·樂志》記載了漢魏留下的相和大曲歌詞十五首,曹氏家族撰詞六首,其中曹操的《步出門下行·碣石》最為有名,他以漢代民歌《隴西行》這首曲調為基礎進行填辭,從曹魏時代到東晉,該作品一直在宮廷中演唱。
對于君王來說,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想要的東西,如果沒有高度的自律精神,有時小小的興趣愛好就足以毀掉整個國家,而曹操對音樂的喜愛是極為理性的。他可以在戰爭的前一天晚上喝酒宴舞,橫槊賦詩,也可以耗巨資打造銅雀臺以養天下才俊,但是他沒有因為追求音樂藝術而耽誤國家大事。歷史上有很多追求藝術而導致國家滅亡的君主。比如唐玄宗李隆基。他才華橫溢,是大音樂家,其作《倪裳羽衣曲》流傳于世。作為君王,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開辟了開元盛世,但是盛世之后的玄宗沉迷于享樂在音樂與美色之中,導致大權旁落,安史之亂,盛世危機。曹操與之不同,他對音樂熱愛卻不沉迷,充分使用音樂有利的一面,不被音樂所操縱,而是掌控音樂。
曹操生活的時代是東漢末年,已沒有了西漢的輝煌,大漢王朝面臨崩潰。經濟決定政治,經濟政治共同作用下決定了文化的發展,音樂作為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種形式,它既是時代的產物,也表達了對時代的看法。西漢國力強盛,朝政清廉,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當時詩詞歌賦音樂的內容全是浪漫綺麗的神仙世界和對帝王歌功頌德,最著名的是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其內容無實際意義,但詞藻華麗,歌頌漢武帝的美德功績。這種現象與儒家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音樂思想休戚相關,音樂,即是政治的輔助工具。可是到了東漢末年,朝廷政務污濁不堪,社會經濟水平極度下滑,士人被宦官排擠,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們中間又開始流行一種以《老子》、《莊子》、《易經》為討論對象的玄學,加之絲綢之路使中西方文化開始進行交流,佛教從西域傳入,音樂的功能從對帝王歌功頌德為主轉向抒發自己理想為主。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了兩派截然不同的音樂觀。一派是以曹操為首的建安七子,一派是以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建安七子激昂文字,痛惜朝廷昏庸,憐惜百姓疾苦,嘆息人生不易,展現士人為天下戰斗的精神狀態,風骨遒勁。竹林七賢則消極避世醉情山水,探尋音樂本質。他們都對現實抱有極大的不滿,前者選擇了面對問題,現世是黑暗的,那我以正義抵抗邪惡,抨擊現實,直抒胸襟,抒發想要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后者則躲避世事,在竹林中縱情自我,尋找自我,拒絕功利。相比之下我更欣賞曹操的音樂觀,那種帶有儒家傳統濟世思想的音樂觀,因為任何人都希望國家太平,社會穩定,如果人們一味為了表現自己的空虛寂寞,消極的對待殘酷的世界,恐怕三國剩二虎,吳蜀競爭霸,‘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也。
曹操借助詩詞歌賦來反映社會現實,抒發抱負與救世理想,繼承了儒家音樂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音樂觀:以天下為己任。作家聶紺弩先生給《三國演義》寫前序時,說到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只是片面奸詐形象的“原因不在其它,而在這樣大的事不是說話人(明代說書人)的精神世界所能容納的,更不是世俗的精神境界所能夢見的。曹操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廣,腦子復雜,非一般聽眾能理解。‘曲高和寡’此一亦證。”
操有雄才大略,治世之心,傳承儒家士人音樂觀,以天下為己任,此乃真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