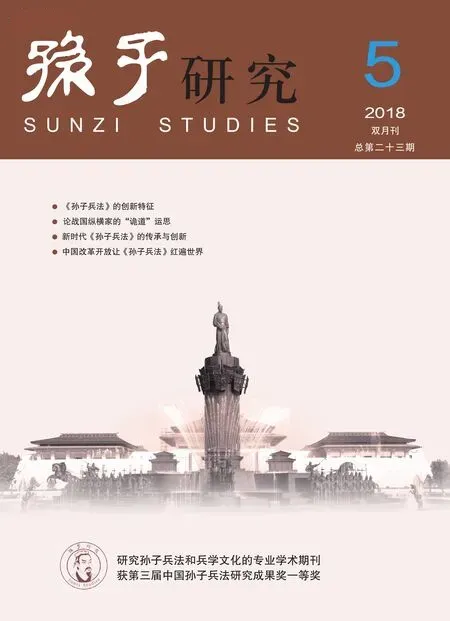王守仁兵學與心學融合脈絡探析
寧志強
近年來,國內學者致力于《孫子兵法》思想研究,探究儒家和兵家戰爭觀的交匯融合。儒家重視仁道,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歸仁,而在歷史上一味講求仁義愛民,不能結合戰場情況權變,會造成用兵的負擔,宋襄公拒絕半渡而擊,最終戰敗負傷而亡。在儒家思想作為主流文化的古代中國,詭道和仁道存在沖突,以仁愛為本的士大夫對兵家的詭道自然存有偏見,宋明兩朝武人地位不高。王陽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為明代著名哲學家,當時為“儒學第一流人物”,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牟宗三先生認為,陽明學是孟子學,其提出“致良知教”以綜括孟子所謂四端之心。另一方面,王陽明為戰功顯赫的軍事家,平定藩王之亂,出征廣西,隆慶中詔贈新建侯,予世襲伯爵。王陽明為儒學與兵學之集大成者,其人貫通詭道和仁道。《明史·王陽明傳》載:“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王守仁所著《武經七書評》,陽明學與兵學有會通。本文通過從陽明學義理出發,嘗試理清其兵儒融合的脈絡。
一、先秦儒家與兵家的沖突和融合
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歸仁,他期望當政者“須有自覺而不只是生命生物,行王道而不是任意荼毒生靈”①顏炳罡:《整合與重鑄——牟宗三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牟宗三先生認為,孔子通體是一精誠惻坦之心在流露。孔子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論語·衛靈公》)孔子并非不懂軍事,而是不愿回答,希望衛靈公不以戰爭方式解決問題。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 孔子崇尚西周以來的禮制思想。與儒家思想不同,兵家則崇尚“詭道”, 追求功利,如《孫子兵法·計篇》 “兵者,詭道也”。孫子認為,詭道是一種用兵方法,是將帥在制定戰略戰術時應該遵守的原則。對于如何實施“詭道”,孫子說:“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詭道論的核心是運用謀略讓敵方獲取虛假信息,做出錯誤判斷,行為失據,為我所用。因此,兵家的詭道論與儒家周禮思想存在沖突。
與儒家思想不同,春秋末年以后的兵家、法家繼承和發展了功利戰爭觀。①李建群、劉曉勇、魏靖宇:《人本主義與功利主義——先秦儒家與兵家戰爭觀的歧異與會通》,《理論學刊》,2013年第10期,第89~92頁。在《孫子兵法》中,孫武深入研究了“利”與戰爭關系。《計篇》提出“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計利”“因利”原則可以類比于優化設計中優化目標思想,追求優化目標即經濟費用最低。明代哲學家、軍事家王陽明對《作戰篇》的評注有“總之不欲久戰于外以疲民耗國,古善用兵之將類如此”②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可見,《作戰篇》主要分析戰爭和國家經濟利益的關聯問題。孫武指出“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作戰篇》從用兵對國家利害的影響來展開,討論戰爭投入、戰爭消耗、戰爭獲利。戰爭消耗如“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不知用兵之利者則不知用兵之害也”等。用兵之利則如“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總之,無論是投入、消耗或繳獲,都是“計利”的具體化。在《孫子兵法》中,“利”字的使用超過50次,可見其對“利”的重視程度。③④程遠:《先秦戰爭觀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兵家追求功利,而儒家崇尚仁道。中國古代理性主義戰爭觀的源頭就在于孔子和孫子這兩位思想家所奠定的人本理性和功利理性的基本原則。④在先秦時代,儒家逐漸從反對暴力到開始認可戰爭的功利價值。從“復禮”之“仁道”出發,孔子則認可戰爭,把戰爭看成維護禮制的重要手段。如《論語·憲問》記載:“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戰國中后期,諸侯兼并戰爭愈演愈烈,儒家順應統一的趨勢,全面認可戰爭及其功利價值。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 出了兵學專論《議兵》。《議兵》以為“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⑤李建群、劉曉勇、魏靖宇:《人本主義與功利主義——先秦儒家與兵家戰爭觀的歧異與會通》,《理論學刊》,2013年第10期,第89~92頁。。 荀子把戰國的軍隊分為兩類:一是“盜兵”,一是“和齊之兵”。“盜兵”包括亡國之兵;危國之兵,如魏氏之武卒;銳士之兵,如秦國之銳卒。“和齊之兵”包括王者之兵,如湯武霸王之兵,如五霸。荀子反對“盜兵”,認可“和齊之兵”。 儒家和兵家思想逐漸由紛爭趨向融合。
二、陽明學和兵學思想的融合
宋明六百年儒學,世稱“宋明理學”。宋明儒者的主要用心在于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成德之教是要成仁者,成圣人。其中心思想是心性問題,本心性體是道德實踐的可能依據。這里的本性性體在周敦頤處稱為誠體,在程顥那里稱為仁體,在陽明處稱為良知。陽明學是孟子學。《孟子·盡心》: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也,良知也。孟子之良知即為人的是非之心,亦是儒家道德實踐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據。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觀點:良知不僅是道德實踐之本體,且亦須是宇宙生化之本體。依道德的進路來接近形上學,由道德的進路對一切存在作“宇宙論的陳述”,因此宋明理學是道德與宗教的合一。①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依牟宗三先生觀點,陽明學之“良知”“心”具有知善知惡的能力。如陽明認為:“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誠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王陽明的“良知”,“心”具有道德本體的涵義,但是否僅具有道德的功能? “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如《明史》所載,明代歷史上王守仁的軍事成就較高。《王陽明全集》中王守仁將個人的軍事成就歸結到 “心”之功,據王門高弟錢德洪追記: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于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于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
這一看似平淡無奇的回答,隱含著極有歷史縱深的精神指向,埋藏著貫通古今的制勝機理。依循歷史資料提供的線索,可以探究王守仁用兵之術的精神內核。②王玨:《 “養得此心不動”:王守仁用兵之術蠡測》,《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第115~120頁。這段文字直言用兵之術在于“養心”。另一方面,王陽明在《武經七書評》中明確指出,“談兵皆曰:‘兵,詭道也,全以陰謀取勝’。”由《武經七書評》知,陽明以用兵要點在于“詭道”,又言“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可知陽明之“養心”必能促進“詭道”“ 陰謀取勝”。因此可知,陽明之“心”除具有道德本體的涵義,亦能促成權謀或機變能力。與陽明相似,《孫子兵法》尤為注重將領權謀或機變能力。《孫子兵法·九地篇》提出“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即“因敵制勝”,根據戰場具體情況靈活機動地調整部署。孫武指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孫子兵法·勢篇》)③付朝:《孫子兵法結構研究》,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版。將領依靠出奇制勝,而如何能打破定勢思維,進而形成創造性的“奇兵”?
依據心理學,定勢指先于一定的活動而指向該活動的一種心理準備狀態。當后繼學習是先前學習的同類課題,定勢能夠對后繼學習起到促進作用,當后繼學習與先前學習不是同類,或是需要靈活變通的相似任務時,定勢干擾后繼學習,對學習遷移起阻礙作用。④石巖:《高等教育心理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定勢有時會妨礙問題的解決,當熟悉一個物體某一項功能,很難看出其他功能。馬謖沒有打仗的經驗,自以為熟讀兵書,根本不聽王平的勸告,堅持要在山上扎營,一味追尋兵書原則,為定勢思維所禁錮,導致失敗結局。將領的權謀機變與心理學中打破定勢思維的能力有關。《王陽明全集》記載:
又嘗聞陳惟浚曰:“惟浚嘗聞之尚謙矣。尚謙言,昔見有待于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盡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后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
由上所述文字可知,陽明認為如果人能在自己的良知上下工夫,不被私欲蒙蔽,自然能臨事不動,應對自如,隨機權變。“不蔽于欲”即不為私欲所影響蒙蔽。依佛教觀點,私欲為執著心。告子說:生之謂性,人不免為各種主觀感性條件所阻隔,宋明儒追求成圣之道,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為要點。陽明評《孫子兵法》:“今之用兵者,只為求名避罪一個念頭先橫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趨避,敵情我獻而不為覺察,若果‘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單留一片報國丹心,將茍利國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計險厄遠近’,而‘料敵制勝’乎?”(《王陽明全集·武經七書評》)。陽明以為,將士若有“求名” “避罪”之心,不能做到“茍利國家,生死以之”,貪生避死,則可以認為“求名”“避罪”之心亦屬私欲,可使將領限于定勢。“單留一片報國丹心”即良知天理流行無礙,蕩相遣執,去除私欲,即去除主觀感性條件之影響。與陽明兵學追求的“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的境界相似,日本武士道追求一種“圓熟”境界,指在意志和行動之間,“毫無障礙,纖發悉除”,無論是世俗的經驗,還是宗教的經驗,猶如電流從電池的陽極流出,流入陰極。沒有達到圓熟境界的人,在意志和行動之間有一塊絕緣板,武士道稱為觀我、妨我。武士經過訓練消除障礙,達到電流在金屬板中自由流動,不須用力。①張萬新:《日本武士道》,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日本武士道的這種境界或受到陽明學“去除私欲”觀念的影響,以及中國儒家和佛家深刻的影響。江戶幕府成立,武士多讀書,孔孟朱王之學盛行一時,王學重知行合一,皆足勵其精神。②陳恭祿:《簡明日本史》,臺海出版社2017年版。
在陽明處,良知本體固為道德實踐之依據,而亦有無道德色彩的事功妙用。在儒家思想中,蘇秦和張儀并不符合儒家道德之價值觀,縱橫家合縱連橫事跡的實質是戰國時期各大國為拉攏他國而進行的外交、軍事斗爭,未必具有正義性。王陽明卻以“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表明良知即使對非正義舉動亦可有其妙用。《王陽明全集》記載:
其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圣人之資。后世事業文章,許多豪杰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于不善爾。”
這段文字指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 儀、秦善揣摸人情得益于良知。“故其說不能窮”則包含一層意思, 如果人能在自己的良知上下工夫,不被私欲蒙蔽,自然能臨事不動,應對自如,隨機權變。
除軍事、政治,陽明認為良知妙用亦可益于讀書做學問。《王陽明全集》記載: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門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圣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為聲利牽纏,甘心為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于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于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觀念為陽明軍事理論的特色,可將之視為心學思想在兵學領域具體呈現。追溯 “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觀念的源頭則可理清陽明兵學和心學融合的脈絡。陽明心學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四句教來概括,四句教起源于陽明晚年在天泉橋上的一次對話,當是時陽明心學思想已完善。明嘉靖丁亥(1527),在赴廣西平定思恩、田州的叛亂之前,陽明與弟子王龍溪(字汝中)、錢緒山(字德洪)在紹興天泉橋上有一段對話,遂成此后王門的一大公案,史稱“天泉證道記”。《王陽明全集》記載: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里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里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后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過,本體攻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在天泉橋上,陽明告誡務要依其四句宗旨,即“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圣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中國哲學史上歷來對“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有廣泛的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以無善無惡四字形容心體,是否背離了儒家思想的“性善論”?一代大儒牟宗三先生對這種爭議給出詮釋,“無善無惡”不是指心體不分善惡,“無善無惡”所指為“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之意。“無心為道”出自禪宗思想,即無分別心,無執著心,無所住心。在牟宗三先生看來,“無心為道”是中國儒釋道之共法,若將此“無心為道”僅判定為佛家思想,則忽視了儒家思想中無執觀念。在儒家思想中,本心性體粹然至善,能知善知惡,但現實中人終究為私欲所染,有善有惡,欲達到圣人境界只須依靠心體自身之動力,心體自然流行則能去除私欲。致良知去除私欲,此處“私欲”涵義廣泛,非單指欲望,亦包括定勢思維,當熟悉一個物體某一項功能,形成定勢思維,進而產生執著心,導致很難看出其他功能,定勢有時會妨礙問題的解決。致良知可除定勢思維,故能“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 指在意志和行動之間,“毫無障礙,纖發悉除”。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儒家崇尚仁道,兵家重視詭道,而“內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術者所追求的,故從先秦時代開始,兵家和儒家逐漸由紛爭趨向融合。王陽明為宋明儒學與兵學之集大成者之一,其所著《武經七書評》有其獨特之處,從打破定勢思維角度詮釋“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 通過從陽明學義理出發,理清其兵儒融合脈絡,對于中國兵學和儒學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