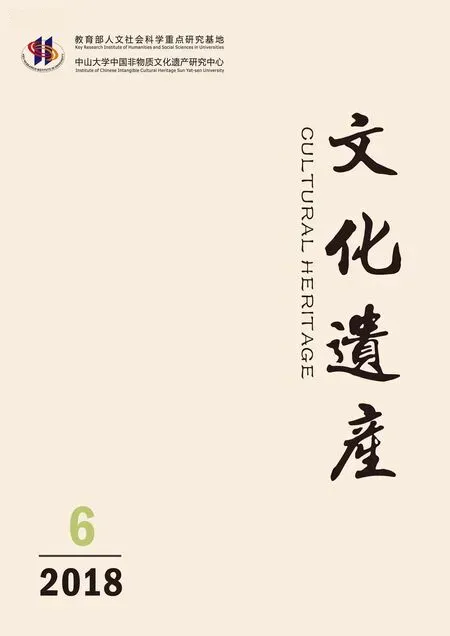非遺保護標準與文化多樣性的矛盾與調諧*
胡玉福
前言
在現代社會,“標準”“標準化”已經進入到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促進工業生產、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積極實施標準化”已經成為一項國家戰略。*呂鐵:《論技術標準化與產業標準戰略》,《中國工業經濟》2005年第7期。但在文化研究領域中,有很多研究者卻以消極或抵抗的態度看待現代標準問題,部分學者談標準而色變。尤其是面對西方近現代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文化工業”*[德]霍克海默、[德]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 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機械復制”*[德]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年。“麥當勞化”*[美]喬治·里澤:《麥當勞夢魘 社會的麥當勞化》,容冰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等大眾文化研究理論的提出,對當代的文化認知產生了深刻影響。在一些學者的觀念中,“標準化”等同于“固定化”“統一化”“刻板化”,與活態傳承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王寧宇:《“非遺”保護與現代“規范”觀之再校正——以陜西傳統建筑彩作為例的調查與思考》,《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在非遺保護、民俗旅游等領域的研究中,“標準化”與傳統文化基本上被置于對立狀態*劉志揚、更登磋:《民族旅游及其麥當勞化:白馬藏族村寨旅游的個案研究》,《文化遺產》2012年第4期。。正如王霄冰、胡玉福所總結的那樣,部分學者擔心因為標準化,“原本鮮活生動的民間文化表現形式會因此而被凝固為一種靜態的、固化的產品,越來越喪失其自由創作的個性”,并“造成文化現象的碎片化及與原本生存語境的脫離,從而違背了非遺保護最為根本的整體性和活態性原則”。*王霄冰、胡玉福:《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規范化與標準體系的建立》,《文化遺產》2017年第5期。
與學術研究形成反差的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卻一直存在著積極探索標準制定的行動。根據筆者的初步檢索,已經制定實施的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相關的地方標準、團體標準約有100余項,這些標準涉及:(1)工藝流程,如《山西刀削面制作規范》(DB14/T 1213—2016);(2)項目衍生產品標準,如《土家織錦》(DB43/T 1019-2015);(3)項目基本內容,如《蒙古族服飾 第1部分 術語》(DB15/T 506.1-2012)等,且主要集中在“傳統美術”“傳統技藝”“民俗(服飾類)”三個類別項目中。盡管相關標準是為非遺項目而定,但制定者多以質監、標準化研究從業者為主,鮮有從事非遺保護工作的人員參與,而且制定的文本受標準書寫格式的限制,活態的工藝過程被進行技術性的量化處理,從而導致標準文本大多缺乏文化內涵。
有鑒于此,本論試圖厘清學術界對于標準制定問題所存在的兩種看似互相矛盾的認識,追溯文化多樣性理念的發展,并結合現實中的標準制定實例來揭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標準化與文化多樣性二者之間既矛盾又可以調諧的關系。
一、標準化:文化多樣性的“天敵”?
2018年3月中旬,剛剛成立的天津市煎餅馃子協會提出“制定團體標準,對煎餅馃子的制作進行規范,實現標準化操作,以改變目前五花八門的現狀,恢復煎餅馃子的傳統小吃面目。”*馬曉冬:《市餐飲行業協會 成立煎餅馃子分會》,《天津日報》2018年3月17日第5版。一時間又掀起關于地方小吃標準化的討論。對報刊媒體的相關報道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各方莫衷一是,難以達成共識。總體來講在這些爭議中,既有支持的聲音,認為應該有規范性的正規標準*《山西青年報》,《煎餅馃子也該有個正規標準》2018年3月27日第10版。,可以促進天津煎餅馃子生產與經營的健康發展*馬愛平:《有了標準的煎餅馃子能走得更遠》,《科技日報》2018年6月1日第7版。;同時又有質疑者發問:“煎餅馃子應不應該有標準?”*胡宇齊:《煎餅馃子應不應該有標準?》,《北京日報》2018年3月23日第8版。標準化之后的煎餅馃子口味是否還正宗?*《新文化報》,《“標準”的煎餅馃子會是好吃的煎餅馃子嗎?》2018年3月21日第A07版。;更有人直接持否定態度,認為制定標準將會使舌尖上的體驗受到束縛*江德斌:《煎餅馃子:“標準”束縛舌尖》,《長春日報》2018年3月23日第10版。;也有一些人持中立態度,認為應對多樣性的“煎餅馃子”形態持寬容態度*《寬容看待“煎餅馃子”創新》,《滄州晚報》2018年3月21日第11版。,既保留傳統又堅持創新*《“煎餅馃子標準” 不宜固守傳統而排斥創新》,《鄂爾多斯晚報》2018年3月21日第WB11版。。盡管引起了一定的爭議,經過各方努力,《天津地方傳統名吃 制作加工技術規范 天津煎餅馃子》(T/TJCY 002-2018)(以下簡稱《煎餅馃子標準》)仍以團體標準的形式得以制定,并于2018年5月26日起正式付諸實施。*王建章:《T/TJCY 002—2018 〈天津地方傳統名吃 制作加工技術規范 天津煎餅馃子〉》,《標準生活》2018年第8期。
煎餅馃子標準制定引起的爭議并非偶然,而是近年來地方小吃、傳統飲食標準化的一個縮影。通過相關檢索可發現,湖南湘菜、陜西肉夾饃、山西刀削面、揚州炒飯、蘭州牛肉拉面等都先后制定了相關標準,且標準制定前后總會引起一番熱議。面對標準制定,為什么會有如此之爭議?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細究起來,其根源在于兩種對標準化的不同認知:標準制定者希望借助標準規范傳承秩序,對非遺制作技藝起到保護作用,這是基于非遺保護工作視角出發的對于標準化的認知;反對者則從非遺活態傳承的特點出發,認為標準的引入會從形式上將非遺項目的文化特色固定住,與促進文化多樣性的原則相悖,也不利于文化的發展,顯然,這是一種基于文化基本特征的對于標準化的認知。
標準制定的推動者一般是行業管理者、行業協會、標準化從業者、政府質監部門等主體,他們秉持的是市場秩序、質量安全等現代性的理念,從行業發展的角度希望通過制定相關標準,對混亂的市場生態進行規范,讓更多的從業者有標可依,按標作業,走文化保護的技術路線。同時,制定標準也是一個讓傳統文化生產方式走向現代化、適應市場規則的一個過程,如各地傳統小吃,面對麥當勞、肯德基等西式快餐的沖擊,生存的最大障礙即是生產和經營管理的規范化問題。事實上,標準化已成為中華小吃走向世界的一條必經之路。*程鵬:《傳統飲食制作技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準化建設研究》,載榮躍明、畢旭玲《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報告( 2018)》,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53-62頁。
對于標準制定問題持否定態度的,多為從事文化保護的工作者和文化研究的學者,他們認為文化是活態傳承的,在傳承中不斷變異,才形成了多樣性的表現形式,不能通過標準來固化。部分標準制定者有關確立“正宗”產品,保留“原生態”的提法往往成為反對者批評的焦點。比如以小吃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文化技藝所呈現出的獨特性,一旦以標準的形式加以固定,恐怕就將失去其特色。各地小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就是源于地域性飲食習慣所形成的不同風格,代表了一個地域的“地方身份(Place Identity)”*Amy B,Trubek X.The Taste of Place:A Cultural Journey into Terroi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小吃很難達成如必勝客、肯德基那樣的標準口味,如果制定一個所謂“正宗”的口味,不僅起不到規范行業的效果,反而會使這個項目所展現的文化多樣性消失。在這一層面上,認為標準化是文化多樣性或者傳統文化的“天敵”似也不為過。
那么,何為標準?何為標準化?在《標準化工作手冊》中,“標準”是指“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經協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認機構批準、共同使用的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編:《標準化工作手冊》(第2版),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04年,第451頁。“標準化”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對現實問題或潛在問題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復使用的條款的活動。”*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編:《標準化工作手冊》(第2版),第451頁。根據這一定義,我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來認識標準和標準化,首先,標準是一種共識,這種共識經過多方協商而達成,并且有一定適用范圍,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其次,標準是一種文本,其制定通過公認機構批準,具有規范性和約束性;再次,制定標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最佳秩序,即對秩序進行規范,使之合理化達到最好效果。
從這個理念出發,標準化與文化保護實際并不矛盾。將標準化引入到文化保護領域本身并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很多人對標準化懷有偏見,以固化的思維去認識標準化,而不去認真地研究標準的類型與內容,試圖改善標準的制定過程和實施辦法。這種固執己見的立場和思維方式本身,才是真正的問題之所在。
二、文化多樣性與標準化的關系
自從二戰結束以來,在追尋國際政治秩序重建的同時,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核心的國際力量也在謀求對文化的重新理解。從大的方面來講經歷了從“文明的沖突”*[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8頁。到“文明的共存”*[德]米勒:《文明的共存 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批判》,酈紅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認識到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特征。尤其是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后,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各國間的文化對話與交流,也產生了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格局。在文化交流中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往往處于弱勢地位,易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侵蝕,有面臨消失的潛在危險。在信息技術和市場化的推動下,西方文化不斷擴張,全球文化有出現單一化的趨勢。
面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潛在的弱勢文化消失和全球文化趨同化浪潮等危機,UNESCO于2001年制定了《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文化多樣性”是“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年。《宣言》是第一份有關“文化多樣性”的國際公約,正式確立文化多樣性概念、描繪文化多樣性對人類可持續發展之重要性,并在國際層面探索對文化多樣性的保障機制。這一機制也就是UNESCO于2005年制定的《保障及促進文化表現多樣性公約》(本文以下簡稱《文化多樣性公約》)。《文化多樣性公約》確認文化多樣性“指各群體和社會借以表現其文化的多種不同形式。這些表現形式在他們內部及其間傳承。”并明確了各締約國需要“根據自身的特殊情況和需求,在其境內采取措施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來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2005年。
UNESCO有關“文化多樣性”的論述和實踐,用劉非非、單世聯的話說,“既是對西方文化強勢擴張的現狀所做的一種合理反應,也是對全球文化趨同化的一種深刻擔憂。”*劉非非、單世聯:《論“文化多樣性”的中國話語》,《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從UNESCO的探索歷程來講,對“文化多樣性”的關注與對世界遺產體系的探索緊密相關。伴隨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的發展過程,保護文化遺產的理論和行動與UNESCO對“文化多樣性”的探索也不斷發展。作為人類社會的文化特征表現的“文化多樣性”被首次提出,然后作為一項理解人類文明的理念被提倡,在目前作為一項公共文化事務表現為全球普遍進行的文化遺產保護活動。*高丙中:《從文化的代表性意涵理解世界文化遺產》,《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在當下的中國已經成為政府主導、全民參與的公共文化工作,“形成廣泛參與的運動,以濃墨重彩重繪了中國的文化地圖,創造了新的歷史”。*高丙中:《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革命的終結》,《開放時代》2013年第5期。非遺保護工作正是要以政府主導的形式延續傳統文化活態傳承的生命力,以現代社會的理念保護傳統社會的文化,其目的之一即是“讓非遺走進現代生活”。因此,非遺保護工作的關鍵就是要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秩序之間的矛盾,以保證傳統的可持續發展。
2007年原文化部制定的《文化標準化中長期發展規劃2007-2020》提出“形成涉及文化領域安全、環保、質量、工藝、功能、技術、檢驗檢測、資質、等級評定、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標準體系”,以標準形式“推動文化產業的秩序化發展”“促進文化市場的規范化管理”等工作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法規全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第90-92頁。2011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十三條提出“國家鼓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的科學技術研究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方法研究”。2015年,國務院印發《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在“文化領域標準化重點 ”專欄中,明確提出“開展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標準研究”“開展中國文化傳承標準研究”的任務*《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機械工業標準化與質量》2016年3期。。由此而見,文化遺產傳承和文化產業的秩序化、規范化已經進入到國家的文化政策決策,表明了從國家層面鼓勵支持文化標準化建設的重要導向。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的文化遺產保護中引入標準化的理念,經實踐證明,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英國注重遺產保護相關的基本術語界定,強調調查和記錄的基礎標準制定,同時制定與遺產修復有關的技術標準;美國在遺產保護中采取開放性的標準制定方式,邀請公眾廣泛參與,并與國際性標準對接。這些做法亦可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所借鑒。*李春玲:《英美文化遺產保護標準化及對我國的啟示》,《東南文化》2016年第2期。
作為文化特征的標準化及其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系,在學術研究上部分學者已經予以揭示。王霄冰對于祭孔禮儀的研究揭示了以王朝和君主為代表的封建統治者在祭孔禮儀的標準統一中發揮的作用,從而實現自上而下的禮儀標準化的行為。但祭孔禮儀在東亞各地的在地化流傳又呈現出多種多樣的表現狀態。*王霄冰:《祭孔禮儀的標準化與在地化》,《民俗研究》2015第2期。李凡關注膠東地區媽祖信仰的標準化現象,作者指出在神靈祭祀趨向標準化的同時,又同時會融入到地方的祭祀空間中,并不完全呈現出標準化的面貌,作者將其稱為半標準化。*李凡:《神靈信仰的標準化與本土化——以膠東半島媽祖信仰為例》,《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隨著全球化、市場化、遺產化的發展,大眾傳媒的宣傳,一些節日習俗、文化儀式等逐漸呈現出標準化的趨勢。如陳志勤以端午節為例關注了節日習俗的“泛時空化”傾向,即賽龍舟、吃粽子、插艾蒿、掛菖蒲等已經超越地域、時空的限制成為端午習俗的通用符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全國普遍在過同一個端午節的意象。但同時,在各地還普遍存在著具有地方性的節日習俗,這種地方性的習俗與全國日漸統一的習俗并存的現象構成了當下端午節的景觀。*陳志勤:《泛化的端午節與村民的端午日——以嘉興海寧長安鎮的三個村落為例》,《文化遺產》2014年第5期。岳永逸將端午節的符號更進一步縮小為粽子與龍舟這兩個元素,指出在端午節日漸遺產化的同時,一些經典的節日元素逐漸形成普遍性的節日活動,從而形成一個標準化的端午節*岳永逸:《粽子與龍舟:日漸標準化的端午節》,《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正如學者研究所揭示,標準化也是文化的一種基本特征,但它往往只是一種趨勢,與同時作為地方化存在的力量之間形成一種張力,并不會出現完全統一化、標準化的情況。標準化的同時也存在著在地化和本土化,全球化帶來的危機激發了文化內部保護本體文化的文化自覺,是作為對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單一化、標準化的抵抗。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保護公約文件制定中,已經注意到將文化固化、標準化等文化認知的理念引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危險性,并提出了防范性的措施,如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沒有使用本真性、完整性等概念,用意即是要避免在文化保護中存在的本質主義的認識與實踐*戶曉輝:《〈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實踐范式》,《民族藝術》2017年第4期。;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倫理原則》中,更明確提出“本真性和排外性不應構成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和障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倫理原則》,巴莫曲布嫫、張玲譯,《民族文學研究》2016年第3期。
三、標準化:文化多樣性的制度保障
將標準化理念引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是為了使非遺保護獲得“最佳秩序”,是借鑒標準化的理念促使非遺保護有序發展。其主要的工作包括對非遺保護工作進行監測評估,使工作在科學管理之下進行;其次對具體項目傳承的秩序進行規范,主要針對生產性保護中的生產營銷秩序;同時以標準化記錄的理念,通過對核心要素的文本記錄,彌補傳統文化經驗性傳承的不足。
(一)作為保護工作的標準——保護工作的管理
從公共文化事務的視角,非遺保護工作需要有一個合理有序的程序。在國際公約、國家立法等相關規范文件的指導下,非遺保護的普查、認定、申報、記錄、評審、保護等工作在符合一定規范或者在統一的規范下進行。非遺保護是一個新事物,在我國主要以政府為主導、自上而下地進行,相關的機構設置、工作人員、管理制度、工作機制以前不曾有過,是在保護實踐中不斷完善的。如作為一種有效的記錄方式,數字化保護在各地被廣泛采用,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技術要求和技術規格,各地各單位在對文化藝術檔案資料進行數字化處理和管理時,各自為政,一些單位因陋就簡進行數字化永久保存工作,反而造成有些資料在數字化過程中被毀損。”*閻平:《文化產業標準化問題研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所以,通過構建一套科學有效的管理體系,對非遺保護工作進行監測評估,銜接各地工作平臺,將有助于保護工作的規范性。
部分學者早已提出,在非遺保護觀念上要有“紅線”意識*高小康:《“紅線”:非遺保護觀念的確定性》,《文化遺產》2013年第3期。,申報、認定等工作需要規范*徐藝乙:《非遺申報和保護都須規范》,《世界遺產》2013年第3期。,建立“嚴格的科學管理和標準化的操作程序”*烏丙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科學管理及規程》,王文章主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第10-20頁。。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深入,有學者提出“后申遺時期”*高小康:《走向“后申遺時期”的傳統文化保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體現了對我國非遺保護工作轉向的一個認識,即非遺保護從重申報轉向重保護,重申報轉向重管理。也有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相關的探索,如數字化保護中的標準對接*楊紅:《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32-146頁。,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標準化建設*周耀林、李叢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長期保存標準體系建設》,《信息資源管理學報》2016年第1期。、精細化管理*藍海紅:《非遺保護管理的廣東經驗:精細管理》,《文化遺產》2018年第3期。、項目和傳承人名錄制度的思考*孔慶夫、宋俊華:《論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名錄制度”建設》,《廣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立法建設*李曉松:《我國現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規研究》,《文化遺產》2018年第2期。等。另有從事標準化研究的工作者嘗試將標準化引入到非遺保護中,探索性地提出非遺保護標準化的框架*嚴菁:《非物質文化遺產標準體系研究——以青海省為例》,《標準科學》2013年第8期;王海瀛:《標準化視角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標準科學》2015年第10期。。在國家的保護實踐層面,全國文化藝術資源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已經制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標準》。在地方保護實踐中,一些地區制定了保護評估的標準,如浙江省寧波市建立了“三位一體”模式,該模式包括責任以及評估體系,已經在地方實施,對區域內的非遺保護工作進行指標量化。*費伊:《“三位一體”:非遺保護的寧波模式》,《中國文化報》2011年12月21日第004版。湖州市制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通用指南》地方標準,規定了湖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內容和要求。*王煒麗、黃家偉:《非遺傳承 標準助力》,《湖州日報》2018年5月15日第A01版。這些保護工作方法和操作規程的研究和實踐,有利于非遺保護走向科學、規范化的方向。
(二) 作為產品質量的標準——傳承秩序的規范
當前生產性保護主要在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和傳統醫藥藥物炮制類非遺領域實施。這些項目的衍生產品或服務可分為兩類,即供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直接消費的產品和滿足人藝術審美需求的產品。對于供人直接消費的產品,傳統工藝的原料使用、生產環境、產品形式、產品質量等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與現代社會秩序、市場安全標準、生態環境保護、民眾消費需求相互沖突的地方。如近年來出現的“新繁藥浴案”*劉偉:《“田婆婆”一方被判賠償194 萬元》,《南方都市報》2013年3月8日第AA26版。“聶麟郊膏藥案”*《河南非遺“聶麟郊膏藥”是假藥?》,《蘭州晨報》2015年5月26日第AII04版。“錢萬隆醬油停產”*《古法釀醬油不符現代標準停產》,《東方早報》2012年3月7日第A14版。“皇家琉璃停產”*李夢婷:《北京叫停非遺“皇家琉璃”生產》,《北京青年報》2017年8月23日第A05版。等,都凸顯了傳統文化進入現代社會不適應的尷尬。為了能生產出環保、安全、高品質的產品,并確保生產過程符合環保與質檢等方面的要求,傳統工藝項目需要確立一套能與當代社會和市場接軌的標準。“有了標準,就有了一個門檻、一個游戲規則,一方面可以提升民間藝術品的質量,規范混亂的價格體系,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民間藝人的文化責任感,促使他們做出更加精美、更具市場價值的藝術品。”*黃小駒:《民間藝術品是否需要“標準”應該如何制定》,《中國文化報》2007年8月7日第1版。在這個層面上來說,標準實際上是對生產行為的一種約束機制。
對于滿足人藝術審美需求的產品,從非遺項目本身的發展來看,項目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改變與創新,具體體現在原材料的更替、工具的創造、技術的發展等。這些變革在讓項目不斷進步的同時,限于知識交流的界限和藝人的個性,難以形成統一共識,使得生產傳播秩序混亂,缺乏監管,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非遺的可持續傳承,不利于保護和合理利用。因此,也需要從原料使用、生產環境、加工過程等相關環節進行與現代社會要求相符合的規范。
在2012年《文化部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第七條中,提出“鼓勵協會制定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在原材料、傳統工藝流程和核心技藝方面的相關標準和規范,支持協會開展行業管理、行業服務、行業維權等工作,通過行業自律和行業監管,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健康發展。”*《文化部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載于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主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資料匯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第61-65頁。這一條意見強調了通過行業協會來制定相應的技術標準和產品標準。2017年制定的《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中也提出“強化質量意識、精品意識、品牌意識和市場意識”“引入現代管理制度,廣泛開展質量提升行動,加強全面質量管理,提高傳統工藝產品的整體品質和市場競爭力”“鼓勵地方成立傳統工藝行業組織,行業組織要制定產品質量行業標準”等主要任務*文化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財政部:《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中國文化報》2017年3月27日,第1版。。其目標即是讓傳統工藝更合理健康地走進現代市場體系。
從傳統行業的發展來說,那些歷經數百年的老字號,之所以能夠長久不衰,享譽盛名,究其原因就是在生產經營中秉持著一定的原則或標準。如創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的北京同仁堂藥店,歷經300年的發展,制藥時始終堅持“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古訓,守著“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原則*楊在軍:《家族企業長壽之家族因素剖析——以1669—1954年的北京樂家同仁堂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正因為堅持此標準,其在制藥過程中精益求精,制作出來的藥效獨特,成為享譽盛名的老字號。雖然這不是現代質量體系中的標準文本,但已經具備了標準的意識。
所以,就作為一種文化產業來說,正如閻平所言,“標準化是促進文化藝術與現代科技緊密結合、提高文化產品和服務質量、獲取最佳經濟效益的重要技術保障。”*閻平:《文化產業標準化問題研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天津煎餅馃子團體標準制定的緣起,就是針對煎餅馃子混亂的市場采取的行動。首先是制作方法不統一,煎餅馃子是天津傳統小吃,在清朝時期就有記載。目前市場上流行有數十種做法,形成了不同的口味。但是具體哪一種口味是正宗的,能夠代表老天津的手藝,并沒有權威界定。其次在用料方面,傳統的煎餅馃子是綠豆、小米加五香粉混合而成,加馃子或馃篦、面醬、蔥花、辣椒醬,再輔助以雞蛋搭配。目前市場上出現各種各樣的材料,如黑芝麻、牛肉、花生、生菜、火腿甚至還有海參。而這些在當地人的眼中并不是正宗的煎餅馃子,只是標新立異出現的新事物。再次是衛生標準參差不齊,煎餅馃子的出售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流動攤位,一種是固定店鋪。一些制作者為了降低成本,在衛生設備、消毒設備等方面缺乏配套,存在著相應的隱患。最后,定價比較混亂。煎餅馃子的定價從四五元到十幾元不等,最貴的海參煎餅馃子賣到78元一個。因此,為了規范市場秩序,行業協會才討論制定標準。
初看已經實施的《煎餅馃子標準》文本,對煎餅馃子分類、食品原料要求、制作場所及設施、設備要求、加工過程控制及機構、人員管理要求、加工工藝要求、標識、包裝、運輸和貯存等內容,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在原材料質量上按照國家相應食品安全標準來制定,使食材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王建章:《T/TJCY 002—2018 〈天津地方傳統名吃 制作加工技術規范 天津煎餅馃子〉》,《標準生活》2018年第8期。。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執法者、監管者的監管工作,生產者自律生產,消費者能夠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保證行業的健康云運營。當然此標準的制定并不是把煎餅馃子固定下來,符合此標準的才是正宗的煎餅馃子,不符合標準的就不是。這一標準實際上是從加工過程中的原料、質量、衛生等方面做的規定,且屬于推薦性標準,并不強制每一位從業者進行采納。標準制定的效果并不會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其具體實施的效果還需要在長時間的實施之后才能體現出來。
(三)作為工藝流程的標準——核心技藝的記錄
藍勇通過對川江木船制作技藝的研究,提出標準性和經驗性兩種技術的傳承方式。西方對于技術的傳承屬于標準性傳承,偏重于量化科學的文本記錄;中國屬于經驗性的傳承方式,技術的學習過程缺乏文本記錄,多靠口傳。在川江木船技藝的傳承中,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存在著“文本化式弱”和“文本精度弱”的問題,作者提出“先進的中國傳統技術與落后的技術傳承途徑存在巨大反差”。*藍勇:《對先進制造技藝與落后傳承途徑的反思——以歷史上川江木船文獻為例》,《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這樣的問題在我國的非遺傳承中普遍性地存在,往往出現面對古代復雜高超的技藝,現代人難以復制或者模仿的窘況。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是我國傳統文化獨特的傳承方式。
與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以量化、可控、精確為特征的科學知識相比,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確定性。如在武術、醫藥、飲食文化中“適量”“少許”“若干”“悟性”等詞匯都是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的體現,這也決定了文化習得的方式,不是通過科學知識的教授,而是口傳心授、體悟式的學習,傳統行業中“只可意會 ,不可言傳”“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會了不難,難了不會”等諺語都說明了這樣的習得方式。因此一門好手藝的掌握需要較長時間,在很多項目中可以發現,快速成長起來的年輕傳承人做出的產品,缺少的往往是上一輩人多年領悟才成就的“神韻”。正因為這樣經驗式的傳承方式,很多技藝缺乏記錄,鮮有系統性的文本流傳下來,即便現代人想復制過去的技術都難以找到參照的范本。
在當下的非遺保護中,也講求創意文化、創意產業。然而,往往設計師設計出來的產品卻不被認可,體現不了非遺文化的精髓,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沒有掌握核心技藝。古人講“萬變不離其宗”,“宗”就是指核心技藝或核心元素,如民間文學神話故事演變,無論怎么改編,但仍是基于幾個固定的母題*陳建憲:《論比較神話學的“母題”概念》,《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傳統技藝歷經幾代人,在原材料、工藝、設備等方面進行變化,傳承下來的則是其核心技藝。核心技藝是一項傳統工藝經濟價值和人文價值之所系,是一項技藝的靈魂*邱春林:《守住“核心技藝”——以大理白族扎染為例談傳統手工技藝的生產性方式保護》,《美術觀察》2009年第7期。。在《文化部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中,“堅持傳統工藝流程的整體性和核心技藝的真實性”這句話出現多達7次,可見傳統技藝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的傳承是生產性保護的核心,而經濟價值的生產是手段,兩者相互促進。在傳承活動中,對于經濟利益、產品開發、技術引進的關注往往忽視了傳統工藝的保護,造成了經濟利潤增長、文化保護滯后的現狀。因此,有必要在記錄完整工藝流程的基礎上對核心技藝進行完整的記錄。
標準化的成果之一就是標準文本的制定。這一文本是在經過多方多次協商討論后達成的一定共識。標準所要保護的是非遺的核心成分,是要通過技術層面的規范來保證其文化內涵的傳承。因此,標準化正是保證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也許有人會質疑,標準文本記錄會把技藝、流程固定住,其實不然,因為標準本身具有一定的彈性空間。標準文本只是在一定時間內的范本,隨著社會發展產生的創新和需求,標準也會適時而變,通過標準的修訂跟上工藝技術的進步。
“煎餅馃子”在天津有600多年的歷史,這個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中的記載。在1986年出版的《津門小吃》一書里,有對煎餅馃子制作技藝相對詳細的記錄。即將綠豆磨成粉,浸泡去皮再磨成糊,加入調料成漿,小火燒熱烙子,放油倒漿,再烙制而成。*天津飲食公司烹飪技術培訓中心編寫組編:《津門小吃》,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第25頁。這算是可見到的關于煎餅馃子工藝的較全面的記錄。煎餅馃子核心的部分在于“馃子”和“馃箅兒”的制作,在《津門小吃》中并沒有相關記錄。平時小攤自己不制作,都是到別處購買。在天津煎餅馃子的標準制定中,煎餅馃子協會認為市場上流行的煎餅馃子很多都不是正宗的煎餅馃子,在工藝流程上缺乏標準,相對“正宗”的是《津門小吃》中記錄的做法。在《煎餅馃子標準》在附錄中,制定者選取了清真“津老味”煎餅馃子制作工藝(干粉型)、“普緣”和煎餅馃子制作工藝(水磨型),作為煎餅馃子制作的代表性工藝。從其中的記錄可見從原料選擇到配料、磨制、調和、成品等都做了較為詳細的記錄,有參考《津門小吃》中的記錄,也有根據現代經營生產添加進入的詳細內容。尤其對“馃子”“馃箅兒”的制作進行細致描述,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使煎餅馃子的核心制作技藝得以保留。
結論
綜合上述討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我們應該區分從兩種邏輯出發的對于標準化的認知,即作為對文化特征理解的標準化和作為規范保護活動的標準化。作為一種文化表達形式,非遺的確不能夠進行量化和測量,無法也不應該固定或者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是作為保護文化表現形式所開展的工作和活動,需要進行規范,使其達到“最佳秩序”。這些工作需要在非遺保護中通過政府與地方當事人之間的互動中得以開展。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標準化與文化多樣性并非完全對立而應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對于文化保護重要的是保障一個有序的傳承環境,而不是規范文化內涵的表現。健全的傳承環境需要依靠多樣性的文化內涵的解釋以及與之配套的實施標準。如前述有關文化特征的標準化的研究所揭示,標準作為一種典范只是一種參照,實際上人們在實踐過程中還是會結合各地的具體情況進行改良和創新,所以反而會促進文化多樣性的發展。例如曾國軍等基于臺灣品牌“鮮芋仙”的研究,提出地方飲食中標準化與原真性的關系為“標準化是原真性的保障,原真性是標準化的根基”*曾國軍、孫樹芝:《跨地方飲食文化生產:鮮芋仙的原真標準化過程》,《熱帶地理》2016年第2期。。受此啟發,標準化與文化多樣性的關系也可以表述成“標準化是文化多樣性的保障,文化多樣性是標準化的根基”。
第三,非遺保護相關標準研制尚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多方協同參與,凸顯文化行業標準的特色。非遺保護作為一項公共文化事業,在國家大力推行公共服務標準化的趨勢下,不可避免地也會引入標準化的管理模式。目前將“標準”的理念引入到非遺保護工作中還存在爭議,沒有達成普遍性共識。因此需要通過學術研究和保護實踐直面存在的問題,在實踐中尋找答案,而不能僅僅停留在話題爭議層面而沒有下文。標準的制定從呼吁到制定再到實施是一個系統漫長的過程,需要多元力量的協同參與。因此,非遺保護標準的研制需要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協調學界、傳承人、產業界、行業協會、消費者等多方關系,形成相互對話*王霄冰、胡玉福:《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規范化與標準體系的建立》,《文化遺產》2017年第5期。,在協商的基礎上使制定的標準既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管理需要,又能延續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鮮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