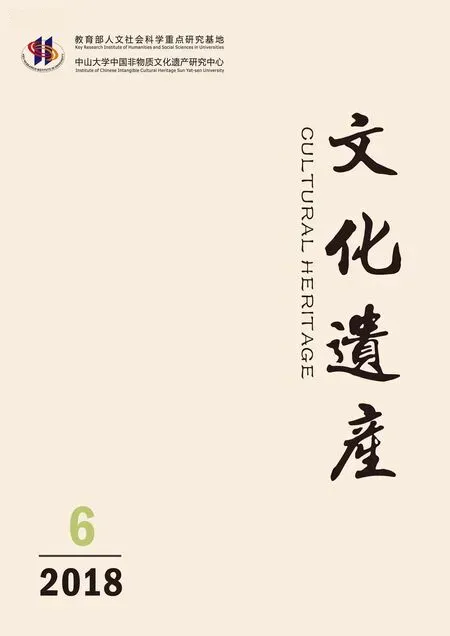影像的神力:高淳的廟會與禳解法*
楊德睿
一、廟會作為一種宗教傳承/傳播形態(tài)
對廟會等宗教節(jié)慶儀式的研究可謂是宗教人類學(xu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然而,盡管人類學(xué)家針對廟會的象征體系、儀式過程、宇宙觀與意義結(jié)構(gòu),以及(社會)結(jié)構(gòu)功能做出了大量的記述和分析,但人類學(xué)大師克利福德·格爾茲于四十多年前在《作為文化體系的宗教》一文中對整個宗教人類學(xué)界的針砭似乎依然有效*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46頁。,他說“宗教調(diào)整人的行動,使之適合頭腦中的假想宇宙秩序,并把宇宙秩序的鏡像投射到人類經(jīng)驗(yàn)的層面上,…但…我們幾乎一點(diǎn)兒也不知道這種奇跡在實(shí)踐中是怎樣完成的…我們有大量的民族志資料來證明這一點(diǎn),但能夠使我們對其進(jìn)行分析的理論框架卻并不存在”,因此,他號召后學(xué)們致力于研究信教者如何“被喚起某種鮮明的習(xí)性集合(包括傾向、能力、癖好、技藝、習(xí)慣、義務(wù)感、趨向),使其行為舉止與經(jīng)驗(yàn)性質(zhì)具有一種長期特征”,他把這種“習(xí)性的集合”稱為精神氣質(zhì)(ethos),它會外在地展現(xiàn)為信徒們“生活的基調(diào)、性格、質(zhì)地”,但更重要的是植入到信徒腦中的“道德與審美的風(fēng)格[即恒常的“動機(jī)”]和情緒”。很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格爾茲所呼喚的那種聚焦于精神氣質(zhì)之陶冶機(jī)制與生效過程的作品依然罕見。不過,盡管還比較罕見,影響也不廣,但宗教人類學(xué)界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對格爾茲的呼吁的間接回應(yīng),比如與格爾茲同屬大師級的維克多·特納于晚年倡議的經(jīng)驗(yàn)人類學(xué)*Victor Turner & Edward Bruner.2001 (eds).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就是從感性面回應(yīng)格爾茲的著例,而近二十多年來緩緩興起的宗教認(rèn)知/傳承的人類學(xué)(anthropology of religious cognition/transmission)則代表了從認(rèn)知面回應(yīng)格爾茲的路線,這也就是本文的問題意識和分析概念的源頭。易言之,本文的企圖也在于以高淳的案例說明廟會如何喚起某種鮮明的認(rèn)知習(xí)性,使當(dāng)?shù)匦疟姷男袨榕e止與經(jīng)驗(yàn)性質(zhì)表現(xiàn)出某種長期特征,從而形成了風(fēng)格獨(dú)特的葦航庵禳解法。
宗教認(rèn)知/傳承的人類學(xué)對本文最重要的啟發(fā),來自哈維·懷特豪斯的“宗教模式理論”*Harvey Whitehouse. 2000. Arguments and Icons: Divergent Modes of Religio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Harvey Whitehouse. 2004. Modes of Religiosity: A Cognitive Theory of Religious Transmission, AltaMira Press.、羅伯·麥考利與托馬斯·羅森的“儀式形式理論”*Robert McCauley & Thomas Lawson. 1993. Rethinking Religion: Connecting Cogni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ringing Ritual to Mi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For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以及賈斯汀·巴瑞特等人關(guān)于“神學(xué)的理論”與“媽媽的理論”之別的洞見*Justin Barrett. 1999. "Theological Correctness: cognitive constraint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Method &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Vol. 11; Barrett, Justin L., Richert, Rebekah A. &Driesenga, Amanda. 2001. "God's Beliefs versus Mother's: The Development of Nonhuman Agent Concepts", Child Development, Vol. 72 No.1。
哈維·懷特豪斯的“宗教模式理論”的要旨是:宗教傳播/傳承的具體形式多不勝數(shù),但必然坐落在意象模式(imagistic mode)和教條模式(doctrinal mode)這兩個極端之間。意象模式以無文字民族的過渡儀式(如成丁禮)為典型,其發(fā)生的頻率很低(一生一次),其間密集使用激起強(qiáng)烈感官反應(yīng)和情緒的媒介,加上肉體的折磨,使參與者形成極為深刻的情景性記憶(episodic memory; 又叫閃光燈泡式記憶),而且這些儀式通常要求保密,所以參與者所獲的靈性體悟不會通過語言外傳,新生代只能通過親身參與同樣的儀式才能得知情況。相對的,教條模式則以誦讀、宣講經(jīng)典文本的活動為典型,發(fā)生的頻率很高(如每天誦經(jīng)念咒許多遍),其過程通常冷靜肅穆無感官刺激、機(jī)械重復(fù),目的是在學(xué)習(xí)者的腦中蝕刻下字串型記憶(semantic memory),對背誦能力、專心能力、抵抗睡魔的能力要求很高,并且通常鼓勵信徒以語言文字廣為傳播其義理。
羅伯·麥考利與托馬斯·羅森可謂是上述宗教模式理論最熱心的響應(yīng)者,尤其是他們的《把儀式帶進(jìn)心里:文化形式的心理基礎(chǔ)》(2002)一書,號稱是站在宗教模式理論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了解釋力更強(qiáng)的“儀式形式理論”,其主旨是將一切儀式大別為“特殊施為者儀式”(special agent ritual)和“特殊工具/特殊承受者儀式”(special instrument/recipient ritual)兩大類,前者指神鬼等超自然力量扮演施為者角色的儀式,后者指超自然力量居于中介或者承受者角色的儀式,前者幾乎絕大多數(shù)表現(xiàn)為懷特豪斯稱為“意象型宗教”的形式,后者則傾向于懷特豪斯的“教條型宗教”。
賈斯汀·巴瑞特等人關(guān)于“神學(xué)的理論”與“媽媽的理論”之別的論點(diǎn)主旨是:幾乎所有成體系的宗教都會創(chuàng)造出一些超越直觀的、對認(rèn)知能力要求較高的“神學(xué)的理論”,比如說“神是全知全能、無所不在、沒有形體的”這種難以把握的觀念,與此同時,就算是精通神學(xué)、很虔誠的人,也不免會懷抱著一種符合直觀的、在認(rèn)知上不費(fèi)吹灰之力的“媽媽的理論”,比如說“在神明的跟前不要淘氣”這種把神構(gòu)想為一個有肉身、有空間位置的凡人的觀念。或許只有極少數(shù)修行境界很高的宗教家能徹底排除掉“媽媽的理論”,絕大多數(shù)人都會無視二者之間的矛盾,視場合的需要而在二者間選擇使用。
以上三種論點(diǎn)對我們?nèi)鐚?shí)地觀察、思考廟會對參與者傳遞的信息提出了重要的指引:“宗教模式理論”促使我們停止幻想作為一種偏“意象型”宗教傳播手段的廟會有可能傳導(dǎo)神學(xué)論說或經(jīng)典教義等以字串編碼的信息,而是應(yīng)該聚焦于群眾在廟會中所獲得的情景性的、閃光燈泡式的記憶。其次,“儀式形式理論”則啟示我們?nèi)绾纹查_繁瑣的細(xì)節(jié),提綱挈領(lǐng)地直探廟會所傳導(dǎo)的情景性記憶中的關(guān)鍵——施為者(agent)在“神-物-人”這套關(guān)于行動的認(rèn)知模塊當(dāng)中的坐落位置和形象,借以分析出這些記憶如何召喚某種認(rèn)知傾向。最后,“神學(xué)的理論”與“媽媽的理論”之別,讓我們得以比較清晰地勾勒出廟會所召喚的認(rèn)知傾向會激發(fā)起什么樣的情緒和動機(jī),并且會擴(kuò)散到廟會之外的領(lǐng)域。
二、高淳的廟會
(1)高淳的宗教氛圍
高淳,位于江蘇省南京市南端,其文化風(fēng)尚與其西面的安徽蕪湖、當(dāng)涂,南面的安徽郎溪、廣德,東面的江蘇溧水、溧陽都很接近,屬于宗教氛圍普遍濃厚的蘇皖浙三省交界丘陵地帶中的一角。上千年的水路網(wǎng)把散布在這一片丘陵地帶上的農(nóng)林業(yè)聚落串聯(lián)了起來,使他們既能在相對獨(dú)立的狀態(tài)下發(fā)展獨(dú)特的創(chuàng)意,又能互通有無、切磋比較,形成了和風(fēng)土產(chǎn)品貿(mào)易市場同樣繁復(fù)而豐富的宗教、戲曲、工藝美術(shù)市場。
與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普遍情況一致,高淳的每個居民聚落都有一座以上的祠廟,人口稠密的城鎮(zhèn)則更是祠廟眾多。據(jù)當(dāng)?shù)匚氖穼<义ш柨稻┫壬谑昵?2008年10月)主持的調(diào)查,不算家族宗祠,當(dāng)時高淳境內(nèi)可考的道佛兩教廟寺神祠還有近七十座,其中有五十多座于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了重修、重建,估計(jì)近十年來這個數(shù)字還在緩慢增加。這數(shù)十座祠廟中絕大多數(shù)供奉的是當(dāng)境的保護(hù)神,如祠山大帝、劉猛將、東平王、降福菩薩、觀音菩薩等等,其運(yùn)營管理全是由周圍的鄰里、家族推舉出來的代表(稱為“老人會”、“村委”等)負(fù)責(zé),僅有極少數(shù)幾個是由道士、和尚等專業(yè)宗教人士主持的。
與鄰近地方相比,高淳的宗教風(fēng)俗或許稍微特殊一點(diǎn)的地方,就是高淳人對廟會活動似乎特別熱衷,尤其是對于與廟會有關(guān)的游藝表演似乎特別認(rèn)真講究,高淳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項(xiàng)特色。不過是一個下轄6個鎮(zhèn)、兩個街道,總?cè)丝诓?0余萬的小地方,高淳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中竟能收錄二月初八古柏鎮(zhèn)韓村的祠山廟會、七月廿四椏溪鎮(zhèn)定埠村的降福菩薩廟會等14項(xiàng)廟會傳統(tǒng),而與祀神有關(guān)的游藝表演傳統(tǒng)更是多達(dá)34種——如淳溪鎮(zhèn)長蘆村楊家抬龍、固城武五猖等!若再加上多少與祀神相關(guān)的年節(jié)、端午、立夏、中秋節(jié)節(jié)慶活動19種,則高淳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中至少有67種與宗教關(guān)系密切的活動。這些活動舉行的頻次和時間長度彈性很大,所以無法精確估算它們在高淳人社會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據(jù)濮陽康京先生的回憶,在上世紀(jì)90年代末之前的那十多年間,一年356天當(dāng)中有某種廟會游藝表演活動登場的日子似乎占到了一半,甚至到達(dá)200天之多!這個數(shù)字也許有些夸張,但是我們大概能肯定,在過去的高淳,至少從秋收以后到次年的二月,再加上立夏和端午前后這幾個時段,高淳的生活里確實(shí)充斥著大大小小的廟會以及相關(guān)的游藝表演。而這些廟會和節(jié)慶活動又構(gòu)成了最重要的傳播語境,讓戲曲、神仙傳說、民間故事、武術(shù)、小吃、工藝品等各種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得以在其中傳承存續(xù),一同編織起傳統(tǒng)高淳人的生活世界。
進(jìn)入21世紀(jì)以后,由于高淳經(jīng)濟(jì)發(fā)展迅速,大量的中青年外出投資經(jīng)商、移民、就學(xué),加上計(jì)劃生育政策導(dǎo)致青少年人數(shù)銳減,于是,雖然民眾修建祠廟的熱情依舊,財(cái)力更比以前還要雄厚,但有空閑時間能投入學(xué)習(xí)、演出、組織這類活動的人數(shù)急劇減少,所以如今高淳的廟會相關(guān)活動只能集中到春節(jié)、五一、十一等長假期間舉行,參演人員據(jù)說也減少了非常多。但盡管如此,與鄰近地區(qū)相比,尤其是與北面的馬鞍山、江寧、南京相比,高淳的傳統(tǒng)宗教氛圍和活躍程度至今還是非常突出的。
(2)“出菩薩”和演戲
高淳的廟會多彩多姿,但無論如何,其基本的共通點(diǎn)是都必須在廟里對全堂神明設(shè)供、上香、祝壽,并在廟會正日子前后數(shù)日開放讓信徒前來參拜進(jìn)香。在此一基本點(diǎn)外,祠廟的組織者可在“出菩薩”和演戲這兩大模式間擇一而行,前者是繞境游行,后者是在廟前廣場之類的定點(diǎn)進(jìn)行靜態(tài)演出。
“出菩薩”,顧名思義就是將神明從廟里請出來繞境巡游一番,據(jù)筆者實(shí)地觀察所見,其操作流程大致如下:
1.祠廟的組織者(老人會、村委)于神誕日數(shù)周甚至數(shù)月之前討論是否“出菩薩”,然后請神明做最終決定。至于他們是通過什么手段得知神明的決定,多數(shù)人甚至包括熱心廟務(wù)的信徒也不甚了了,僅聽過傳言說他們會通過“開口仙”(即靈媒)去請示神明。
2.組織者分頭布署籌款出納會計(jì)、組織人手培訓(xùn)演練、打掃檢修廟堂和各種儀仗法器裝備。
3.于神駕繞境前三日(最晚也要在前一日)完成所有的打掃和設(shè)備檢修,在整修干凈的廟堂里,除既有的神龕、供桌之外,另擺設(shè)幾張八仙桌,每張八仙桌上放置一頂馗頭、一幅面具和一柄寶劍,前設(shè)香爐及清茶、水果、甜點(diǎn)等供品,另將神明出巡時穿的袍服用衣架子架好,陳列在廟堂兩側(cè),然后開始每日早、晚對神像和馗頭面具奉茶、上香,并開放給信徒燒香上供(見彩圖1、2)。同時,所有的祠廟執(zhí)事,尤其是負(fù)責(zé)扛馗頭扮神的壯丁們和捧面具、香案的禮生們開始齋戒(戒酒、肉、房事)。
4.廟會正日子當(dāng)天清晨四、五點(diǎn)開始向主神和全堂馗頭面具焚香、奉茶、獻(xiàn)供,領(lǐng)頭執(zhí)事稟請神明起駕,扮神的壯丁們隨即開始著裝,在眾人的幫助之下把數(shù)斤重的鐵和竹制衣架在身上束定,再套上寬大的繡袍,背后插上旗子,之后把數(shù)十斤重的馗頭頂在頭上,與穿在身上的鐵架綁縛固定好,最后再把面具套上。(見彩圖3、4、5)
5.扮神接近完成時開始鳴鼓,扮神完成后,廟門大開,放炮竹煙花,扮神者和捧香案的前導(dǎo)人員以及其它儀仗隊(duì)人等在炮竹聲中列隊(duì)完成,扮神者兩手捧起寶劍,隨即鳴鑼開道,開始繞境。(見彩圖6、7、8)
6.巡行途中會每隔幾里路停下來休息一段時間,其地點(diǎn)一般是自然村的中心或者幾個村落間道路的交匯點(diǎn)。組織者會先在休息站用八仙桌和板凳設(shè)置好香案,擺設(shè)好供品,隊(duì)伍到達(dá)休息站后,首先就是讓當(dāng)?shù)卮迕裣蝽斨割^和面具、坐在寶座上的扮神者上香上供,一會之后由眾人合力將馗頭和面具從扮神者頭上卸下置于香案上,扮神者才能喝水,但除非接下來隨即要換人,否則扮神者依然不能吃東西和說話。通常在休息一刻鐘左右之后,扮神者再次著裝、扛上馗頭、戴上面具,儀仗隊(duì)就位,然后鳴炮、鳴鑼開道,向下一站走去。(見彩圖9、10)
7.巡行經(jīng)過其它廟宇時以及回到本廟之前,似乎是最容易“來神”的時刻,意即神靈降附在扮神者的身上,使得扛著數(shù)十斤重(估計(jì)不會少于25公斤)的馗頭面具等裝備的扮神者陷入迷狂狀態(tài),突然不再步履遲重,感到周身輕盈起來,似乎可以翩然起舞,甚至做出飛跑轉(zhuǎn)圈等動作。“來神”通常會使游行隊(duì)伍偏離原來預(yù)訂好的路徑,拖長巡行的時程,并使扮神者過度疲倦或者過度亢奮而不得不換人,才能將隊(duì)伍帶回原來設(shè)定的軌道。
8.游行隊(duì)伍回到本廟前,眾人協(xié)助扮神者把馗頭面具袍服等卸下,扛回原香案處安座,然后再向主神上香、奉茶、獻(xiàn)供以表示謝恩、慰勞之意,隨后鳴放煙花炮竹以慶賀功德圓滿。之后,各來參會的游藝表演團(tuán)體開始依序向神明獻(xiàn)演,獻(xiàn)演同時或結(jié)束后,祠廟執(zhí)事與工作人員散齋開葷,聚餐會飲。
9.廟會期間結(jié)束,馗頭、面具、寶劍、袍服等法器收回到平常擺放的位置(通常是主神身旁兩側(cè)的神龕內(nèi)),八仙桌和板凳擺出的臨時香案撤除,廟堂恢復(fù)平時的原貌。
除了以上所描述的核心程序外,規(guī)模較大的廟會還會有游藝表演團(tuán)隊(duì)參與游行。高淳在游藝表演這方面特別發(fā)達(dá),單就被列入了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的項(xiàng)目就有蕩旱船(和蕩湖船;含蚌精舞)、舞龍(抬龍)、舞獅、跑馬燈、踩高蹺、武術(shù)(打叉、打水滸、打羅漢)、花車(龍吟車、轔轔車、串串燈)、抬閣、儺舞(跳五猖、跳八怪)、打蓮湘等十大類,此外還有許多分量較輕、缺乏傳統(tǒng)而不被列入的表演形式,比如花傘隊(duì)、孩子們的“扮仙”等等。
看完了出菩薩,接下來再看第二種基本形式——演戲。
演戲這一模式操作起來相對單純,因?yàn)閼虬嘧雍痛顟蚺_的班子都是專業(yè)團(tuán)隊(duì),當(dāng)?shù)鼐用竦娜蝿?wù)基本上就是籌錢,只要功德主資金到位、“掛紅”(即贊助、打賞戲班子的演出)來得夠多,剩下的就是找戲班和搭臺的班子,而且據(jù)說高淳人不但特別愛看戲,而且對戲曲的胃口寬廣,不管徽劇、錫劇、黃梅戲、揚(yáng)劇、高腔、目連戲、昆腔、京戲,只要演的好都行,再者,高淳人對酬神戲的戲碼并沒有太多的規(guī)矩,只要不是太悲慘的悲劇、劇情多少能跟神仙沾上邊,就都能接受,所以安排戲班子訂戲碼也并不麻煩。一旦安排好了戲班子和搭臺班子,之后就是等廟會期間開鑼上演便是。至于那些較小的廟宇,多半只能請得起放電影的班子,那就更是省事,連搭臺子都不必了。
然而,與“出菩薩”的情況類似,規(guī)模大的廟會在演戲這個主要的節(jié)目之外,也常會添加一些游藝表演,比如在戲臺搭好要啟用時或是在正戲開鑼之前,先請?jiān)栖?又叫托托車、串串燈)來表演一下“破臺”,或是讓舞獅隊(duì)、打蓮湘、打羅漢等團(tuán)體先鬧一下場。
(3)“神學(xué)的理論”和“媽媽的理論”:廟會傳導(dǎo)的認(rèn)知傾向
高淳的廟會活動究竟召喚著了怎樣的認(rèn)知傾向?或者更精確地說,參與廟會強(qiáng)化或抑制了高淳百姓的哪些認(rèn)知傾向?
懷特豪斯的宗教模式理論可能對此提出的答案大概是這樣:偏于“意象型宗教”的高淳廟會,會強(qiáng)化事件性、情景性的閃光燈炮式的記憶,提升感官體驗(yàn)在知識體系中的地位,給予個人自主的靈性體悟較大的空間。這種大分類框架式的回答,顯然太過空洞,幸而麥考利和羅森的儀式形式理論在此給出了一條線索,即人類認(rèn)知包括廟會在內(nèi)的一切儀式,都使用著與關(guān)于“行動”的認(rèn)知相同的認(rèn)知模塊,而“施為者”的位置與角色則是這套通用認(rèn)知模塊的關(guān)鍵。換言之,儀式所傳達(dá)的核心信息內(nèi)容,和一切關(guān)于“行動”的信息內(nèi)容一致,就是人要怎么做才能做成一件什么樣的事情,唯一不同的只是在宗教儀式情境中有鬼神等超自然力量參與,所以,儀式所傳達(dá)的核心信息可以歸納為“人應(yīng)該對什么樣的鬼神、采取怎樣的行動才能達(dá)到目的”——即求得什么樣的賜福、獲得什么樣的饒恕、免除什么樣的災(zāi)禍等等。這種信息的形式框架是跨文化普遍的,但其內(nèi)容必然是文化/宗教特定的,也就是肯定與當(dāng)?shù)氐闹髁鱾惱淼赖隆⒗硇浴⒏行杂忻芮械年P(guān)系(一致、對抗或逃遁),而且往往形成了為數(shù)不多的幾種傳統(tǒng)套路。而在傳授/習(xí)得這些套路時,或許最先被注意到的,可能也是最核心的層面,就是施為者——即神鬼等超自然力量——的形象,以及他們在這些套路中與工具(如建筑、法器、靈媒、祭司)和承受者(信徒)的相對位置、角色關(guān)系形態(tài)。
循著這個線索來看,高淳廟會中最明確地呈現(xiàn)出超自然施為者形象的情境,無疑就是“出菩薩”,而這一情境所描繪出的超自然施為者——神明——是戴著馗頭和面具、穿著古代官袍、手拿木制寶劍的凡人!此處的重點(diǎn)在于神明不能被分析、化約為以上任何一個元素,祂必須是一個組合。
首先,裝扮成神的凡人當(dāng)然不是神。他們的凡俗軀體器官,如頭、臉、軀干、四肢,除了手以外都被寬大的服飾徹底地掩蓋了起來,而且這些服飾和道具在風(fēng)格上一貫刻意地突出與當(dāng)代人之間的古今區(qū)隔,盡力讓旁觀者不會感受到眼前這位神明的內(nèi)里是個活生生的現(xiàn)代人,此外,這些扮神者在脫掉身上一切的神明服飾之前,按老規(guī)矩是不能說話和吃喝拉撒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凡俗肉身的生理機(jī)能都要暫時關(guān)閉,變成一具幾乎沒有任何施為作用(agency)的“活尸體”。這些肢體被隱藏起來、暫停了生理機(jī)能和施為作用的“活尸體”當(dāng)然不是神,只是神的肉質(zhì)載具。
其次,組成神明外觀的馗頭、面具、官袍、靴、木劍等物件(法器)也不是神。很顯然,高淳人會認(rèn)之為神的,只有安坐在神龕里、與人一樣有完整身體的神像,還有就是“出菩薩”時由真人裝扮成的神,其它一切物件都不可能。不過,馗頭和面具的確擁有比其它一切物件崇高得多的地位,所以有必要仔細(xì)審視一下這套裝置的角色意義。
所謂馗頭就是面具上方的那一塊形狀類似于碑(見彩圖1、5、6、7)的巨大頭飾,它是用數(shù)百片如箭簇形狀的木片組合而成的,總高約一米到一米二、寬50至60厘米。在這塊木片組成的“碑”上,由上而下一層層地嵌著數(shù)十尊高約20厘米的小木質(zhì)神像,最上層的多半是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南極仙翁、真武大帝、太乙救苦天尊等道教的上圣高真,然后是正一天師張道陵、雷祖、二郎神、四大天君等神格略低的道教大神,而到了下幾層則率多不為道教正統(tǒng)所承認(rèn)的高淳民間俗神,甚至包括《封神榜》、《西游記》等小說中的虛構(gòu)人物黃飛虎、孫悟空、豬八戒等。比較講究規(guī)矩的廟宇會請道士來為馗頭“開光”,于是道士就會為每一尊小神像用朱砂和黃紙書一道符,然后折成翅膀形狀扎在神像背后,并為馗頭掛上開光鏡。但不管有無請道士開光這一手續(xù),馗頭上方都要嵌上一方靛藍(lán)色的名牌,寫上這座馗頭歸屬的神名。
“馗頭”這個奇特的裝置究竟要表達(dá)什么?它為何被設(shè)計(jì)成這般模樣?我在高淳當(dāng)?shù)貨]有問到任何答案,幸好在幾位道教研究專家的提示下*筆者謹(jǐn)在此對提供線索的李滔祥先生、陶金先生致謝,并感謝祝逸雯博士慷慨提供的“虛皇”圖片。,我意識到它應(yīng)該是把“全神圖”或“全神卷”加以立體化的結(jié)果(見彩圖11),而且這一立體化也不是高淳所獨(dú)有的,上海尤其是浦東地區(qū)很多的道觀里都藏有稱為“虛皇”的類似木雕(見彩圖12),在舉行科儀的時候可用它來代表“三清”。“虛皇”即“虛皇上帝”之簡稱,在魏晉道教上清派最核心的經(jīng)典《上清大洞真經(jīng)》中尊稱為“高上虛皇君”,隨后,南朝的華陽陶隱居先生繪《真靈位業(yè)圖》時將“虛皇道君”也就是元始天尊(即“三清”之首)奉為宇宙萬靈之首。所以,筆者認(rèn)為馗頭的概念可以溯源到陶隱居的《真靈位業(yè)圖》,該圖的概念被后世的道教徒立體化,并以其中最崇高的“虛皇”來稱呼,而同樣的概念被通俗化演變成為全神圖,而后再被立體化成為馗頭。如果上述推測是正確的,那么馗頭意圖表現(xiàn)的,可說是統(tǒng)轄高淳的各層級神明的整套神譜,就像陶隱居的《真靈位業(yè)圖》意圖呈現(xiàn)當(dāng)時道教的完整神譜一樣。
高淳當(dāng)?shù)孛癖婋m說不出馗頭的來歷,但非常清楚馗頭是特別神圣、尊貴的東西,只有祠山大帝、二郎真君等神明能把它頂在頭上,表示這些大神是有本事“通天”的,被神明收為護(hù)法的五猖、八怪(或“八愷”)等下界的魔頭是沒有資格頂?shù)摹R簿鸵驗(yàn)樗硎尽巴ㄌ臁保簿褪钦f神會從馗頭上下來,所以頂了它才能“來神”。同時,馗頭的神圣與尊貴具體表現(xiàn)為它在一應(yīng)相關(guān)儀式中的角色位置。馗頭平常被謹(jǐn)慎的存放在主神兩側(cè)的神龕里,出菩薩前必須請出來仔細(xì)地清潔、檢修,然后小心地移到神案上接收信眾上香供奉幾天,然后在出菩薩的過程中,馗頭一貫是注意力的焦點(diǎn),如果當(dāng)次出菩薩有“來神”,那當(dāng)然就是整場活動的最高潮,如果沒有,那么整個出菩薩過程中的第一個高潮就是扮神者換裝并把馗頭戴定這一相當(dāng)麻煩的程序,它總是能吸引熱烈的關(guān)注,之后,在出菩薩的隊(duì)伍中,高聳的馗頭當(dāng)然是整個隊(duì)伍的中心,到休息站暫歇時,頂著馗頭的神明是民眾上香跪拜的對象,休息結(jié)束后,扮神者再次頂起馗頭的程序又往往成為一次小的高潮,最后,等出菩薩結(jié)束,扮神者卸下馗頭,馬上又被眾人小心翼翼地簇?fù)碇埢厣颀惔娣拧?/p>
那么,馗頭加上面具就是特殊的施為者(神明)嗎?從某種角度來講應(yīng)該不是。這不僅因?yàn)楦叽救瞬粫@么說——亦即這樣的觀念不符合高淳人能用言語表達(dá)出來的顯意識中,更是因?yàn)椋瑥乃趦x式中的角色位置來看,馗頭和面具只是一組把神的意識與力量和凡人的身體匯合起來的媒介。這一媒介的功能一般保持在潛隱/關(guān)閉狀態(tài),直到出菩薩前幾日才開始被逐漸激活,但直到扮神者將馗頭和面具戴上的那一刻,這個媒介才真正啟動匯合作用,將信徒們期盼的神明帶到人間,呈現(xiàn)在眾人面前。正因如此,所以戴上馗頭和面具的過程總是引來熱切的關(guān)注,因?yàn)槟菐缀醯扔谏衩鹘凳阑蝻@圣的時刻,至于能證明神明之施為作用的“來神”,更是不需要附加任何刺激感官的包裝就自然引人注目。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出菩薩結(jié)束后,馗頭和面具從扮神者頭上一卸下來,就被請回到主神身旁的神龕內(nèi)作為配享,不再直接受香火供奉,這充分表現(xiàn)了它作為暫時性媒介的功能就此關(guān)閉,而“超自然施為者”的角色又回到了安坐在廟里的神像身上。
然而,正如賈斯汀·巴瑞特等人所說,在超越直觀的、較復(fù)雜的“神學(xué)的理論”底下,人們通常會同時懷抱著一種符合直觀的“媽媽的理論”,并且長期無視二者間的矛盾,視場合的需要而在二者間采擇其一。同樣的,高淳的老百姓對“超自然施為者”的認(rèn)知恐怕也不止于上述那套能從語言/修辭規(guī)則還有儀式操演過程中習(xí)得的觀念,從而一貫地把馗頭和面具視為“媒介”——把神靈與人體短暫匯合成肉身神的媒介。這種超越直觀的“神學(xué)的理論”當(dāng)然存在,否則無法解釋高淳人依然恪守的語言和儀式規(guī)則,但似乎還有一種更貼近直觀的“媽媽的理論”潛藏在底下,那就是把馗頭和面具當(dāng)作有超自然力量的施為者本身而非其媒介,也就是說馗頭和面具本身就有法力,或者干脆說它就是神!
為了避免“拜物教”或“圖騰崇拜”的污名,時下的人幾乎肯定會盡力把“媽媽的理論”關(guān)在潛意識里,但是眾多的認(rèn)知研究早已經(jīng)通過實(shí)驗(yàn)確認(rèn)對于“有意識的施為者”的超級敏感是人類的天性,他們認(rèn)為這種具有適應(yīng)優(yōu)勢(adaptive advantage)的認(rèn)知傾向就是宗教的認(rèn)知根源。這種夸張到變態(tài)程度的敏感促使人類在任何情境中都傾向于假定有“有意識的施為者”存在,并有把“有意識的施為者”角色強(qiáng)加到任何物體身上的傾向。而且,在偵查或賦予“有意識的施為者”角色的過程中,人類普遍會以有臉孔的物體為首選對象,尤其是人的臉孔,特別是帶有某種表情、表現(xiàn)某種情緒的臉孔!因此,上頭布滿了小臉孔的馗頭以及它底下的那一副大過人臉數(shù)倍的面具,可以說是老實(shí)不客氣地針對人類這種天賦的認(rèn)知傾向而設(shè)計(jì)的,召喚著深藏在高淳老百姓腦中的“媽媽的理論”。
特定“神學(xué)的理論”的陶冶,可能會使人對數(shù)字、文字、語言(含誦經(jīng)、咒、論說)、物件(含器物、建筑)、空間等某些類型的經(jīng)驗(yàn)元素特別敏感,相對于此,“媽媽的理論”最突出的認(rèn)知傾向就是對人臉(含容貌、表情)以至于整個人形(含裝扮、配件)的特殊關(guān)注。與這種認(rèn)知傾向相呼應(yīng)的行為表現(xiàn),首先是近乎偏執(zhí)地在宗教生活中一切可能的界域里塞進(jìn)人臉和人形,而為了避免無聊的重復(fù),在創(chuàng)造這些人臉、人形的過程中也會摻入一些其他動物的面容和形象特征,再加上多種裝扮、配件的設(shè)計(jì)與錯雜的排列組合來制造出各種細(xì)微的分別。此外,另一個行為上的表現(xiàn)就是對于“變?nèi)荨钡膹?qiáng)烈興趣,這一興趣的基礎(chǔ)在于傾向于認(rèn)為“變質(zhì)”和“變?nèi)荨笔且惑w的兩面,這話有兩種可能的理解方式,一種是說質(zhì)變必然導(dǎo)致外貌改變,這點(diǎn)還可能被理智勉強(qiáng)接受,然而,對“變?nèi)荨钡膹?qiáng)烈興趣正好就來自理智肯定會跳起來反對的另一種理解——“變?nèi)荨笨赡軐?dǎo)致“變質(zhì)”,即改變外觀容貌可能徹底改變一個人,比如一個人頂起馗頭、戴上面具,可能就變成了祠山大帝,一個老旦演員穿戴好行頭,拄起龍頭拐,可能就變成了佘太君。
為節(jié)省篇幅,“媽媽的理論”所陶養(yǎng)的兩個行為傾向在高淳廟會中的體現(xiàn)似乎就不必再細(xì)數(shù)了,讀者只需稍微想像一下“出菩薩”中的馗頭和面具、充斥在抬閣、龍吟車等各種游藝表演中扮神仙的人們、酬神戲臺上上了大妝的演員們便足夠了。
三、葦航庵的禳解法*為保護(hù)隱私,本節(jié)所提及的地名、廟名、人名均為化名,請勿對號入座。
驊騮村的葦航庵可說是“媽媽的理論”所創(chuàng)造的一個奇觀。
葦航庵傳說始建于元末明初,但目前的葦航庵始建于二十世紀(jì)末,是將一間農(nóng)家民房稍微改造而成的,之后信徒日增、香火漸旺,所以陸續(xù)把鄰近的幾間民房也拿來改成了殿堂,但擴(kuò)建至今,其建筑總面積大概也不過2百多平米。葦航庵至今沒有建起完整的圍墻或籬笆把整個建筑群圈起來,房屋的外觀色調(diào)也都和一般農(nóng)戶無甚差別,更沒有招眼的露天佛像、碑碣等,唯有的一個戶外香爐也比較小,能完全隱藏在兩棟緊鄰的殿堂中間,所以若不是走到屋旁幾米之內(nèi),很難察覺這是一座廟。
然而,外觀的低調(diào)素樸,只是讓這座廟色彩絢爛的內(nèi)部益發(fā)令人驚訝!此地的神像之多,讓人不由得聯(lián)想起印度教的廟宇。分布在該廟的五個大小殿堂中的,除了大、中型神佛立體坐像二、三十尊,還有上百個信徒送來分享香火的小型陶瓷觀音、財(cái)神、關(guān)帝等神像。不過,雖然葦航庵的這些立體神像似乎特別擁擠了些,但這并不算特別,許多不在道協(xié)、佛協(xié)領(lǐng)導(dǎo)之下的廟都有類似情況(見彩圖13)。
葦航庵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是它在墻上張掛的上百幅平面神像畫,其中有很多,特別是比較大的那些,圖中描繪的都不止一位神明,而是中間一位較大的主神搭配兩名侍從或使者,所以這些畫中呈現(xiàn)的人臉、人形總數(shù)應(yīng)在數(shù)百之譜!這上百幅畫中最大的大約有1.2米高、1米寬,裱褙在規(guī)格一致的木板上,整齊排列在正殿對門的門房里(即一般佛寺中放置韋陀和四大天王的地方),筆者判斷這也是葦航庵中最早的一批畫像。
此外,葦航庵里還充斥著其他大量較小的神像畫,從約四開、八開到明信片大小的,掛得琳瑯滿目,其中有相當(dāng)一些的構(gòu)圖風(fēng)格與這些大畫像的傳統(tǒng)風(fēng)格偏離較遠(yuǎn),比如描繪武裝的男神正在拉開武打架勢、女神的侍女正在撩水袖等動態(tài)(見彩圖14、15),這些顯然是以戲曲角色的裝扮以及對劇中場景的“抓拍”為仿效對象的構(gòu)圖,與傳統(tǒng)神像畫中神明幾乎都是安穩(wěn)的正坐或正立的主流風(fēng)格相當(dāng)不同。
此外,甚至還出現(xiàn)了一些徹底背離傳統(tǒng)風(fēng)格的畫,比如有幾幅顯然運(yùn)用了西洋透視法畫的、非常類似于電影海報(bào)的畫,還有極少數(shù)如以下這幅甚至不能稱為“神像畫”的畫(見彩圖16),其內(nèi)容是某個意象或場景,似乎是寓言故事的插畫,或者是夢中所見情境的再現(xiàn),完全沒有出現(xiàn)人臉或人形。
這些畫究竟是哪來的?據(jù)葦航庵的住持,也就是這座廟的主要重建者兼唯一的管理者賢風(fēng)和尚所說,一切都是十方善信們自己主動畫了送來的,他只是提供場地而已。事實(shí)上,這座廟之所以會從最初的兩間農(nóng)舍逐步擴(kuò)大成如今的五間,主要就是因?yàn)樾磐剿蛠淼纳裣窈蜕裣癞嫈[不下了,所以信徒們自發(fā)募款,一步步把鄰近的農(nóng)舍買了下來,并入葦航庵。
那么,此地的善信為什么如此熱衷給廟里送神像和神像畫,甚至于要為此出錢擴(kuò)建寺廟呢?因?yàn)檫@是一種治療怪病的方法!被人稱為葦航庵“第一大護(hù)法”同時也是賢風(fēng)和尚的“大弟子”的當(dāng)?shù)刂跋赡铩贝浞寂浚沁\(yùn)用這種禳解法的高手。據(jù)她所說,每當(dāng)有人得了醫(yī)院查不出、看不好的怪病,或者運(yùn)勢很背、家里不平安的時候,她就點(diǎn)香叩問她“頂”的菩薩(她有時稱之為干媽、干爹),請菩薩指點(diǎn)問題癥結(jié)和禳解的辦法,結(jié)果答案通常是患者族中的先人或當(dāng)境的地方神來憑附、騷擾患者,而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為他們塑像,經(jīng)濟(jì)條件不行的就畫像,然后送到廟里讓他們享受香火供奉,尤其是患者本人,理論上必須定期到廟里向自己“頂著”的神靈祖先上香獻(xiàn)供。
在這套禳解的程序中,最麻煩但也最有趣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就是塑像或畫像,患者必須在請工匠塑像或畫像時,盡可能的向后者說清楚所要刻畫的神靈祖先的長相、身材、穿著、配件、姿態(tài)等等,因?yàn)椤跋癫艜`”,如果刻畫得不像,得不到神靈祖先的認(rèn)同,這套做法就不靈了。正是在此,翠芳顯現(xiàn)了超越其他眾多仙娘的本事,那就是她特別擅長于幫助患者獲得夢示,使患者得以在夢中看見自己“頂著”的神靈祖先,并善于通過談話幫患者逐漸梳理清楚她們在夢中看見的影像。此外,翠芳很尊重患者自己陳述的夢境而不囿于傳統(tǒng),不會迫使患者和工匠按照傳統(tǒng)神像畫的模式,非但歡迎傳統(tǒng)戲曲人物廣告畫片風(fēng)格的作品,甚至也能接受沒有人物形象的插畫和電影海報(bào)風(fēng)格的畫作,只求盡量傳真地再現(xiàn)患者的夢境所見。
成就了今日葦航庵的這套禳解法,顯然是在高淳廟會文化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來的。說得更精確一點(diǎn),禳解法和廟會二者共同的根底,就是“媽媽的理論”以及它所陶養(yǎng)出來的認(rèn)知傾向。充斥在葦航庵里的人臉和人形,仿佛是填滿了廟會經(jīng)驗(yàn)的馗頭、面具、游行隊(duì)伍里扮神扮仙的人、尤其是酬神戲臺上粉墨登場的演員們的一幅倒影,至于通過繪制形容影像來確認(rèn)神靈祖先的身份的做法——加上“像才靈、不像就不靈”這種起效原則的強(qiáng)化——更是直白地暗示“形容影像”幾乎就等于神靈本身,而這就是促使人們在路頭對祠山大帝、二郎真君的“肉身顯化”焚香跪拜的直觀意識。
不過,和高淳的廟會一樣,葦航庵的這套禳解法也并非全然依賴“媽媽的理論”,“神學(xué)的理論”還是在當(dāng)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具體的儀式做法方面,“神學(xué)的理論”所蘊(yùn)涵的媒介、圣俗位階與權(quán)限等觀念是不可或缺的關(guān)鍵元素。這話如何理解?很簡單,只要認(rèn)清葦航庵的禳解法是“出菩薩”儀式套路的演繹,便可一目了然。
依照“神學(xué)的理論”,“出菩薩”是神明通過馗頭面具等媒介與人體結(jié)合而有了施為作用(也可說是“駕馭”了人體),成為特殊的施為者(“來神”是其最高展現(xiàn)形態(tài))。這就意味著只要把馗頭面具等媒介和人體分離、卸下,神明就會離開人世而趨于隱沒,社會恢復(fù)常態(tài),凡人取回自己的施為者身份,只剩下在廟中端坐的神像作為神明的代表,被動地聽取人的祈求。把葦航庵的禳解法與此相對照,不難發(fā)現(xiàn)它就是以“來神”的情況來構(gòu)想患者的處境:患者“頂著”神靈祖先而偏離了常態(tài),正如頂著沉重馗頭面具的扮神者陷入了迷狂。因此,正如后者的解除法是要先把馗頭面具卸下,也就是馬上把人體和神力的媒介分離開,祈禳的工作原理也是要把患者和他頂著的神靈祖先分離開。然而,要解除“來神”時,我們能針對馗頭面具這些物質(zhì)性的媒介來施展操作,被憑附的患者頭上卻沒有這樣的東西,所以禳解法就必須創(chuàng)造出某種類似的媒介物來作為操作對象。要進(jìn)行這個步奏有非常多可能的選項(xiàng),比如寫出鬼神的名字*例如在河北無極、蠡縣等地,與此相類似的儀式被稱為“拉單子”、“立堂”,就是把眾多神祇的名字寫在紙上,然后貼在木板上做成牌位,在家中設(shè)香案供奉,參見楊德睿《事、功、斗:河北省無極縣S村的迷信世界的理論意涵》,《社會理論論叢》2009年第5輯;楊德睿《在家、回家:冀南民俗宗教對存在意義的追尋》(香港樹人大學(xué)當(dāng)代中國研究論文系列第二輯),香港:香港樹人大學(xué)當(dāng)代中國研究中心2010年;楊德睿《傳承:認(rèn)知與宗教人類學(xué)的探索》,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第196-257頁。、把患者常穿的衣服鞋帽做成代替患者的人偶等等,但由于“媽媽的理論”的強(qiáng)大影響,高淳的仙娘選擇了給神靈祖先塑像或畫像。
事實(shí)上,塑像或畫像就是把鬼神和患者分離開來的開始。患者在仙娘的指示、協(xié)助下,第一步是接受“自己的困境是外力造成的”這一假定,第二步是盡力“看清楚”這個外力的影像,第三步是用語言(不時加上信筆涂鴉)來描述給仙娘和刻工畫工聽,第四步是親身看到、摸到用顏料、木料等物質(zhì)材料呈現(xiàn)的那種困擾自己的神秘外力。以上這四步完成時,神秘外力已經(jīng)被呈現(xiàn)為外在于患者身心的、有形體邊界的媒介之物,這就好比把之前缺失的馗頭面具給補(bǔ)上了,接下來就可以回到出菩薩的結(jié)束程序了。于是,第五步是將這個代表外力的媒介物體放到遠(yuǎn)離患者生活空間的葦航庵里去,把它安放在神圣位階較高的神佛身邊的從屬配享位置。第六步是再以香燭供品等物定期地來奉祀那個媒介物,使它更安定地系屬于葦航庵而不至四處游走。這最后的兩步和出菩薩結(jié)束后把馗頭面具送回神龕里,安奉在主神側(cè)后方的位置享受配享基本上是一樣的,至此人神分離,各安其所,患者又回到凡俗生活的常軌。
五、結(jié)語
以上我利用高淳的案例,論證了特定廟會傳統(tǒng)中最富于感官刺激性的儀式物件(在這里是指馗頭和面具)和情景(出菩薩和演酬神戲),可能會特別強(qiáng)化某種天賦的認(rèn)知傾向(“媽媽的理論”),從而培養(yǎng)出特定的美感風(fēng)格(對人臉和人形特別強(qiáng)烈的興趣)以及相配適的行動套路(四處刻畫人臉和人形的癖好、對實(shí)踐和觀賞“變?nèi)荨钡鸟焙?,而這種美感和行動的套路是有擴(kuò)散性的,有可能對廟會之外的生活領(lǐng)域(禳解災(zāi)病)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
除了記載和報(bào)道當(dāng)前高淳的獨(dú)特廟會形式、葦航庵的獨(dú)特禳解法以外,這份案例研究更核心的目標(biāo)在于希望能證明:宗教人類學(xué)的廟會研究,不僅限于結(jié)構(gòu)分析、意義闡釋和集體記憶這三大傳統(tǒng)路徑,新興的宗教傳承/傳播研究也是有極大潛力的一種路徑。雖然迄今為止,宗教傳承/傳播研究的既有文獻(xiàn)中似乎還未出現(xiàn)針對廟會等周期性宗教慶典的成果,也針對當(dāng)代中國本土宗教案例的討論也才剛開始起步*Hornbeck, Ryan G., Barrett, Justin L. & Kang, Madeleine. eds. 2017 Religious Cognition in China: "Homo Religiosus" and the Dragon. Springer似乎是此一話題領(lǐng)域中的第一本論文集,另可參見楊德睿《傳承:宗教與認(rèn)知人類學(xué)的探索》,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但是我們并不難從這一領(lǐng)域的既有文獻(xiàn)中攫取極具啟發(fā)性的暗示,使我們很有可能在針對中國廟會的研究中斬獲新的見解,這種見解不僅能充實(shí)宗教傳承/傳播研究,也可能是對克利福德·格爾茲對整個宗教人類學(xué)的所提出的號召的具體回應(yīng)——事實(shí)上,本文嘗試說明的正是高淳的民間宗教傳統(tǒng)如何通過廟會“喚起某種鮮明的習(xí)性集合”,使高淳的信徒們的“行為舉止與經(jīng)驗(yàn)性質(zhì)具有一種長期特征”。
當(dāng)然,本文提出的見解還很初步而粗淺,尤其是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重大缺漏未加以好好處理,那就是相對于“媽媽的理論”的“神學(xué)的理論”。這種比較“反直觀”或“超越直觀”的認(rèn)知慣習(xí),傾向于將超自然施為者及其施為作用假定為非感官所能把握的非物理對象,因而也就慣常把感官可及的事物想象成超自然施為者的媒介或象征、符號,并有種習(xí)慣性的沖動要把一切存在編入某種上下位階秩序(而且往往是以越非物質(zhì)、越非感官所能企及者為高、為上、為有權(quán)力,而越能為感官所把握者為越卑下荏弱)。這套“神學(xué)的理論”也明確地出現(xiàn)在高淳的“出菩薩”和葦航庵的禳解法之中,但本文并沒有善加挖掘這條線索可能引出的另一番境界,這個遺憾只能留待日后再來彌補(b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