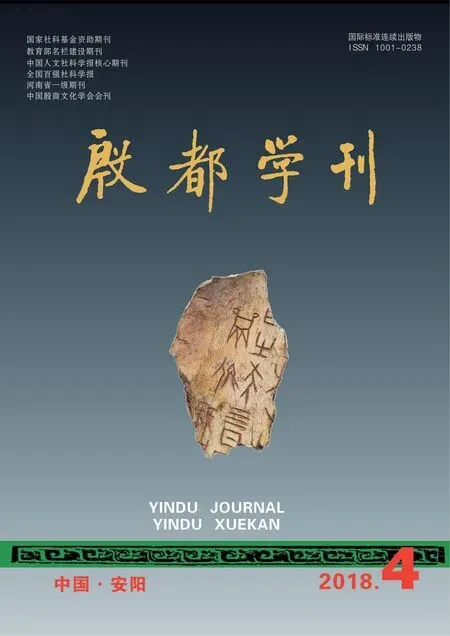章學誠對民國學者方志編纂思想影響初探
王旭東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其方志學思想對民國志家影響很大,前人對此的研究也有眾多的成果。比較著名的有倉修良、葉建華著《章學誠評傳》,對章氏的生平及學術主張等有較為系統的研究;而對于章氏的方志學思想研究者也著述頗豐,喬治忠在《章學誠方志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一文中,結合章學誠的修志實踐,分析了章氏方志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1];宏觀研究章學誠方志思想的有張君炎的《試論章學誠的方志學說》[2]、劉耿生的《論章學誠〈文史通義〉的方志學思想》[3]以及沈松平《章學誠方志思想的再認識》[4]。更多的是對章學誠提出的方志學核心思想的細化研究,如孔祥龍著重關注章學誠的譜牒入志思想,在《章學誠譜牒入志思想淺析》一文中分析了譜牒入志表述氏族的主張對方志學和譜牒學發展的影響[5];劉克明則著眼于分析章氏的圖學思想,在《章學誠方志圖學思想探述》一文中強調了章氏的圖學思想對于促進中國圖學的發展和地方史志中圖樣的編繪的積極作用[6];馬春暉則在《章學誠方志藝文思想探述》一文中詳細論述了章氏對于方志藝文志的編纂理論及其闡述[7];對于章學誠的方志編纂主張的研究則有何林夏《論章學誠的“方志立三書”說》[8]、楊軍仕的《試論章學誠關于方志人物記述的主張及實踐》[9]以及張鐵誠的碩士論文《從“六經皆史”到“方志立三書”》[10]等。關于章學誠方志學思想影響的研究則有宋佳的碩士論文《論章學誠的方志思想在后世的影響》[11]、薛艷偉的《論章學誠的方志學說在晚清之回響》[12]。但是從近代轉型的角度研究章學誠的方志學思想的文章還較少,就筆者目力所及,只是散見于如劉開軍的《傳統史學理論在民國史學界的回響——論劉咸炘的章學誠研究》[13]、沈松平的《從余紹宋看民國志家對傳統方志學理論的揚棄》[14]等,尚未見整體影響的有關研究。故筆者不揣淺陋,試圖通過本文探究民國學者對章學誠方志思想中的近代因素的繼承、發揚與民國修志實踐的關系,側重通過傳統方志學和西學兩個方面來分析對民國方志編修的影響,以求推動在方志學的近代轉型研究的深入。
一、章學誠方志學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章學誠關于方志學有系統的論述,從方志的性質到修志體例均有涉及,對此前人已有較為詳盡的論述,在此不加贅言,僅就其理論中雖未能突破傳統方志學理論束縛但已包含有近代因素的部分內容加以介紹。
章學誠通過多年的修志實踐以及與同時代的志家交流、探討,對于方志撰修有獨到的見解,在其著述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方志理論,其中不乏具有近代意義的創見。關于對方志的認識方面,他提出“志屬信史”[15](《修志十議》,P846),反映了其“六經皆史”主張的發散,這一主張肯定了方志“史”的性質,厘清了方志作為史書與地理類書的區別,使得方志在地位上有所提高。章氏關于方志“史”的性質的闡述雖然并非首倡,其認識卻十分獨到。他強調“方志乃一方全史”[16](P56),這就與近代方志編修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民國諸多方志即在傳統志書所涵蓋的內容外將記述范圍擴大,尤其是對經濟的關注,使方志記錄的內容更為完備。此外,還應看到章氏在這一主張里所強調的“信”,既屬信史,其內容的編纂即需考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15](《修志十議》,P843),強調保證志書的真實可靠,而不能一味地對前史加以因循抄襲,這個主張也符合近代對方志的真實性與可靠性的要求。
章學誠關于方志的作用也有較多闡述,其所提出的“資政”與“存史”兩大作用尤能代表章氏方志理論中的近代因素。在章學誠看來,方志的一大功用在于“經世”,他強調方志應該有裨風教、資世。這就必須避免以往方志抄撮舊史、編排附會的現象,而賦予方志本身以功用。他認為“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生勇,貪者廉立。”[17](P1288)體現有一定的經世致用思想,雖然章氏主張的道德標準于今看來不免有階級局限,但是其經世致用的意識對后世方志的編修產生了巨大影響。對于存史,章氏針對明清修志人員多為臨時編湊,因此主張設置常設機構,其認為“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因此主張“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后行也。”[15](《州縣請立志科議》,P589)這一主張幾可視作當今“方志辦公室”的雛形,體現出了章學誠超前的學術意識。
對于方志編撰理論,章氏也以遠超同代志家的前瞻性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創制統一的修志體例。鑒于以往方志編寫體例不一的混亂情形,章學誠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方志義例,即“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15](《方志立三書議》,P571),學界對“方志立三書說”雖然褒貶不一,但是對章氏所倡的統一方志編修義例的意識多持肯定態度。針對以往方志體例漫渙缺少統屬的問題,章氏提出了以“皇言”、“恩澤”作為統領,強調“史之有紀,肇于《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于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于是其主張“至于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15](《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P703)章氏的這一主張雖然囿于時代所限,仍帶有皇權至上的思想,但其闡述的修志要有綱領的思想值得肯定,章氏后來在《湖北通志》的序例中又有關于“編年紀”的論述,這就較“皇言”“恩澤”進步很多。“史以紀事為主,紀事以編年為主。方志于紀事之體,往往缺而不備,或主五行祥異,或專沿革建置,或稱兵事,或稱雜紀,又或編次夾雜,混入諸門之中。不為全書綱領,今取自漢以后,凡當以年次者,統合為編年紀,附于皇朝編年紀后,備一方之記載。”“紀以編年為名,例仿綱目。大書分注,俾覽者先知古今,了如指掌。”[18](P5)如此一來,則一改以往方志散漫無次的狀況,有一條脈絡可循。這一主張經后人發展形成大事記,在后世所修的諸多縣志中都有體現。
此外,章學誠還批評了以往方志不注重圖學,“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于史裁也。一則廁于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為系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為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茍為悅人耳目之具矣……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即楮幅之廣狹,為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繼而提出了“今以開方計里為經,而以縣鄉村落為緯;使后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15](《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P733),這一主張雖仍未解決舊方志輿圖在邊界上極為模糊這一巨大缺點,但其提出的“經”“緯”概念已較前人所修輿圖具體不少。尤其是其所強調的“開方計里”的輿圖繪制方法,較之以往方志中較多采用的星野圖更為實用。其后又在《湖北通志》凡例中強調“諸圖開方計里,義取切實有用,不為華美之觀”[18](P5),章氏對方志中圖的作用認識深刻,在其所修撰的志書中也較多運用了圖作為輔助。
二、民國學者對章學誠方志學思想的發展
章學誠的方志學思想從問世以來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以民國時期最為有代表性。胡適、梁啟超對章學誠的推崇使得研究章學誠的學術思想一度成為顯學,“民國方志學家,無論是繼承或者批評、揚棄傳統方志學理論,都言必稱章氏之學,其中不乏如李泰棻、傅振倫、黎錦熙、陳訓正、余紹宋這樣的佼佼者。”[11](P43)各志家對于章氏的方志學思想也有較多述及,章氏儼然成為傳統方志學的標志,如傅振倫編著的《中國方志學通論》,在篇五用了整整一章來論述章學誠的方志學,李泰棻更是在其著作《方志學》中用了兩章或介紹或駁議章學誠的方志思想,萬國鼎、壽鵬飛、瞿宣穎等方志學家也都各自在論文中對章學誠的方志思想有所論及,而民國志家對前文提到的章氏方志學思想中的近代因素尤為關注。
雖然民國時期關于方志性質的爭論仍舊存在,但是主張方志為地理類書者業已式微,方志“史”的性質為人所接受,“志者,史也。史以明治亂興衰之故,志以補郡國利病之書”[19]“方志者,以地方為單位之歷史與人文地理也”[20]民國諸志家基本認可章氏所倡“志乃信史”的觀點,在方志編修上也強調資料來源的可靠、詳實,“一切材料,皆有來源,擷入篇中,即非原文,必注出處。所據舊籍,固應篇卷分明;即系新材,亦當源頭清楚,如調查、報告,檔案、試卷,凡所根據,逐段注明。雙行小字,無礙行文;約旨要刪,非同集句。所以昭質實謹嚴之義,免模糊影響之譏。”[21](P129)隨著新史學運動的發展,民國時期的方志理論家已經開始用發展的眼光研究方志,李泰棻就已經用進化論的觀點來研究方志了,他認為“方志者,乃記載及研究一方人類進化現象。”[22](P2)這不可不謂一大進步。
關于方志的作用,民國志家對于章氏提出的“經世致用”思想基本都予以接受,并且為之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由于時代所限,章學誠所謂的“經世致用”不過是強調“裨風教”與國史提供材料,民國學者對之有所揚棄,民國時期的社會環境整體注重民事、強調經濟,學術方面又由于西學的廣泛傳入,民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將方志學與西學進行聯系,有志家將方志的作用闡釋為“夷考方志之始,蓋出自晉《乘》、楚《梼杌》、魯《春秋》,而其綜賅刑政、禮樂、風土、山川則托體書志,揆之近世科學,殆合史地而一之。史與地殊科而同用,相乘而互翼,原無嚴格之界劃。故吾國四郡屬地于史,而西洋地理學家又多以地釋史,合史與地然后能經緯旁通,而為一切國家建設之所根據,此方志之為用也。”[23]除此之外,更多的志家還是將方志視作對于民生實用有參考價值的典籍。
章學誠提出的州縣設立志科議,在民國也為政府所關注,并根據實際情況對所謂的“州縣志科”的內容做了調整。1928年,譚延闿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后,主張全面開展各地方志的撰修工作,民國政府于1929年12月頒行的《修志事例概要》中即規定“各省應于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志館,由省政府聘請館長一人,副館長一人,編纂等十人組織”[24](P139),而《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大綱》也強調“市縣政府所在地應設一文獻委員會為永久機關,對于本市縣文獻材料負保存征集之責,各區得設分會分任調查事宜;文獻委員會由市縣政府組織,以教育局長、各區區長、各學校校長、各圖書館館長、各教育館館長為當然委員,并得延聘本地方之碩學通儒及熟悉地方掌故者為委員,由各委員互推一人為委員長。”[25](P138)盡管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這一規定并未得到貫徹實行,但是亦足以體現民國志家乃至決策者對章學誠方志所提的州縣設立志科建議的接受及發展。
章學誠所提出的創制方志編修體例的主張得到了民國多數志家的認同,但是其所創制的方志義例卻沒有得到太多的認可。“方今事變,皆從前所未有,方志為一省、一縣紀事之書,近日社會狀況,與曩日大殊。即政府之建設,亦月異而歲不同,據事直書,方為信史,烏得以舊例相繩乎?”[26](P179)至于章氏為解決志書缺乏統屬而提倡的“皇言”、“恩澤”等紀,更是被民國學者批判封建和為專制政體服務,但是對于章氏提倡的“編年紀”卻予以接受,民國志家將之發展為“大事記”,在民國編著的多本志書中均有體現,或列于志前,或殿于志后,以為全志綱領。
關于在方志中圖的運用,劉咸炘在《雙流足征錄》里有所闡發,他肯定了方志中圖的作用,但是認為只有圖還遠遠不夠,強調圖表并用。“考郡縣之沿革,不難于名之廢置,而難于疆域之廣狹。疆域之變遷,尤重于名,往往其名則是,其地則非。”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惟是古地志書,皆不詳疆域。疆域非圖不明,而圖皆載縣名,無輪廓。元和、太平、元豐諸《志》,雖載四至八到,僅及郡而不及縣。至于域有徙治,鄉有改隸,茍其名未改,則皆不書。晚近統志,縣皆詳至到矣,縣志亦各載鄉名,且有圖矣,又止一時,而非通古。”于是他認為“惟就沿革總圖,觀其四境之大概。而世之修志,又僅立沿革表,不作沿革圖,此志地者之大缺也。”[27](P969)基于這樣的認識,他發展了章學誠關于圖學的主張,創造性地提出了沿革表與沿革圖并舉的志地方法,制沿革圖,割取四方并注寫古名,再制沿革表中以古名、詳注鄰境,附在每代之后,這一主張雖有繁復,但較前人志書在疆域沿革方面確實便于理解查看。更多的志家則是肯定章學誠主張制圖要“開方計里”,并自覺將這一思想應用于編纂志書的實踐中,用實地精測或直接將經緯地圖編入方志,使民國方志的地圖更為可靠明晰。
三、傳統與西學雙重影響下的方志編修實踐
晚清以降,學術界愈加受到西方文化沖擊,在西方學術思想與傳統學術思想的共同影響下發展,方志學領域也不例外。民國志家非惟在理論界進行探討,更是直接將各自主張付諸于修志實踐,在這一時期,有一大批方志付梓,據統計,民國時期編纂的方志達1187種,[28](P324)其中不乏諸如《城固縣志》《重修浙江通志稿》《泗陽縣志》等深受西學影響的志書,也有受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傳統方志編修思想影響較多的《龍游縣志》《歙縣志》《奉天通志》等志書。但是深入探察這些民國方志則會發現這些志書在修志理論上無不帶有傳統與西學的雙重影響,體現出濃厚的近代氣息。
在民國縣志的編修上,余紹宋的《龍游縣志》最能體現受章學誠方志編修思想的影響,余氏在體例上甚至直接用了章氏所主張的“掌故”及“文征”,可以說余志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章學誠的修志思想,梁啟超在該縣志的序中對此大加贊賞。余氏雖有“至其一時代之政治制度,有所變易,盡可因其需要而別立新裁,本無循用舊志體例之必要。況不問舊志體例適用于今時與否,而但依類指歸以為之續,則非依樣葫蘆,即是削趾就履,其非良志,可以斷言”[29](P156)這樣的論述,但是編修《龍游縣志》時在體例上對章學誠所編諸志模仿頗多,以至于創新不足而為人所詬病,傅振倫即有“今觀《龍游志》全書,知梁氏之言,實屬妄譽溢美之詞。不僅不能貫徹自定體例,且缺點很多。”接著列舉余志的六大缺點,他認為:“此志僅可說是一邑文獻的私家雜記,既未實地調查,不合現實,談不上有裨實用的地方志書。雖經啟超的荒謬宣傳,并不能抬高其學術價值。”[30](P63)但是亦有值得稱道之處,受當時西方現代科學、社會科學的影響,余紹宋在志書的編纂方法上也體現了時代特色,他在《浙江省通志編纂大綱草案》中廢輿地圖立經緯度數,注重民族、社會、黨務、實業等內容,在古跡考中大量使用攝影,且余氏強調“凡能以表表明之事,悉用表,附于各部門之內”[31](P22),這就使其所修的《重修浙江通志稿》較《龍游縣志》更富現代特色,體現了其方志編修思想的變化,更具有了科學性,有學者指出:“圖與表相結合,相得益彰。除此以外,《民國重修浙江通志稿》還使用了前人未曾用過的現代科技——照片,如名勝、特產、陵墓、古物均附照片于后,如此刪繁就簡、文省事明,使志稿眉目清楚,也容納了更多的信息,與章志相比又進了一步。”[14]
許承堯總纂的《歙縣志》也體現出明顯的受傳統與西學雙重影響的特點,許氏早年方志編修思想受西學影響較大,他在《歙縣修志私議》中寫道“蓋值立憲預備年限詔下,國是大定,自治基礎萬端紛紜之日,必不暇斤斤侈文墨、口佚聞以事繢飾,而當求確有效益于今后之設施,故第一首宜著手者為測繪也,地圖必用今法,必須精細,此為萬政之原始,百端之所憑藉。若因襲茍簡,用舊圖,或用某某之新造圖,以之計里索村鎮,且不核實,他何論,是絕無所用也。第二宜調查實業,今后謀自治,不先從實業肇基,則地方稅無所出,必貧竭,百事不舉……第三宜調查戶口,某年月某村某鎮,男若干,女若干,學童若干,某土、某客,賈外者若干,某某業,某無業,宗教若何屬,必詳書。以上皆地圖之附屬品,隨測量時調查,必精確,皆舊志所未詳,而今必詳者,為其可以備籌畫,資考核,確有效益于今后之設施,故須以全力注之也。”[32](P242)關于地圖、實業、戶口的三點主張表明許承堯本人早期的方志編纂主張受西方社會思想影響較大,但是后期著手修纂《歙縣志》時,其早年的諸多觀點并未落實。民國二十六年刊刻的《歙縣志》只在輿圖和分野方面較之舊方志有所改善,民國《歙縣志》地圖有經緯,有例圖,“程君霖生有志精測,曾捐資數千金要汪君采白諸人任其事,實地測繪三年乃成。于山川脈絡最為詳密,因商之程君得攝影本一襲。惜圖中村落仍無標識,乃更加勘察增益并易原圖,陰蔭式山脈為暈滃式以求簡顯,庶將來政治軍事皆可取資焉。”[33](P12)此外很明顯的一點是改傳統志書中沿襲不衰的“分野”為具有科學依據的“晷度”,體現出許志在修志方法上的科學性。但是該志也有諸多受傳統影響的地方,如在體例上仍舊沿用章學誠等傳統志家主張的列女傳,食貨志等,在內容上用卷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共四卷(《歙縣志》共十六卷,筆者注)記列女,且多以節烈入志,食貨志亦多遵舊志,表明該志仍受傳統影響較大。
民國時期編纂有大量志書,但是多為縣志,通志中付梓刊刻的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王樹枬、吳廷燮等編纂的《奉天通志》,在其敘中有“奉志雖用舊例,統名曰志而敘大事、人物綦詳,蓋參用章氏之法,以備一方之史。似舊實新,似因實創。”[34](P1)從奉志體例來看,基本延續了傳統志書的修纂體例,但是內容有所變更。例如改傳統方志中的食貨志為田畝志、實業志、物產志、財政志分列,體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尤其對實業志的編纂,已經跳脫了舊方志只志方物的羅列現象,對奉天省的農、工、商、礦、林、漁、畜牧以及蠶業等都分卷詳述,極富參考價值。值得一提的是,奉志采用了章氏編年紀的思想,首志即為大事志共五十卷(奉志共260卷,筆者注),使奉天一省以大事為諸志之綱,條理甚為明晰。此外,王、吳二人還參與了《河北通志》的編纂工作,遺憾的是該志由于抗戰爆發而未能刊刻。從建國后依據稿本出版的《河北通志稿》來看,其體例與內容亦顯示出深受傳統方志影響但又有所創新的特點。就其編修體例而言,“凡屬舊志,如〈光緒志〉已有之篇目為〈通志稿〉沿用者,如關隘、古跡、陵墓、園亭宅墅、寺觀、科舉教育、津梁、堤閘、謠俗、方言、金石、元明列傳、職官、藝文、宦績等篇章,多以〈光緒志〉為藍本,略加損益或襲用原文等,大多未脫舊志窠臼,功力頗為不足”[35](P247)明顯體現出受傳統方志編修的影響;而就《河北通志稿》出版目錄來看,全書分地理志、經政志、民事志、食貨志及文獻志共五志,同光緒年間編纂的《畿輔通志》相比,刪去了《帝制紀》以及“星野”等篇,且“五志中于民事、食貨二志特詳,從而彰顯《通志稿》與《光緒志》之編纂旨趣明顯不同,尤以突現‘吾民族之情態’為主旨”[35](P245)這些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本志體裁,雖仍舊貫,而宗旨微有不同。方志大都詳于文獻政典,而于民事殊略,本志則于民事加詳。共和國民為重也。”[36](P5)體現出該志的編纂思想受到西方民本、科學思想的影響。
隨著民眾史觀的傳入,在方志學領域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國體改矣,修書宗旨與往日微有不同。往日修志,于民事疏略;近日修志,應于民事加詳。民主國,民為重也。”[26](P159)在民國方志的編修實踐上,部分志家是在傳統修志體例不變的基礎上對民事、事業等內容予以重視,如鄔慶時在主修《寶安縣志》時即對此觀點有所體現,“戶口、氏族、語言、風俗、宗教、實業、團體此就縣民之普通狀態言之。選舉、畢業、公職、仕宦、封蔭、人物、耆壽,此就縣民之特別分子言之。舊志詳特別而略普通。今則先普通而后特別。”[37](P3)還應看到的是,鄔氏修志雖然體現了一定程度上受西學的影響,但是傳統方志編修的思想依舊根深蒂固,如在其總纂的另一部志書《龍門縣志》中,雖是對民眾多著筆墨,但是仍受節烈操守觀念的影響,在人物志里對列女的記載依然是強調貞操、名節,即便是對民國人物也未能有所突破,《龍門縣志》收錄的民國時期僅有的何麗華、沈氏、劉氏三人,也全都是以節婦錄入,鄔氏在其方志編修實踐表現出的這種受傳統與西學影響的矛盾深刻體現出了方志學近代轉型的時代特征。另一部分志家則是變革了方志編修體例,創立了富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實業志,如前文提到的《奉天通志》《河北通志稿》等;變革傳統志書中的“望族考”為“氏族考”,如余紹宋編纂的《龍游縣志》,沈松平對這一變革的認識很深刻,他指出“章志有《望族表》,余志有《氏族考》,后者雖受前者的啟發,但兩者有很大的區別。余紹宋與章學誠對采用什么樣的家族入志所見不同。章志以門第為人志標準,而余志則破除門第觀念,意在用客觀的記載反映當地社會結構”[14]盡管這些志家都根據時代變化變革了方志體例,但還是不難看出基本框架還是沿襲以章學誠的方志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方志學,只是有所損益,呈現出明顯的在傳統與現代方志編修過渡的特點。
四、余論
作為傳統方志學的代表人物,章學誠的方志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多年的修志實踐與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其所提出的諸多主張包含有一定的近代因素,“明清史學內部潛滋暗長的近代性因素,與西方相比有異曲同工之妙。”[38]章氏方志學理論中的這些近代因素也為民國諸多方志學家所注意,結合時代發展對之進行揚棄,強調方志“史”的性質及“經世致用”的功能,發展了近代方志理論,并自覺將這些理論付諸修志實踐,又在實踐中豐富完善了方志編修理論。在民國的學術環境下,他們的理論深受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傳統方志學思想和西學的雙重影響,成書于這一時期的志書,也打上了承上啟下的過渡期的深刻烙印,使民國成為方志發展史上極富特色的一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