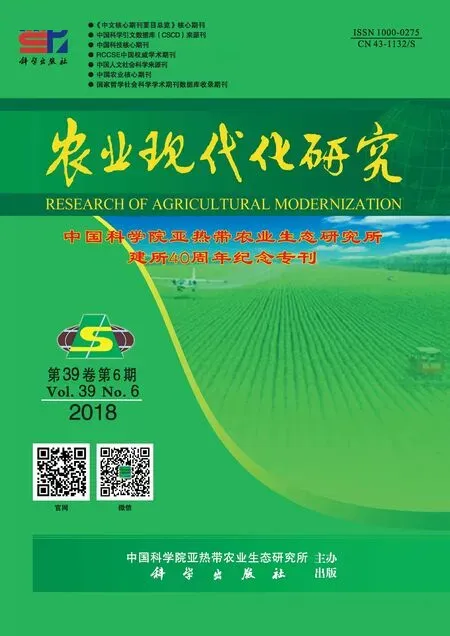洞庭湖區“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中的鼠類群落管理
張美文,王勇,李波,周訓軍
(1. 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亞熱帶農業生態過程重點實驗室,湖南 長沙 410125;2. 中國科學院洞庭湖濕地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站,湖南 岳陽 414018)
“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復雜系統,它是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通過人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因此,必須以“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思維處理我們遇到的各類問題[1]。作為地球上種類與數量最多的哺乳動物鼠類,在生態系統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也有一些種類會對人類的經濟發展和健康造成危害。以生態學的觀點看,鼠類的存在對生態系統有積極的意義,至于其為害,是人類在一些社會活動與經濟建設過程中,鼠類對人們的利益產生侵害所致。一般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生態系統平衡被打破,生態系統失去了暫時的平衡,某些適應的種群數量就有可能大暴發,進而威脅到人類生活、生產活動和生命健康,造成人類利益方面的損失。
目前,我國社會經濟處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大部分城鄉地區的生態環境狀況總體還是有利于害鼠的生存和發展。特別是在許多地區農田和村莊,害鼠的密度還較高。直接減少動物種群的數量(最為常用的就是化學方法殺滅)是人們對于自己想消滅的有害動物所采取的最為直接防治措施,也是比較常用的方法。但此時動物種群數量已高,并已造成部分的危害,而且防治需花費更多的成本(包括物質的和生態的)。但有效的措施應該是綜合分析其種群數量暴發的根本原因后,據此尋求控制其種群數量方法,從根源上控制鼠害。同時,當社會、經濟、自然條件發生改變而影響到生態環境發生改變時,適時地評估這些改變對鼠類種群產生的影響,將有益于提前采取措施,預防害鼠種群的大暴發。但無論如何,都應以“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觀念看待鼠類群落或種群及其成災的原因,采取的控制對策也應與之相適應[2]。
在洞庭湖區,鼠類群落最適棲息地就有住宅區、農田區、丘崗區和湖灘草地等,在其中形成相應的群落,各自占居一定的生態位。它們的食性也有雜食、草食之別,常對工農業生產形成危害,其互相填充產生的總體危害很大。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所野生動物生態學科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洞庭湖區域從事鼠類群落和種群的研究。對洞庭湖嚙齒動物主要種類的生物學和生態學特性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背景資料,據此研究提出了相應的鼠類控制技術和藥物。總體以“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為基礎分析鼠類群落的發生、發展和演替,以及提供相應的防治對策,可為管理鼠類群落數量提供參考。
1 影響鼠類種群的自然因素
1.1 害鼠生物學特性研究
動物選擇棲息于一定環境中,是長期對環境適應演變的結果。許多因子都能對嚙齒動物選擇棲息地產生影響。這些因子除了溫、光、水、氣、土等生態因子外,還包括捕食、競爭、食物和人類活動等因素。在自然條件下,很多因素可以調節和制約種群增長,因此,自然種群不可能長期連續增長。一個物種被引入或占據適宜的棲息地后,其種群開始增長,經過增長而建立起來的種群在各種生態因子的影響下,可出現不規則或規則的波動,也可長期保持相對穩定,有時種群可能出現大暴發,有時也可出現大崩潰,有時亦可出現長期下降甚至滅亡,這與每個物種本身的生物學特性有很大關系。通過對以湖南省為主以及周邊省份(主要為長江流域)的實地研究調查,初步掌握了洞庭湖區域害鼠種類及其群落組成特點。對當地農業害鼠主要種類——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3-4]、東方田鼠(Microtus fortis)[4-5]、黑線姬鼠(Apodemus agraricus)[3-4]、黃胸鼠(Rattus tanezumi)[6]、小家鼠(Mus musculus)[7]、社鼠(Niviventer niviventer)[8]等的生物學特征、為害特點有較明確的了解。特別是對前3種(也是為害較大的)鼠在洞庭湖區域的生態特性、種群發生規律進行了系統研究,提出了有效的數量預測預報方法和綜合治理技術,經示范區檢驗,證明行之有效,鼠害防治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都有顯著提高[4]。
在洞庭湖區,除東方田鼠外,其它鼠種冬季基本為全年繁殖低谷期或停止繁殖,一般在春、秋有兩個繁殖高峰,種群數量也會據此季節波動。東方田鼠的繁殖隨生境變遷而變化,夏季繁殖率最低,秋季開始大量繁殖,冬季維持較高繁殖能力,一直到初夏遷出湖灘生境,然后進入繁殖低谷期。針對本地較為特殊的東方田鼠長江亞種,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連續多年進行了深入研究與監測,為學界揭開了該鼠棲息習性[9-11]、巢居與洞群結構[12]、食性[13-14]、以冬春為主的特殊繁殖特性[15]、種群數量消長規律[5,16]、遷移規律(包括遷出與回遷動因、過程、行為特點等)[17-18]、與江湖沼澤化相關的成災原因[5]等一系列謎團;據其生態學特性設計了發生量預測技術和“阻斷遷移通路”防治方案[5,19];創立的東方田鼠室內繁育技術[20],為該鼠實驗動物化奠定了基礎,并由此與湖南、上海等地合作,開展東方田鼠抗血吸蟲病機理及實驗動物化研究,同時還為東北、西北等地該鼠亞種的分類學鑒別提供了重要意見;對東方田鼠殺幼行為、取食行為的實驗和對遷移行為的觀察[13-14,17-18,21],被認為是國內動物行為學重要進展。同時,從密度制約效應對東方田鼠種群暴發的原因進行探究,更深入地研究種群數量控制因素[22-25]。東方田鼠長江亞種生態學、行為學研究進展大多系我所首創成就,引起國際學者很大興趣,國內同行亦有高度評價。
1.2 洪澇對鼠類群落的影響
洞庭湖區域水系發達,常有洪澇發生,各種重大自然災害也是影響生態系統中生物群落的重要自然因素。對洪澇后生物群落結構變化的研究,了解各生物群落受到破壞后的恢復或演替過程,對生物群落的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洞庭湖湖灘每年汛期必須經歷被演沒3~5個月的過程,因此歷史上形成了以東方田鼠為絕對優勢種類的結果[9]。而在湖區被大堤保護的垸田,屬農業生態系統,一般不會被淹沒,但也有因潰堤或內澇形成的洪澇災害。對此的觀察結果顯示,洪澇災害對害鼠的影響及對洪災后害鼠回升的情況與滅鼠活動對其的影響完全不同[26]。首先殘留的鼠種有異,滅鼠后的殘留鼠種主要以小型鼠為主,而洪災后的害鼠主要是大中型鼠,主要集中在房舍區。回升動態也截然不同,盡管洪水已將害鼠種群降得很低,但其回升速度卻很快,并會達到很高水平。大面積滅鼠后,害鼠的種群密度如果壓得很低,種群將以很慢的速度回升,也不像洪災區達到特別高的水平[26]。因此在洪災區,災后應注意害鼠種群數量動態,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害鼠種群密度,預防鼠傳疾病的發生。
2 社會經濟因素對鼠類群落種群的影響
最為典型的事例就是20世紀80年代農村體制改革,實行年產承包責任制,造成糧食豐產與種植的多樣化,加上糧食的分散儲存(由過去的集體變為各家各戶儲存),改善了鼠類營養條件卻疏于防治,引發了全國性的鼠害暴發[27]。隨后,對人工滅鼠、農村住房結構變化、洞庭湖區退田還湖工程和長江上游的三峽工程等對鼠類影響的長期跟蹤觀察和系列分析,獲得鼠類群落演替和優勢種群對脅迫因素的反應特性等重要信息,為長期綜合治理技術設計提供了科學基礎[28]。
2.1 人工滅鼠對鼠類群落的干擾
短期看,化學滅鼠活動可以在短時間內對害鼠群落結構造成重大的影響,如經常使用化學殺鼠,小型、耐藥性強的鼠種有可能逐漸成為優勢鼠種,導致優勢種發生變化;從長期看,害鼠群落的演變有著自身的規律,滅鼠后一定時期,鼠類的群落結構會恢復到環境所決定的格局,滅鼠區鼠類群落的長期演替結果仍與相似環境內未滅鼠區的類似[29-30]。種群數量上講,滅鼠質量的好壞和實施滅鼠區域面積的大小,是滅鼠后的數量回升速度重要因素。一次性殺滅的滅鼠率越高,實施滅鼠覆蓋面積越大,害鼠種群在滅后恢復過程中保持在較低水平的時間就越長,即害鼠種群回升的速度就越慢。另一方面,若鼠類生成的生態環境條件不變,毒餌殺滅后害鼠種群密度總會回升。也就是說,僅單純依靠毒餌滅鼠手段, 難以持久控制鼠害。所以在害鼠數量較高,必須進行化學方法滅鼠時,既要因地制宜提高化防質量以抑制害鼠數量, 更應大力提倡生態防治為主的綜合措施[30],才能根本上控制鼠害發生。
2.2 農村住房結構變化對鼠類群落的影響
通常,在家具等物品擺放整潔、食物與水源少的硬化地面的房間鼠密度較低,且以小家鼠占優勢;在雜物堆放較多、臟亂差的泥土地面房間的鼠密度較高[31]。隨著我國農村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將土木結構泥土地面的房屋逐漸改造為磚混結構混凝土地面的房屋后,明顯降低害鼠密度。鼠類群落結構也在隨房屋結構的變化發生不斷的演替,小家鼠已經成為整個洞庭湖農區農房鼠類群落中的優勢鼠種。同時,在防治過程中應根據農舍結構的不同,增設適當的防鼠設備,采取相應的防治措施,可以取得最佳的防治效果[32-33]。
2.3 農業生產活動的影響
農田生態系統內,鼠害的形成是土地農業利用和開發的“副產品”,農業生產格局、作物布局和各種農業措施等都會對鼠類的生存與發展產生影響[34]。洞庭湖區農業生產格局和生產活動對農田害鼠種群數量的影響結果表明,水稻田鼠密度高于棉花地,初冬稻茬地鼠密度高于油菜地,開春后油菜地鼠密度高于稻茬地;無酚棉田鼠密度高于有酚棉田,田埂硬化農田鼠密度顯著低于未硬化田埂農田。早稻播種、雙搶和晚稻收割等全局性農事活動可改變生境導致鼠在不同棲息地間遷移或擴散,進而對農田害鼠種群數量變化產生一定影響,但受農田害鼠自身繁殖特性制約而對總體鼠密度的影響呈不明顯差異[34-35]。因此在實際控制策略上,需要關注不同類型農業生產活動對鼠類群落產生的影響,特別關注可能導致鼠類種群數量增長或暴發的因素。如現在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糧改飼等新的結構調整,也有可能導致鼠類群落結構的變化,需密切關注。
2.4 重大工程的影響
2.4.1 退田還湖工程對鼠類群落的影響 退田還湖是我國政府1998年提出的重大生態環境恢復工程。洞庭湖濕地被列為了退田還湖的重點區域之一。結合歷史數據以及植被協同演替進程,對退田還湖后鼠類群落的變化進行的觀察和研究結果看[36-37],顯著變化主要體現在雙退垸鼠類群落的演替,即東方田鼠在此退田還湖區的安居,這也是植被演替趨向原有湖灘植被群落的結果。退田還湖后5~10年的雙退垸生境內鼠類群落,除了有以湖灘為主要棲息地的東方田鼠種群,也有原來農田絕對優勢種黑線姬鼠,且以這兩種鼠類為主要優勢種類。其中,黑線姬鼠仍為第一優勢種。因此,隨著雙退垸植物群落向現有湖灘草地的頂級群落演替,即東方田鼠喜食的薹草種群在植被群落中的優勢地位進一步加強,將非常有利東方田鼠的發展。加上東方田鼠在雙退垸區域夏季的高繁殖特征[38],雙退垸的鼠類群落與草本植物群落一樣,還會有較大的變化。鼠類群落的演替將會繼續進行下去,一旦東方田鼠種群暴發的外部條件成熟(如處于數量高峰年份)出現,在一些雙退垸區域,東方田鼠種群是很有可能大暴發。從2007年洞庭湖東方田鼠史無前例的大暴發似乎可以得到印證[39],因此需要密切加以關注和跟蹤監測。
2.4.2 三峽工程對鼠類群落的影響 由于東方田鼠種群消長與湖區水文和洞庭湖沼澤化密切相關聯,而長江三峽工程后三峽水庫對下游水流量的調度將明顯改變水庫下游長江段的來水狀況,東方田鼠種群自然會受到較大影響。據三峽工程建成后下泄流量之調度方案,預測了三峽工程后洞庭湖湖水水位的變化以及相應對洲灘環境的影響,進而預測三峽工程對東方田鼠種群動態的影響。結果顯示三峽水庫完全運行后,由于對下泄流量的控制,洞庭湖中低位洲灘出露面積會不斷增大,空間上相應地將擴大該鼠的最適棲息地;冬春連續出露天數將增加,則在時間上延長該鼠繁殖盛期。在不考慮其它因素的情況下,其種群基數較以往有較大增加的可能[40]。這也應該是洞庭湖2007年東方田鼠種群大暴發的重要因素之一,盡管也與上述退田還湖后東方田鼠棲息地擴張關聯。
但此后洞庭湖湖灘鼠類群落的演替動態與預期有一些差異。從長期的演替觀察看,三峽工程后,湖灘生境鼠類群落已發生重大變化,由單一絕對優勢種群落演變為東方田鼠和黑線姬鼠并為優勢種類的群落。包括黑線姬鼠、褐家鼠、鼩鼱和刺猬等其它種類均已侵入湖灘[41]。在此背景下,由于黑線姬鼠和褐家鼠的大量進入,湖灘生境的鼠類群落已變得與農田生境相似,在鄱陽湖的觀察結果也有同樣的趨勢[42]。那么本來處于從農田生境向湖灘生境演替的雙退垸內鼠類群落演替將來會怎么發展呢?需要密切關注。
3 害鼠成災規律的分析
結合以上研究成果,對害鼠的暴發原因進行綜合分析[3-5,28,39]。特別是對東方田鼠種群數量調節機理,從密度制約方面[22,24-25]和棲息地評估[10]進行了較深入地探討。鼠類成災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種群數量過度增長,也就是自然生態系統中抑制種群的各種因素保持的一種平衡關系被打破,是某一生態系統受到自然或外力作用所致。由于鼠類成災的狀況基本呈現于人類生活與生產活動相關的各類復合生態系統中,所以人類活動的干擾對害鼠群落的演替過程和鼠密度的波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常常是引起害鼠種群的暴發和形成危害的關鍵因素。如常有鼠害暴發的農田生態系統就是一個受人工干預很大的系統。農田內主要種植各種作物,單一地區的作物種類是較少的,導致植被的多樣性降低;同時人類農事活動對生態系統的頻繁干擾,在各類型區域均會形成以不同的少數鼠種為主的群落格局。這種狀況下,一旦鼠類種群發展的自然條件滿足或較為優越,可促進害鼠種群數量的大暴發,形成嚴重的危害。
在長江流域,大部分區域農田內一般以黑線姬鼠和褐家鼠為主要優勢種,常會維持在較高的水平[3-4]。在洞庭湖區濱湖區域,東方田鼠暴發成災的根本原因也與人類活動有密切關系。人類活動導致長江上游和四水(湘、資、沅、澧)帶來的洞庭湖洲灘泥沙淤積,在湖區的圍湖造田、圍湖滅螺等活動導致的湖面萎縮,最后結果就是洲灘擴展,湖泊沼澤化,這些無意中給東方田鼠種群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最終導致東方田鼠成為一新型有害種類[5]。2007年東方田鼠的暴發成災還與當地實施的退田還湖重大生態工程和三峽工程的影響有關[39]。
因此在決策和實施社會經濟建設的某些活動時,若能考慮對害鼠種群的發生發展影響,對有關項目可能對鼠類生存環境的影響進行預測,并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害鼠種群的預案,將有可能避免或減少鼠類種群暴發帶來的各種損失,更有利于我們的經濟建設。因此,適時地采用“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思維,關注社會經濟活動中重大舉措對鼠類群落的影響,科學地制定鼠害控制對策,是非常有意義的。總體而言,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長遠發展來講,害鼠種群數量將受控制而趨于下降;但中短期考慮,社會經濟建設的某些活動可能引發局部或大面積害鼠種群的暴發。
4 害鼠群落數量管理措施
在掌握我國南方農業害鼠生態特性基礎上,結合毒餌技術改進,形成“全棲息地毒鼠法”[3]和新型鼠藥“復方滅鼠劑”系列產品[43-44],并將全棲息地毒鼠法與復方滅鼠劑整合——總稱“全棲息地毒鼠技術”。此技術以害鼠生態學為基礎,將毒餌滅鼠三要素——殺鼠藥物、用藥技巧和組織措施有機地結合,成為一套適合我國亞熱帶農業區防治鼠害的實用技術。包括6大環節,即查明鼠情、選準時機、制好毒餌,組織圍殲、正確投放和查漏掃殘的技術要領與原理。
在湘、桂、川、皖、鄂、贛、滇、滬等省市,與當地政府結合,組織大面積全境群眾性滅鼠活動,農田和農房的滅鼠率(大多達90%~96%)、有效控制期和經濟效益都顯著高于常規毒餌滅鼠法,極受當地贊賞[4]。針對東方田鼠在洞庭湖區域暴發成災,據其生態學特性采用“阻斷遷移通路”防治方案,獲得多年的成功驗證[4-5,19]。
需要注意的是,沒有絕對概念的害鼠,不是在所有區域的鼠類都要求去控制,如洞庭湖區的東方田鼠,當它們生活在洲灘時,可成為當地生態系統中天敵的食物資源,也不會對農業生產產生為害,就完全沒有必要采取措施進行滅鼠。在汛期遷移過程中,只要采取“阻斷遷移通路”的方法控制其不進入農田,就可以避免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所以當地采用“設障埋缸法”和利用“防浪墻”等物理防治措施,既可保留該鼠在湖灘自由生存,又可防除其導致的為害,比化學滅鼠方法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都有明顯地提升和改善。
5 討論
5.1 鼠類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基本功能
通常人們很容易將鼠類同“為害”或“危害”聯系起來。然而生態學的觀點認為,每一物種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沒有絕對有害的動物。雖然由于人類自身的活動和健康的需要,要求居民住宅和飛機、輪船、車輛等交通工具及某些特殊場合不容許有鼠存在,但在廣大的農田、森林、草原等景觀范圍內并不要求完全無鼠。也就是說,鼠類只有在與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活動發生沖突時,才形成一定的危害性。說明,鼠的益害是相對的,是相對于人類的社會、經濟利益而言的,而它們在各種生態系統中的作用或功能則是復雜的,也是必須的和不可替代的[45-47]。
鼠類作為生態系統中的初級消費者,是目前世界上種類與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哺乳動物,為次級消費者提供大量的食源。它們是自然生態系統中重要的必需組成成分,通過食物鏈—食物網及其間接作用,在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幾乎與生態系統中的各物種都會有一定的關系,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穩定因素,因此它們在維持正常的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上是不可缺少的[45-47]。
鼠類本身也被人類所利用,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如鼠類中不少種類有毛皮用、肉用價值和藥用價值,一些種類被列入《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更重要并且至今難以完全替代的是一些鼠類被純化培育成為實驗動物,為人類的健康和科學發展作貢獻[47]。
5.2 主要生境的鼠類群落演替
受到群落內部因素和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鼠類群落在不斷的演替,如洞庭湖不同生態類型區[48]、丘崗平原區[27]、濱湖區[49]、住宅區[33]和湖灘[36]的鼠類群落。由于鼠類是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且種類豐富,不同生態系統或生境會有相適應的鼠類群落存在,并隨生態系統的變化在不斷演替,因此了解鼠類的群落結構特點和演替規律,對于闡明鼠類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及防治鼠害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掌握鼠類群落的演替驅動因素,可制定具有針對性的防治措施。
目前而言,三峽工程后洞庭湖湖灘鼠類群落的顯著變化已非常明顯,特別是黑線姬鼠在湖灘生境群落中優勢地位已超過東方田鼠,但具體驅動因素并未深入研究。同時這種狀況對當地工農業生產和人們生命健康的影響也有待進一步評估。因此,需加大投入,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從鼠害防治角度看,幾年低水位情況下,黑線姬鼠種群在湖灘極度膨脹之后,再出現一次高水位年份的話,是否出現黑線姬鼠大幅從湖灘遷移侵入農田的情景?而黑線姬鼠對可致死其他動物和人類的許多疾病病原體具有驚人的抵抗性,潛在傳播疾病的能力是也強,已知傳播的疾病多達17種之多,且為腎綜合征出血熱和鉤端螺旋體病的首要宿主,因此針對目前三峽工程導致的洞庭湖洲灘的鼠類群落改變后有可能導致的害鼠種群暴發,很有必要利用“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探索針對性的措施預防鼠害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