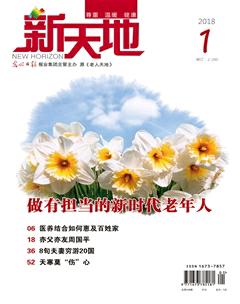半生守護兩項“非遺”
張玉榮
2017年10月24日,湖北省襄陽市圖書館聯合老河口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特別邀請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老河口絲弦傳承人余家冰,為大家分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老河口絲弦。
從9歲開始接觸民間音樂,今年73歲的她,用了大半輩子學習、保護、傳承和創新這種文化。
留住民間文化就留住了鄉愁
“老河口”地名出現在明洪武年間,因地處漢江故道之口,最早稱老河口鎮。清光緒版的《光化縣志》記載,“鎮長十里,為邑一大都會”,曾“商賈輻輳,煙火萬家,誠為富庶之地”。
1944年,余家冰出生在這“富庶之地”。“我出生時,老河口絲弦和鑼鼓架子已經誕生、流行了200余年了。”她自豪地說。
絲弦樂興于古都開封,在清乾隆年間被一些行商或路過的河南人帶入老河口,演奏絲弦的是古箏、琵琶、月琴、洞簫、二胡等彈撥樂器。隨著時光流逝,源自河南的絲弦樂深深地烙上了鄂西北的印跡。同樣,老河口鑼鼓架子在清雍正年間,由山西商人帶進老河口。余家冰說:“我的老師、老藝人王直夫告訴我,清咸豐初年(1851年),僅山西會館,一次出燈會就有20多臺鑼鼓,再加其他會館的鑼鼓,當時的老河口鼓樂喧天,熱鬧非凡。”
1950年以王直夫為首的老藝人組建了“國樂社”,培訓糅合了當地鑼鼓技藝的“老河口鑼鼓架子”,鼎盛時期,演奏學員有70多人。無論是老河口絲弦還是鑼鼓架子,都帶有濃郁的民族、民間和地域特色。余家冰形容,就像印度音樂,無論是哪一首曲子,那種民族旋律的辨識度都極高。
9歲那年,余家冰聽到王直夫的演奏后,“沒有過渡地就入了迷。過年時為了聽老師彈奏都賴在他家里不走”。父親是音樂教師的余家冰,從小對音樂和各種樂器不僅有興趣,并具備天賦。她對音樂的興趣和天賦,后來深得王直夫的喜愛。
“老師擅長古箏、琵琶、二胡、嗩吶等多種樂器演奏,還對絲弦和鑼鼓架子有創造性研究,我最初有意識記錄這兩項樂譜,是因為感覺那是老師的心血,而且它們那么好聽。如果不記錄下來,隨著老師那一輩人逐漸離世,這些曲譜就消失了。”那是上世紀60年代,年僅20多歲的余家冰的憂慮。之后,她付諸行動,開始了堪稱龐雜的整理、記錄工程。
跟眾多古老民間文化一樣,至王直夫,老河口絲弦和鑼鼓架子的傳承都靠口口相傳。兩種民俗音樂,各有10多人參與表演,要整理出一支樂譜,就等于要記下10多首不同的演奏曲子。
王直夫等民間藝人不識字,使用的是古老的工尺譜(百度百科介紹:工尺譜是中國傳統的記譜法之一,因用工、尺等字記寫唱名而得名;將工尺譜譯成簡譜,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而且,民間藝人的演出,受情緒心情等影響,有一定的隨意性,余家冰要記下絲弦和鑼鼓架子的曲牌,要每一次都全神貫注。“但這種艱難,跟后來將工尺譜翻成簡譜相比,是小巫見大巫。”她說,上世紀70年代,已是兩個孩子母親的她,為了把工尺譜翻譯成簡譜,常常在深夜孩子熟睡后才開工,然后干一通宵。因為勞累,當時還是老師的她,上課時數次暈倒在課堂上。30首絲弦曲目和40余首鑼鼓架子曲目,后來被余家冰完整地記錄、保存了下來。她說:源自于對滋養了自己的民間文化的摯愛。現在很多過年才回老河口省親的中老年人,聽到鑼鼓聲響,就立刻想到小時候……那是一種留住鄉愁的旋律。
半生守望喜迎文化保護
國家級非遺項目的珍貴,來自于它保護和傳承的難度。“文革”開始,已經記錄了厚厚3本曲牌的余家冰,像“母牛護犢”一樣保護著自己的“寶貝”。“曲牌記在硬紙殼上,外面包上幾層油布紙,藏在竹子搭的頂棚上,然后再用舊報紙糊住頂棚。”她回憶道。那時,她沒有超前意識:覺得自己保護的是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是因為她的記錄過程太過艱難,她不想失去它們……上世紀80年代初,搜集、編撰《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湖北卷》的專家們,首次看到余家冰整理的曲牌手稿,如獲至寶。為了幫助余家冰更好地留存,武漢音樂學院甚至派出幾名研究生幫她謄寫、編印手稿。
2006年,已經62歲的余家冰,為凝聚了半生心血的“老河口絲弦”申報國家級非遺項目。兩年后,經過層層評審,這個項目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她被認定為項目傳承人。5年后的2011年,余家冰為“老河口鑼鼓架子”申報國家級非遺項目。2014年8月6日,這個項目申遺成功。
2014年10月18日,在老河口市委大院溫暖的秋陽下,余家冰平淡地說著那兩項眾人眼里厚重的收獲,“兩次‘申遺,我都僅提交了一次資料。因為項目文化底蘊深厚、申報的資料翔實等原因,最終通過了兩年進行一次的嚴格的專家評審。”
申報和傳承兩項非遺項目過程中,余家冰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幫助。老河口市友誼社區和光明社區,為她和伙伴們的排練提供了必需、優質的場所;老河口第八小學成立了“老河口絲弦傳承基地”,邀請她定期授課……“趕上了好時候。”余家冰說自己是幸運兒,在有生之年,能將前輩們留下的文化精品保存好、看護好、傳承好。
隨著老河口絲弦和鑼鼓架子申遺成功,喜歡、重視與有興趣學習它們的年輕人也多了。現在的余家冰每天都感覺時間不夠用,要做的事情很多:授課、排練、演出、接受采訪、受邀參加活動、深入挖掘當地特色音樂……即使再忙,她也堅持每天坐在古箏旁練上一個多小時,“白天感受著時代的變化,晚上練琴練著練著,就有了新的感受。傳統文化想要有生命力地傳承下去,必須與時俱進。像那首《蘇武思鄉》,原創的曲風凝重、抑郁,可是我現在覺得‘思鄉的感情是那么熱烈和明亮,因為國家越來越強盛,越來越讓人愛……用現在的感情演奏傳統曲目,傳承才更接地氣、更有意義。”她輕撥箏弦,一臉陶醉。
(責編:孫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