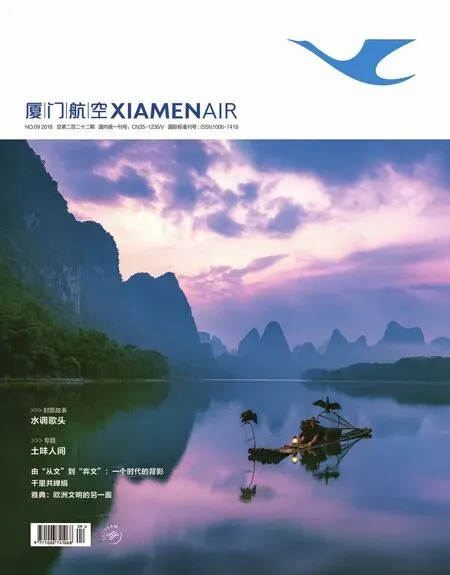從土地神到鄉愁
撰文_肖伊緋
在中國,土地是有神靈的。
在中國人眼中,土地本身即是神靈。
土地神,可能是中國最本土、最“基層”的神祇。曾幾何時,漫步于古鎮老街之中的旅客,都不難發現,那安然供奉于小石龕中的,悄然置放于村頭巷尾的屋舍轉角處的土地神像,千百年來香火未絕,依然還是中國人骨子里的信仰。
無須多言,中華五千年文明,經歷了漫長而又深刻的社會制度與經濟文化變遷,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無論政體與國體如何變換,中國人的生活都緊緊依附于土地,始終與土地血脈相連。中華文明進入兩千年帝制時代之后,上至國家興亡,下至婚喪嫁娶;大至天文歷法,小至衣食住行,無一不與土地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所謂安居樂業,無非是耕者有其田與王者有其道。耕者如何有田,王者如何有道,百姓如何安居樂業,兩千年來一直是中國帝制時代的重大主題。兩千年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擁有土地的多少直接反映了社會地位的高低,擁有土地就意味著安居樂業的開始,就意味著個人發展與家族昌盛可以預期。
與此相反,流離失所與背井離鄉,則是熱望著擁有土地的中國人的最大失望。因天災、人禍、戰亂等種種不可抗力,不得已離開故土,四處游走而謀生計者,歷史被稱作與“良民”相對的“流民”。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沒有固定的住所與職業,沒有穩定的收入與家庭,未來不再可以預期,安居樂業的夢想更是再難以企及。他們對故土的思念,對家鄉的眷戀,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下去,無論將來富貴或貧窮,無論將來顯達或無名,這份思念與眷念,都始終帶著濃重的鄉土氣息,被人們稱作鄉愁。
當代著名作家、詩人余光中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年初隨母自南京逃往上海,再去廈門,轉廈門大學外文系二年級下期。當年7月,又隨父母遷香港,失學一年。1950年5月,輾轉赴臺灣。至此,22歲的余光中,就此與故土海天兩隔,再未回還。1971年,已經20年沒有返鄉探望的余光中思鄉情切,在臺北廈門街的舊居內寫下那首膾炙人口、感動世人良久的《鄉愁》。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在臺灣高雄醫院逝世,享壽90。這位被譽為“中國現代詩壇的最后守夜人”的詩人,一生創作過大量詩文,但最能讓世人記憶深刻的,恐怕還是《鄉愁》。這首詩,曾經打動過、至今仍在感動著無數海外華人。毋庸多言,他們那份思念故土、感念家鄉的衷心,在這首詩中找到共鳴;這首詩,最深切地反映著中國人千百年來綿延不絕、始終濃厚如初的土地情結。
事實上,在離鄉去國、隔海迭山的華語世界中,與余光中的流徙生涯相仿者,何止千萬;與余光中道出的鄉愁隔空共鳴者,又何止萬億?從蜀山深處走來,漂泊半世、享譽海內的著名畫家張大千,亦是這隔空共鳴、遙望故土者中的一員。
1982年3月,一位美籍友人從長江三峽入蜀游覽,一路迤邐行來,輾轉又到臺北去訪晤時年83歲的張大千。此行,友人為張大千帶來了一份神秘且珍貴的禮物:一包故鄉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故土,且慰鄉愁;張大千為之老淚縱橫,鄭重的把這一捧故土供奉于居所案頭。
這一捧故土,于已步入人生暮年的張大千而言,意義非凡。須知,他于20世紀40年代離開故土,游蹤遍及世界各地,以筆墨丹青弘揚中國藝術,載譽馳名于國際藝壇。因種種原因,他終未能歸國返鄉、落葉歸根,可他對故土的思念,無時無刻不在牽動情思、蘊藉情懷。二三十年間,凡所經歷之地,他皆購置與營造能一慰鄉愁的中國式居所——以中國古典園林的布局與形態表達其中國情結。他在海外有居所數處,從美國舊金山的“可以居”,美國十七里海岸的“環篳居”,到巴西的“八德園”,無一處不映現著中國情結,無一處不閃現著故土情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遷居至臺北之前,巴西“八德園”是張大千在海外居住時間最長、營造規模最大的私家園林式居所。張大千對“八德園”的營造,傾注了極大心血與精力;他在此引水設渠、造湖穿山,盡最大可能摹仿蜀地故鄉原貌。對于自己追懷故土、神思鄉景的這一作品,張大千頗感快慰,常常與友人提及,居于巴西“八德園”,渾如巴蜀山鄉間。
1983年4月2日,也就是在收到友人千里送贈的“故土”一年之后,一直渴盼落葉歸根卻終未能的張大千在臺北病逝,享年84歲。遵其遺愿,張大千的骨灰被埋于其親自設計營造的臺北摩耶精舍的梅丘石碑之下。一位聞名世界、載譽全球的著名藝術家,就此在異鄉隕落。不難揣想,漂泊半世、游藝四方卻終未能回歸故土,未能長眠于隔海相望的蜀中故鄉,始終是張大千傳奇一生的最后也是最大的遺憾吧。
遙思中華文明五千年,以農耕文明為核心所造就的土地情結,始終扎根在中國人的心田之中。無論是先民神壇上的皇天后土,還是百姓街巷間的神龕供奉;無論是余光中筆下的鄉愁,還是張大千案頭的故土,中國人對土地的深沉摯愛與衷心崇敬,千百年來無以復加的“借題發揮”著,始終是中國人“借景抒情”的重要母題。可以說,從土地神到鄉愁——中國人的土地情結,歷經千百年歷練與沉降,已然從神靈到靈魂,經歷了骨血的洗禮與基因的復制。
這樣的情結,歷久彌新;這樣的情結,恒久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