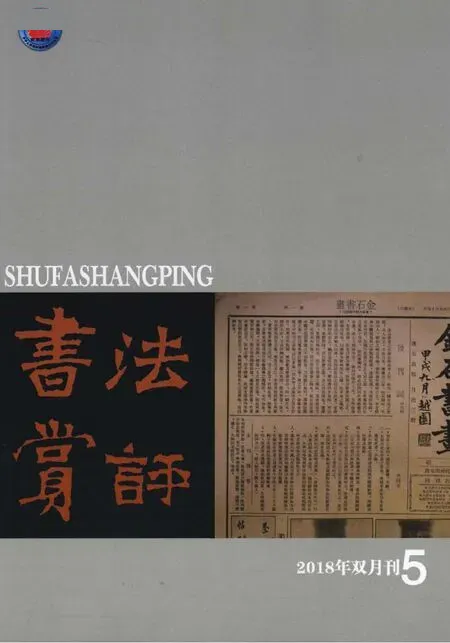《龍藏寺碑》與 《董美人墓志》文風比較研究
《墨子·明鬼下》中記載: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后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后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以金石,以重之。”[1]早在先秦,遺世留名的人文觀念就已成為人立身揚名的價值追求,遂將文字 “鏤于金石”的文化傳統由來已久。墓志、碑刻、摩崖、造像等,或記事、或言功,都昭示子孫銘記歷史。立碑早在先秦已有, 《石鼓文》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立碑經歷了漢代的興盛,再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輝煌與沉寂,發展到隋代的時候已經成熟,在制作上有統一的形制,在文風上也從最開始簡單的記述發展成為統一的寫作范式,形成了鮮明的文學特點。人生百代,死生之間,若欲垂留千古,遂有墓志。墓志于生者,乃心靈的慰藉;于死者,乃生命的足跡。志,記志也。銘,記也。墓志的起源眾說紛紜,我國著名的金石學家游壽先生在其 《墓志的起源》一文就指出: “古無諛墓之文,墳冢樹豐碑,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有穿,所以系而下棺也。事畢,即閉壙中。至于有功德懿行者,然后褒榮其終,刻銘于碑。”[2]墓志的起源與發展亦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到隋朝亦已經形成規范的形制和固定的文體范式。
《龍藏寺碑》刻于隋開皇六年 (586),現位于河北省正定縣隆興寺內。碑額刻 “恒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3行15字。碑陽刻文30行,滿行50字,碑陰及碑身右側刻恒州諸庶士僧官的題名。碑文主要記述恒州刺史王孝仙 “奉勅勸獎州內士庶一萬人等共廣福田”修建龍藏寺諸事宜。 《董美人墓志》刻于隋開皇十七年 (597),原石于清嘉慶、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西安。21行,行23字。原石毀于兵燹,現僅存拓本流世。《董美人墓志》是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楊秀為其過世愛妃董氏而撰寫的悼念銘文。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胡小石先生在 《<中國文學史講稿>第一章通論》引言中引用清代大儒焦里堂對文學史的梳理和定位: “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則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3]由此闡明文學與時代之關系。王國維在 《宋元戲曲考·序》中有同樣的論述: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莫能繼焉者也。”[4]“知人論世”作為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成為解讀文本的重要途徑。如果說文學是一片森林,那么時代就是其中深埋地下的根。隋代文學作為文學史的一個階段,雖然隋朝僅存三四十年,但同樣有滋長于隋朝時代及文化背景下盛開的花。隋代文學盡管不能與漢賦唐詩宋詞相媲美,但對認識漢賦、南北朝文風對隋文學依然有其獨特而有價值的研究意義。將隋書名品 《龍藏寺碑》和《董美人墓志》置于文學史的視野研究,從碑刻或者墓志文體發展的角度來說, 《龍藏寺碑》碑文和 《董美人墓志》墓志銘明顯受到漢賦及南北朝駢文的影響,或者說是對漢代散體賦和南北朝駢文的借鑒。
漢賦極盡鋪張之能事,詞采華麗,氣勢如虹。極盡詞匯,事無巨細地對客觀事物進行描寫,如司馬相如的代表作 《上林賦》和 《子虛賦》,其中對齊國、楚國極盡鋪陳之能事,在描寫山川城邑、鳥獸草木時匯集大量詞語,進行詳盡甚至繁瑣的細節描寫。從 《子虛賦》對后花園中一隅的描寫便可見一斑,如下:
云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云;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玞。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茳蘺麋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玳瑁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楂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鹓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5]
《子虛賦》在用字上喜選用生疏艱澀的詞匯,窮盡狀物之妙,充分體現了作家對客觀事物的觀察和把握,也充分體現了漢代散體賦的文體和文風特點,漢賦在形式上的用心導致其在文學作品抒情性方面的欠缺。但 “文本同而末異”,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體裁和形式,如曹丕在 《典論·論文》中說: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6]奏章宜文雅,書論宜有理有據,銘誄宜尊重客觀事實,詩歌和賦宜華麗。不同的文體立意要求各不相同,陸機在 《文賦》中亦有這樣的表述: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7]陸機指出詩歌、賦、銘文各自的文體標準,同時陸機也指出各體語言應該清晰暢達,避免冗長。
駢, 《說文解字》注: “駕二馬也。從馬并聲。”后引申為兩物并列,成雙、對偶。所以,駢文與散文相對。駢文在句式上慣用四六句,以偶句為重,注重對仗工整;在用韻上,講究平仄;在修辭上,注重文辭華美,慣用典故。駢體文和漢賦一樣,過分重視形式上的統一,難免弱化內容上的深刻。駢文中,庾信的 《哀江南賦》是其中的代表,如其中在哀嘆故國家園時的心聲:
“且夫天道回旋,生民賴焉。余烈祖于西晉,始流播于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于天門,驪山回于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于金張,聞弦歌于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8]
由此可見,駢文的四六句格式,講究對仗互文。
從文章篇幅上來說, 《龍藏寺碑》全文1800余字。由于墓志在客觀條件上的限制, 《董美人墓志》全文500字。隋代墓志和碑刻在行文方式上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前為序,后為文,或者前為序,后為銘。序是鋪墊,文和銘是對序的高度總結和凝練概括,是文章的主體。 《龍藏寺碑》主要記事, 《董美人墓志》主要記人,兩者的主要內容雖然不同,但在行文方式上環環緊扣,又皆可見對漢賦及南北朝駢文的借鑒。今以兩文各段互較之:
《龍藏寺碑》:
竊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明自在,如無畏。取譬金剛,信畢竟而不毀。是知涅槃路遠,解脫源深。隔愛欲之長河,間生死之大海……若至凡夫之與圣人,天堂之與地獄,詳其是 (非) (得)失, (安) (可)同日而論哉!往者四魔毀圣,六師謗法。拔發翹足,變象吞麻。李園之內,結其惡黨;竹林之下,亡其善聚。護戒比丘,翻同雹草;持律□□, (忽)等霜蓮。慧殿仙宮,寂寥安在;珠臺銀閣,荒涼無處。
《董美人墓志》:
美人姓董,汴州恤宜縣人也。祖佛子,齊涼州刺史。敦仁愽洽,標譽鄉間。父后進,俶儻英雄,聲馳河渷。
此段兩文立意相似。如 《龍藏寺碑》第一段先解釋佛理佛法,從 “竊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至 “故知業行有優劣,福報有輕重”。轉而再寫佛道被毀,佛法被惡勢力毀掉后的后果,從 “若至凡夫之與圣人”至 “珠臺銀閣,荒涼無處”。 《董美人墓志》先介紹董氏的家族背景,為下文頌揚其人品德行做鋪墊。其中作者在闡述佛理時,極盡佛法詞匯和典故,且慣用四六句,雖有賦的遺跡,卻因鋪陳并不冗長,語言清麗而更能打動讀者。
這段南北朝駢文的影子也很明顯。在形式上大量使用對仗句式,使得整個文章行文如流水,整齊勻稱。兩者在句式上慣用四六句格式,講究對仗對偶,如:
《龍藏寺碑》:
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
無船求度,既似龜毛;無翅愿飛,還同兔角。
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諦三乘,法門斯起。
檢粗攝細,良資汲引之風;挽滿陷深,雅得修行之致。
《董美人墓志》:
祖佛子,齊涼州刺史。
敦仁愽洽,標譽鄉間。
父后進,俶儻英雄,聲馳河渷。
《龍藏寺碑》第一段用佛理被毀的前后對比,為引出下文做鋪墊,即在隋文帝的圣明下恢復佛法,普濟眾生。
《董美人墓志》從上文其祖、其父的敦厚倜儻人品引出下文董氏的賢良品性。如:
《龍藏寺碑》:
離離綴彩,寧勞周客?含含奏曲,詎假殷人?我大隋乘御金輪,冕旒 (玉) (藻)。上應 (帝/天)命,下順民心。飛行而建鴻名,揖讓而升大寶……所以金編寶字,玉牒綸言;滿封盈函,云飛雨散。慈愛之旨,形于翰墨;哀殷之情,發于衿抱。日月所照,咸賴陶甄;陰陽所生,皆蒙鞠養。故能津濟率土,救護溥天;協獎愚迷,扶導聾瞽。澍茲法雨,使潤道牙;燒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壹之果,建最勝之幢;拯既滅之文,匡已墜之典。忍辱之鎧,滿 (于) (清)都;微妙之臺,充于赤縣。豈直道安、羅什,有寄弘通;故亦迦葉、目連,圣僧斯在。
《董美人墓志》:
美人體質閑華,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順以乘親。含華吐艷,竜章鳳采。砌炳瑾瑜,庭芳蘭蕙。既而來儀魯殿,出事梁臺。搖環珮于芳林,袨綺繢于春景。投壺工鶴飛之巧,彈棊窮巾角之妙。妖容傾國,冶咲千金。妝映池蓮,鏡澄窓月。態轉回眸之艷,香飄曳裾之風。颯灑委迤,吹花回雪。
從修建龍藏寺碑的角度來說,前文主要是介紹佛理——佛法被毀——隋文帝順應民心——恢復佛法的思想脈絡,為引出下文修建龍藏寺做鋪墊。從描繪董美人的角度來說,此段詳細介紹了其品德、談吐、作文及一顰一笑之間的神姿,為我們描繪了一位生動活潑、內外兼修的妃子形象。在這個過程中,歌頌隋文帝的偉大事跡明顯借鑒漢大賦的文體特點,極盡夸飾,不遺余力地頌揚其對百姓及佛法的貢獻。從這個層面上來講,這暗合漢賦的政治功能。在寫董美人的過程中,詳細到其一顰一笑,舉手投足之間百媚生。
有了前文的層層鋪墊,才引出下文龍藏寺的修建情況、董美人仙逝的前后過程,如:
《龍藏寺碑》:
龍藏寺者,其地蓋近于燕南。昔伯圭取其謠言, (筑) (京) (易)水;母恤往而得寶,窺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踐祚;靈王北出,登望臺而臨海。青山斂霧,淥水揚波。路款晉而適秦,途 (通)□而指衛。□□之落,矩步非遙;平原之樓,規行詎遠。尋泒避世,彼亦河人;幽閑博敞,良為福地……竭黑水之銅,罄赤岸之玉。結琉璃之寶綱,飾纓絡之珍臺。于是靈剎霞舒,寶坊云構,崢嶸膠葛,穹隆譎詭。九重一柱之殿,三休七寶之宮。雕梁刻桷之奇,圖云畫藻之異。 (白)銀成地,有類悉覺之談;黃金鏤盾,非關句踐之獻。其內閑房靜室,陰牖陽窗;圓井垂蓮,方疏度日。曜明珰于朱戶,殖芳卉于紫墀。(地) (映)金沙,似游安養之國;檐隱天樹,疑入歡喜之園。夜漏將竭,聽鳴鐘于寺內;曉相既分,見承露于云表。不求床坐,來會之眾何憂;□ (然)飲食,持缽之侶奚念。粵以開皇六年,歲次鶉火,莊嚴粗就。庶使皇隋寶祚與天長而地久,種覺花臺,將神護而鬼 (衛)。
《董美人墓志》:
以開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終于仁壽宮山苐,春秋一十有九。農皇上藥,竟無救于秦醫;老君靈醮,徒有望于山士。怨此瑤華,忽焉彫悴;傷茲桂蘂,摧芳上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于龍首原。寂寂幽夜,茫茫荒隴。埋故愛于重泉,沉余嬌于玄隧。惟鐙設而神見,空想文成之術;弦管奏而泉濆,彌念姑舒之魂。
這兩段詳細交代了龍藏寺的修建情況和董美人從病疾到仙逝前后的過程。修建龍藏寺上主要從其地理位置、修建者、寺廟環境等方面描寫,其中對寺廟環境的描寫上用賦中鋪陳的筆法,渲染龍藏寺華美的建筑。大量使用駢文,四六句,語言華麗豐富。寫董氏時,從 “以開皇十七年二月感疾”到 “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于龍首原”,是其從生病到埋葬過程的敘述;從 “寂寂幽夜,茫茫荒隴”到 “彌念姑舒之魂”,是蜀王楊秀對董氏的憐惜。
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主體,以 “乃為詞曰”引出正文:
《龍藏寺碑》:
多羅秘藏,毗尼覺道。斯文不滅,憑于大造。
誰薰種智,誰壞煩惚。猗歟我皇,實弘三寶。
慧燈翻照,法炬還明。菩提果殖,救護心 (生)。
香樓并構,貝塔俱營。充遍世界,彌滿國城。
憬彼大林,當途向術。於穆州后,仁風遐拂。
金粟施僧,珠纓奉佛。結瑤葺宇,構瓊起室。
鳳 (穴)概日,虹梁入云。電飛窗戶,雷驚橑棼。
綺籠金鏤,縹壁椒薰。綈錦亂色,丹素成文。
髣髴雪宮,依悕月殿。明室結幌,幽堂啟扇。
(臥)虎未窺, (蜷)龍誰見。帶風蕭瑟,含煙蔥茜。
西臨天井,北拒吾臺。川谷苞異,山林育材。
蘇秦說反,樂毅奔來。鄒魯愧俗,汝潁慚能。
惟此大城, (瑰異)所踐。疏鐘向度,層磐露泫。
八圣四禪,五通七辯。戒香恒馥,法輪常轉。
《董美人墓志》:
高唐獨絕,陽臺可憐。花耀芳囿,霞綺遙天。
波驚洛浦,芝茂瓊田。嗟乎頺日,還隨湲川。
比翼孤棲,同心只寢。風卷愁慔,氷寒淚枕。
悠悠長暝,杳杳無春。落鬟摧櫬,故黛凝塵。
昔新悲故,今故悲新。余心留想,有念無人。
去歲花臺,臨歡陪踐。今茲秋夜,思人潛泫。
游神真宅,歸骨玄房。依依泉路,蕭蕭白楊。
墳孤山靜,松疏月涼。 (左土右匧下心)茲玉匣,傳此余芳。
序一般為四言句式,這種藝術形式最早的源頭在 《詩經》。句式的整齊使意義的表達更加凝練,語氣更加協調,朗朗上口,富有音樂上的美感和節奏感。將四六句的形式運用到碑文及墓志銘中,這是文體順應時代發展的產物,更是文學自覺下的約定俗成。
劉勰在 《文心雕龍》中解釋用典: “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9]借他事言己意,借古證今。在修辭方面,《龍藏寺碑》與 《董美人墓志》善用典故。
如 《龍藏寺碑》中 “舍利弗盡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 “天女之花不去”出自 《維摩詰經·觀眾生品》,維摩詰在說法時,其房間有位天女現身,天女給各位菩薩和大弟子灑落天花,天花只灑落在大弟子身上,卻沒有灑落在菩薩身上,大弟子運用佛法依然不能使身上的鮮花脫落。天女問舍利佛為何要去掉這些鮮花,舍利佛回答身上沾花不合佛法。天女便說: “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施逾奉蓋,檀等布金。”中“奉蓋”典出 《維摩詰經·佛國品》。 “竭黑水之銅,罄赤岸之玉。”典出 《尚書·禹貢》。
《董美人墓志》中 “投壺工鶴飛之巧,彈棊窮巾角之妙。” “巾角”,典出 《世說新語·巧藝》: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狀奩戲。文帝于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棋,妙逾于帝。”除此而外, “惟鐙設而神見,空想文成之術;弦管奏而泉濆,彌念姑舒之魂。”中的 “文成之術”和 “姑舒之魂”分別典出 《史記·孝武本紀》和 《搜身后記》。
《龍藏寺碑》 《董美人墓志》巧用典故,一方面以古證今,巧妙地表達了作者的思想,語意婉轉;另一方面減少詞語繁贅,使文章結構和句式更加整體、統一。
由上可見,我們不難發現,兩篇文章在行文上呈現 “碑文似賦”及駢文的特點。萬光治在 《漢賦通論》中言:“漢代是賦文學的時代,但漢代的賦又并不都是以賦名篇的。諸如頌、贊、箴、銘,因其較注重句式的整飭和用韻、換韻,不獨可與賦同入韻文范疇,而且大多數篇章文辭繁富,重在鋪陳,與賦實為同體異用,這是漢文學研究中應予注意的問題。”[10]可見其實在漢代,石刻文獻已受漢賦的影響,如 《石門頌》等。已有學者詳盡論述了碑文似賦的淵源辯證及歷史因緣,[11]如程章燦先生在 《論 “碑文似賦”》中總結碑、賦二體在體用方面的眾多聯系:首先是題材上的類同,主要體現在寫人、紀事、寫地三大項;其次是風格上的類同,兩者都有頌的風格成分;其三是文學地位與功能上的類同。此更有利于我們理解 《龍藏寺碑》和 《董美人墓志》文體及其他碑文的文風。
三
《龍藏寺碑》和 《董美人墓志》兩者都有賦和駢文的文體特點,其辭藻華美,句式整飭等。但又不完全只是簡單的復制照搬。竊以為 《龍藏寺碑》和 《董美人墓志》本身區別于其它簡單的賦、駢文或者碑文在于它們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和思想性,其文學意義更豐富,其思想情感更深刻。單純的漢賦和駢文用豐富的想象、華美的文辭為我們構建一個包羅萬象、無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會讓我們體會物產的豐富,弱化抒情的成分,不能給讀者審美享受上的愉悅。所以,在情感的表達和審美的蘊含上, 《龍藏寺碑》和 《董美人墓志》集文學性與思想性為一體,雖以碑和墓志的身份處于文學的邊緣,但從其中仍可管窺隋朝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思想情感內涵,且它們都表達著文學永恒的主題:生死與愛情。
(一)如幻如夢,誰其受苦
《龍藏寺碑》植根于隋朝歷史文化背景,隋代大興佛法,修建大量寺廟。隋代文學作品總是夾雜佛教元素,或闡釋佛法義理,或表達佛教感悟。文人在賦詩為文的同時,體悟佛理,參悟人生。 《龍藏寺碑》作為寺廟碑文,于敘事當中解說佛義。 《龍藏寺碑》作為為寺廟建設而立的碑,序言和文都用極多的筆墨闡釋佛理。佛教義理的根本是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何為 “空”? 《大智度論》卷五: “觀五蘊無我無我所,是名為空。” “空”即指世間的一切因緣際會、緣起緣滅都無目的,無規定,虛幻不實,來去皆無定法。空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文章開篇即講: “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明自在,如無畏。”在這里 “空王” “大人” “師子”都是對佛的尊稱, “名相”即佛教語,耳可聞者曰名,眼可見者曰相。佛教作為人的精神支撐,給人在痛苦的時候一絲慰藉。佛法包羅萬象,普度眾生,眾生在來去之間自有佛佑。但人世間 “涅槃路遠,解脫源深,隔愛欲之長河,間生死之大海。無船求度,既似龜毛;無翅愿飛,還同兔角”。佛家說人生來是受苦的,所以需要一生完成自己的涅槃;解脫的道路是漫長的,所以需要佛教給予眾生信仰的力量,求得來生的福報。人如何在人生的漫漫長路修行?于是有 “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諦三乘,法門斯起”。 “五通” “八解”都是佛教義中使眾生禪定的方式。 “二諦” “三乘”指不同的解脫之道。 “如幻如夢,誰其受苦?如影如響;誰其得福?”八字高度涵蓋了佛教的精神境界,蕓蕓眾生終其一生都在苦和福中徘徊糾纏,人生幻滅的夢,如觸摸不到的影子,誰在受苦誰在享福?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只有佛法神通廣大,告知眾生所有的福報有輕有重。 “四魔毀圣,六師謗法。拔發翹足,變象吞麻。李園之內,結其惡黨;竹林之下,亡其善聚。”列舉出一系列毀壞佛法的行徑,導致 “慧殿仙宮,寂寥安在;珠臺銀閣,荒涼無處”。遂要修建龍藏寺,以復興佛法,除惡揚善。所以觀看 《龍藏寺碑》碑文對佛教徒來說本身就是一種修行。人在死生之間,思考存在的意義。
(二)如泣如訴,誰為情癡
愛情作為文學永恒的主題,從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朦朧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的癡狂;從 “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的堅貞到 “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誓言;從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相望到 “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的相思。自古以來,多少癡男怨女有理不清、剪不斷的綿綿深情?董美人年芳十九,不幸仙逝。蜀王楊秀痛徹心扉,為自己的愛妃深情撰文,以寄相思。
《董美人墓志》在描述董氏美貌與賢淑上頗有幾分曹植 《洛神賦》的風采。蜀王楊秀首先對董氏的品德舉止給予褒獎: “體質閑華,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順以乘親。”再說其談吐、作文方面很有文采, “含華吐艷,竜章鳳采。”接下來借用屈原 《離騷》中香草美人的寓意,以美玉、蘭蕙芳草比喻董氏在人格上的高潔。又以極富有詩意畫面的場景描繪董氏的日常: “搖環珮于芳林,袨綺繢于春景。”我們仿佛看到一位少女在百花芳菲的林子里游玩,她的羅裙在春日的微風中拂動搖擺。她做游戲時機靈巧妙,她的妝容如池上之蓮,如窗外之月,傾國傾城。她回眸之間的嫵媚,裙擺香飄之間的風情,頭發美如飄花,如飛雪,姿態萬千,淋漓盡現。曹植在 《洛神賦》中對洛神有類似的描寫: “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
悼亡詩一直是文學的題材之一,后世蘇軾在悼念自己的亡妻王弗的時作: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12]細細品讀,就會發現,蘇軾的這首詞與 《董美人墓志》銘文部分在語言、在心境、在情境上很相似。蜀王楊秀以優美的文筆描繪完自己的嬌妻,轉而敘述董氏不幸患疾至仙逝的過程。想到如花似玉的愛妃與自己陰陽兩隔,如今在黑夜躺在茫茫荒隴上,不禁泛起相思。“寂寂幽夜,茫茫荒隴”, “惟鐙設而神見,空想文成之術;弦管奏而泉濆,彌念姑舒之魂”。都是蜀王楊秀在夜深時分對愛妃的遐想。 “依依泉路,蕭蕭白楊。孤墳山靜,松疏月涼。”銘文最后的四言句式,句式對仗,語言簡單清麗,用韻和諧,節奏感強。 “依依”與 “蕭蕭”更是襯托出蜀王心中無限的悲傷和思念。我們仿佛可以看到在一輪冷月下,仙逝的董美人靜靜地躺在地下,彼時夜深,山格外靜,松樹的影子在月光下斑駁稀疏。 “寂寂幽夜,茫茫荒隴。” “寂寂”與 “茫茫”,寫黑暗寂靜的夜晚和荒蕪的田隴,一方面寫董氏的墓冢環境,一方面烘托蜀王內心的寂寞黯淡的思緒。在漢樂府民歌 《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最后對焦仲卿表白: “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韌如絲,磐石無轉移。”此言以蒲葦和磐石比喻兩人愛情堅貞不移,天長地久。“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此言人生的短暫與金石的永恒。歷來金石以其堅且硬的特性成為古人心中 “永恒”的象征,大概蜀王楊秀也想借此墓志銘為董美人留一份不可磨滅的真情吧!
結語
綜上所述, 《龍藏寺碑》碑文與 《董美人墓志》銘文首先在文體上是對漢散體賦極南北朝時期駢文的借鑒和應用。從碑刻和墓志文體演變上來說,其行文方式明顯受到漢賦和駢文的影響。當然,這是順應時代和文學文體自然演變規律而產生的。而且,縱觀書法史上的碑刻作品, “碑文似賦”在漢代已經出現,在頌、贊、箴、銘中也有明顯的表現。其中的四言句式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 《曹全碑》 《張遷碑》等。而 《龍藏寺碑》和 《董美人墓志》區別于其它碑或者同時代文學作品的地方在于其內在的思想內涵。 《龍藏寺碑》為建造寺廟而立,其中用大篇幅文字講述佛理,佛法及人的解脫修行之道。蜀王楊秀對董美人情真意切, 《董美人墓志》文章讀來讓人潸然淚下,不禁為董美人的離世唏噓,也為蜀王的癡情感動。
注釋:
[1] [戰國]墨翟著, 《墨子譯注》,張永祥肖霞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七月第一版,第二百六十一頁。
[2] 《游壽書法藝術》,阮憲鎮主編,中國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三十三頁。
[3] 《胡小石文史論叢》,周勛初編,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十八頁。
[4]王國維著, 《宋元戲曲史》,岳麓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一月第一版,第一頁。
[5]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二卷,郁賢皓主編,魯同群、顧復生本卷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二版,第十五頁。
[6] 《曹丕集校注》,夏傳才唐紹忠,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三十七頁。
[7] [晉]陸機著, 《陸機集校箋》,楊明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七月第一版,第十七頁。
[8] 《駢文觀止》,莫道才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九頁。
[9] 《文心雕龍》,劉勰著,黃霖導讀,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七十七頁。
[10]萬光治著, 《漢賦通論》,華齡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百〇一頁。
[11] 《論 “碑文似賦”》, 程章燦, 東方叢刊, 二〇〇八 (一)。
[12]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四卷,郁賢皓主編,鐘振振、程杰本卷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七月第二版,第一百三十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