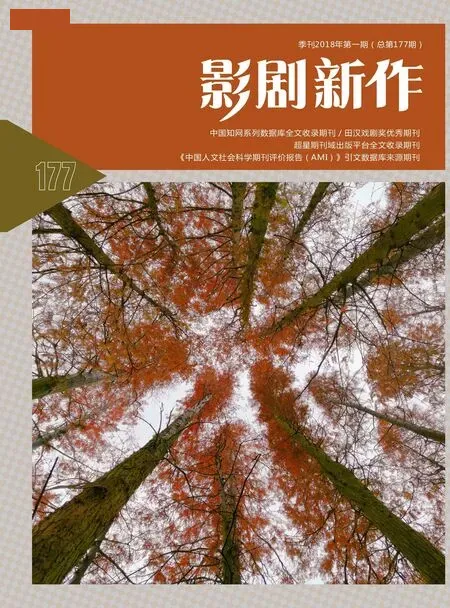也談滇劇《水莽草》的“毒性”
蘇 鳳
2016年10月24日晚,入圍第十一屆中國藝術節的地方戲《水莽草》在西安西飛俱樂部上演。帶有鮮明地域特色、民間審美意趣、富有生活氣息的滇劇《水莽草》給現場觀眾詮釋了一個理念: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又復歸生活,讓觀眾于輕松愉悅中感悟生活,體驗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作為參評第十一屆中國藝術節文華大獎的地方戲劇目,《水莽草》無論編劇還是演員的舞臺呈現都有諸多不能讓人滿足的地方,若深思該劇背后的東西,會讓人感覺詭異神秘、毛發直豎,仿佛回到中世紀。
一、道德的獨角戲
戲曲雖然是“角兒的藝術”,但是一出好戲的完美呈現也要靠其他角色合力打造,才能讓故事更具可看性。一開場,代表婆婆和媳婦兩個對立的歌隊分別以舞蹈形式表現了洗衣和納鞋底兩種不同勞動的場景,巧妙地將婆婆和媳婦兩個不同陣營的立場和身份感傳達了出來。接下來,觀眾自然期待一群婆婆和一群媳婦之中,必然會有一對婆媳矛盾作為重點突出表現。事實上,該劇也正是如此做的:茂壯家娶親,茂壯媽因娶了一個美麗、懂禮的書香門第小姐而欣慰。馮詠梅飾演的媳婦麗仙,對婆婆也是孝敬有加。但婆婆受其他婆婆們挑唆,加之見兒子茂壯在情感上對媳婦的傾斜,心態失衡,開始刁難媳婦。這本也是人之常情。在這里,編劇預設了一個前提:婆婆本性善良,對媳婦也曾滿意,只是其他婆婆們挑唆使然。這就為后面劇情中婆媳矛盾的緩和做了伏筆。接下來,觀眾自然便期待二人上演從沖突到和解的起伏跌宕的婆媳對手好戲。
但接下來的舞臺呈現就有問題了,這個戲仿佛變成一個人的獨角戲。馮詠梅飾演的新媳婦麗仙受婆婆刁難,先是通過一系列舞蹈化的動作將生活中的掃庭院、喂雞、給婆婆奉茶等場景再現,表現了書香門第小姐麗仙初為人婦的質樸和笨拙。隨著矛盾升級,麗仙心中那種新媳婦的不適逐漸轉為對婆婆的強忍、委屈和不服心理。她向丈夫茂壯求助,茂壯卻在母親建議下離家做工。于是,家中只剩婆媳二人。麗仙失去丈夫護佑,又迫于婆婆強勢,無依無靠又無法聲張,想到自殺,后被老草仙勸住。老草仙向麗仙推薦了一種不痛苦且不難看的死法——水莽草。返至家中,麗仙熬好湯藥后卻被婆婆誤飲,麗仙以為婆婆將在四十九天后離世,心生愧疚,于是改頭換面,對婆婆百依百順。婆婆說想吃雞蛋白菜絲湯面,麗仙就乖巧地給婆婆做面。于是在舞臺上出現一段極具麗仙個人化的表演:她擼起袖子,擼高擼低,切白菜,切寬切細,打蛋,炒蛋,翻鍋、攪動、顛勺、高空接蛋,生活中家務勞作的舞蹈化動作一氣呵成,非常富有生活氣息。同時也把麗仙百般忍、欲忍不能又不忍不行的矛盾心理表現出來。眼看四十九天臨近,麗仙內心的負罪感和無法贖罪的焦慮感始終縈繞在心頭,在夢中只身闖入閻羅殿,與判官進行了一番較量,愿代婆婆受死。在這一場戲中,主演馮詠梅非常賣力,炫出雙水袖長舞絕技,在陰曹地府演繹了一段心理活動外化為身體語言的好戲。但是,不得不說,馮詠梅戲份太多,以至擠壓了婆婆這個對手的戲,擠壓了丈夫這個配角的戲,也擠壓了判官本該有的喜劇戲份。馮詠梅也因自身負重太大而致體力不支。在現場舞水袖時,幾次出現表演失誤,讓臺下觀眾唏噓不已。
馮詠梅是一個好演員,這是毋庸置疑的。在塑造麗仙這個人物的時候,馮詠梅說她“仔細揣摩分析人物,力爭準確把握人物心理脈絡,并精心設計,充分外化,努力做到魂魄相通、形神相似,務求表演生動、形象豐滿”。馮詠梅非常努力地從傳統滇劇良家婦女人物形象塑造中汲取營養,抓住了麗仙這個角色的魂與形,做到了演員和人物之間氣質、心靈接通,并把竹派的特點發揮得恰到好處。她的表演的確做到了生活化、地域化、滇劇化。
可是一臺好戲,絕不能是一個人的獨角戲,我們可以看到滇劇《水莽草》“人保戲”的傾向。尤其婆婆這個對手的戲太弱,完全不能跟馮詠梅飾演的麗仙構成真正的“對手較量”,這就容易帶著觀眾一邊倒,我們完全被帶入到一種展現女主角善良、勤勞、勇敢、智慧、孝順等種種美好品格的褒揚戲中,而把戲劇本身該有的矛盾、沖突、情境等要素都沖淡了。前面編劇曾給婆婆這個角色預留的“生性還是善良的”鋪墊,隨著劇情的推進,并沒派上任何用場。全劇都圍繞如何刻畫麗仙的真善美來做戲。最后,婆婆感于媳婦善良和孝心,重新接納媳婦。這樣的結局是平庸且落俗套的,它將婆婆性情轉變完全歸因于被媳婦感動而非出于自己本身的善良天性,這樣的編劇手法讓我想到中世紀戲劇。最后謎底揭曉,完全沒有一點毒性的水莽草,便成為道德的酬謝品。實際上,這里有一只看不見的“上帝之手”——道德的感召力在控制著劇情的變化發展。看似是編劇手法問題導致該劇變成了馮詠梅一個人的獨角戲,其實該戲的真正主角應該是道德倫理,是這只看不見的手一直操控著每一個人的行動。麗仙的行為貌似每一步都是自主選擇,可是每一步卻又都不是自己的選擇。在一個以媳婦孝敬婆婆為本分、婆婆欺壓媳婦是常態的強大社會倫理面前,麗仙只能按照社會道德規定做事。所以,與其說是主演一個人的獨角戲,不如說是道德的獨角戲,道德的強大力量讓每一個人都處在一種被安排好的命運之中,個人行動毫無意義。這只“上帝之手”的存在讓水莽草徹底沒了毒性。
二、被禁欲主義閹割的男性
《水莽草》讓我們仿佛看到了中世紀戲劇中的人物。中世紀戲劇是禁欲主義和道德至上主義的。在中世紀戲劇中,美來源于克制,它借助道德和宗教力量實現與塵俗社會和市井生活的對照。《水莽草》通過平凡樸實的生活常態挖掘人性,是這個作品最可貴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在這個戲中,除了婆婆和媳婦之外,還有一個男人茂壯也是活生生存在著的。茂壯在母親和媳婦之間束手無策,于是編劇就用了“神來之筆”,讓這個“是非男人”缺位。茂壯離開后,婆媳之間又從三角關系變成了相對簡單的二人關系。于是,婆媳關系逐漸緩和,最后相知相惜甚至相依為命。從表面上看,男人的離開,少了很多是非,實際上,該劇中男人的缺位恰合中世紀戲劇的“克制觀”。編劇貌似要關照人性,實則抹殺了人性。
整臺戲看下來,我們禁不住要發問:茂壯是來打醬油的嗎?他在劇中的作用和身份是什么?這個角色給人的印象非常模糊,他既不鮮明,也毫無特點。在“孝道”為先的理念中,茂壯雖在情感上偏向媳婦,行動上卻一定要傾向母親才行,因此人的情感和行動就會出現脫節。編劇欲表現主角美好品德的初衷就會因這樣一個男人的存在而被打亂。這實際暴露出“道德倫理”這個護身符在編劇表現現代社會人的精神困境方面的不協調。
所以,在這個“上帝之手”的壓力下,編劇不得已對茂壯這個人物進行了肉體閹割、精神閹割和多重閹割。首先,茂壯媽責怪媳婦過門半年還“母雞不下蛋”,看似是對媳婦麗仙的嘲笑,也可以解讀為是對茂壯身體殘缺的一個暗示。其次,讓茂壯離家實際是對男性視角的一個刻意回避。茂壯的缺席淡化了《水莽草》的婆媳矛盾,反使麗仙悔罪、贖罪變成重頭戲。至于麗仙在丈夫眼中是何種形象,或者在兒子心中,母親的所作所為又是何種感覺,編劇并未照拂。茂壯的看法是不重要的。這是對男性視角、男性精神的一種有意疏離。再次,該戲還對茂壯的形象進行了多重閹割。夾在媳婦和婆婆中間的那個男人本應是婆媳矛盾的焦點所在。但是該戲在戲核上刻意造成了一種事實上的“閹割焦慮”。其實,演出伊始,劇情即交代:“寡母獨子”,那么,媳婦的出現必然打破了二人原本和諧穩定的關系。按說這個“第三者”所帶來沖擊才該是劇本著力要表現的內容。可是隨著劇情推進,兒子被母親趕出做工。這樣,編劇前面辛辛苦苦預設的前提又被自己稀里糊涂地消解掉了。這樣的編劇,不免給人一種莫名其妙、頭重腳輕的感覺,男人的缺位,導致“缺席的焦慮感和無力感”。這種“失控”實際是禁欲主義和道德至上主張在遭遇活生生的人類肉身和生命個體時,所產生的一種無法調和的矛盾。
三、偽善的象征性
《水莽草》從戲中所體現的道德規范和舞臺樣式來看,應屬舊社會的故事,編劇的本意大概也是借古喻今。道德教化初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世紀戲劇的寓言化傾向。中世紀的道德劇和宗教劇尤以象征性和寓言化著稱,所要揭示的道理無非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意即在宗教或集體主義光環籠罩下對人們遵守道德或者禮教的一種報酬性承諾。編劇楊軍說:“寫《水莽草》時我自己有一個‘寓言劇’的追求,我希望這個戲既充滿生活質感,但又和生活有一定距離,以‘非常態’體現寓言性”。可見,《水莽草》出發點是想通過一個家家戶戶都可能存在的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婆媳關系來隱喻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借此來傳達真善美品格的重要性。如果完全把這個戲當作一個輕喜劇去看,不去深究它所要傳達的社會道義,觀眾沉醉于演員的美、馮詠梅的表演美、人物的心靈美也就夠了。如此,還算尚好。但是,如果一旦深究這個作品背后的東西,去試著理解它所要傳達的寓言性,那么我們就會陷入深深的失望。
首先,在婆婆誤飲湯藥那場戲的編劇上,楊軍說《水莽草》最初的設想是媳婦不堪婆婆折磨,意欲毒殺婆婆,后又修改成媳婦不堪忍受婆婆,找來水莽草煎成湯藥,本想自殺,偏巧被婆婆看見,不由分說把媳婦熬好的湯藥喝了下去。這樣編劇貌似“守住了麗仙這個人物的善良本質”,也為她后面的后悔和贖罪提供了道德上的可能性,即可救贖性。但這樣處理讓明眼的觀眾很容易就看到編劇一直在極力維護的那個“道德”寓意上的破綻:麗仙明知湯藥有毒,婆婆卻是不知,婆婆誤會麗仙,麗仙卻無辯解,她阻攔婆婆,更加重婆婆疑心,最后貌似未攔住而致婆婆喝下湯藥。但是,麗仙真心勸阻婆婆了嗎?她或者從內心更希望婆婆自己喝下去,免得自己動手而致更大罪孽。若真如此,《水莽草》所要傳達給觀眾的“真善美”實際是建立在偽善基礎之上的。其實,從現實邏輯來講,要勸住婆婆,只需媳婦大喝一聲“那是毒藥”就夠了,可麗仙偏偏沒說。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她內心深處藏有一種縱容和共謀的動機。這比編劇楊軍最初設想讓麗仙直接想毒殺婆婆的想法,更讓人毛骨悚然。人的道德若有瑕疵,可以改正,人的道德若是偽善的,無法救贖。編劇還不如索性坦坦蕩蕩從人性出發,直面媳婦不堪忍受婆婆折磨的現實而對婆婆心生殺意,后深感良心不安,尤其漸覺婆婆的感情,所以幡然悔悟,進而贖罪。這樣編劇,可能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和情感邏輯。
此外,作為一個極力要打造的“寓言故事”,該劇結尾處也不盡人意。《水莽草》號稱具有象征性,實際并未讓人感覺有何象征意義。婆媳和好,茂壯歸來,兩個女人冰釋前嫌,相互體諒,“母慈媳孝”大概是每一個男人的美好理想吧。但是,要想成為一個象征戲劇,這樣的結果顯然是不夠深刻的。倘若編劇改一下結尾,或許會出現一些不一樣的效果。不妨這樣試試:婆媳和好,茂壯歸來,然后婆媳二人又相互不滿、開始互掐……讓故事又回到原點,進入一種死循環,這才更具有象征意義和寓言化色彩。婆媳關系尚且如此,再擴展到人與人之間關系,單純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規定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顯然是一個烏托邦想象。人類面對自身的困境,無法解決,無力掙脫,也無法避免,從而上升到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思考。現代人寧愿相信有瑕疵的真性情,也不希望看到神一般的存在,更不喜歡精神導師對我們進行苦苦婆心且根本不構成說服力的道德訓誡。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水莽草》還是不夠毒,其毒性遠不足以引發人們更多思考。
四、結語
水莽草是無毒的,或者說水莽草有沒有毒最終是取決于人的內心是善還是惡。老草仙是真人還是神仙,也不得而知。或許編劇意在說明美好道德會有一個好的回報,即所謂“善有善報”。但是在個人主義和個性要求如此鮮明和迫切的現代人面前,中世紀這套“上帝之手”顯然是蒼白無力的。雖然,我也承認滇劇《水莽草》是一首富有生活律動的民間小調,它用舞蹈化的動作表現生活中的人情,用直白如話的俏皮語言傳達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這都是很好的,包括演員馮詠梅的表演也是可圈可點的。但是編劇在劇情架構上的諸多硬傷也是現實存在的。我認為編劇沒有想明白中世紀的“上帝之手”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之間的不協調性。誠然,如果在主演和其他角色關系的處理上,把戲份適當分給其他演員一點,而不是主角的獨角戲,可能會更好一些。更重要的是,道德信念如果總是跳出來支配編劇,這個戲就會失去很多本該有的思辨性。茂壯這個人物若能突破活道具這個擺設角色而真正發揮作為一個兒子和一個丈夫甚至一個男人的作用,婆媳間的戲劇沖突可能會增彩不少,人物關系也更具合理性。在編劇上,對于男性角色的閹割無論如何都是對該劇本不小的傷害。讓戲劇本身具有象征意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要想讓該戲更具寓言效果,編劇還需要再深入思考如何才能讓這個戲更深刻、更抓人心。《水莽草》的“毒性”還是稍欠那么一點點。
[本文為北京市教委社科計劃面上一般項目“戲曲文本譯介主體和譯介策略研究”(項目編號SM201710049003)的階段性成果。]
[1]蒲松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張友鶴校[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楊婷.高原之鶯馮詠梅[J].中國戲劇,2016(04).
[3]楊軍.讀懂一個劇種的生命精魂 滇劇《水莽草》創作談[J].中國戲劇,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