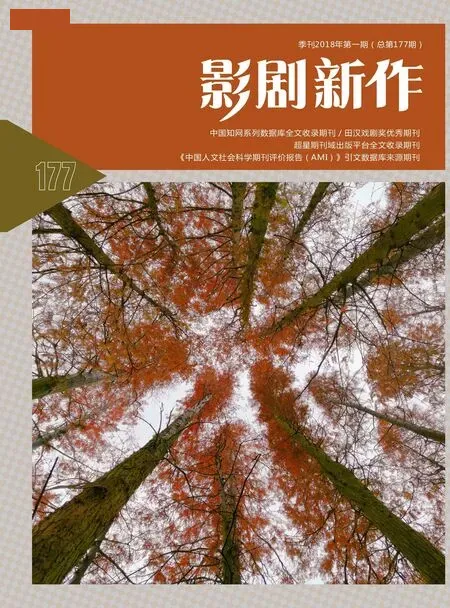戲曲的傳承與發展
——觀十地方戲曲劇種《桃李梅》的幾點思考
高桂峪
“花開桃李梅――十地方戲曲劇種《桃李梅》同城會演”是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也是吉林省省級文化發展專項資金扶持項目。此次在長春的會演匯集了越劇、秦腔、河北梆子、評劇、唐劇、呂劇、豫劇、茂腔、閩劇、吉劇等十個地方戲曲劇。筆者有幸全程觀看。十場地方戲《桃李梅》看下來,有幾點感觸和想法,以供方家思考。
舞臺布景
舞臺布景或者舞臺設計,這其實是個西方戲劇語匯,是個舶來品,英文是Stage Design或者Scenograph。傳統戲曲舞臺中是不存在舞臺設計或舞臺布景的,戲曲舞臺一般是三面面向觀眾,唯一的所謂布景是一塊供演員出相入將的刺繡帷幔。位于舞臺的后區,在其一左一右各有一個門簾,門簾上方分別寫有“出將”和“入相”二字,作為演員演出的上場口和下場口,稱作“鬼門道”。因保留古制,便稱其為“守舊”。但“守舊”只是它本身,不代表任何環境和地點,其上面的圖案也不代表任何的階層和時代。十場地方戲《桃李梅》的舞臺布景,受話劇的影響,整體偏向寫實性,無論是后區背景還是場中道具。花園場景就掛上花園的畫幕,河流場景就掛上河流畫幕,沒有留有讓觀眾想象的空間,明顯在向話劇舞臺樣式靠攏,偏離了傳統戲曲舞臺的演出呈現,丟失了戲曲演劇所特有的“寫意”性。其實演員上場會自報家門,一句話就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環境地點,不需要寫實的畫幕來呈現。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中“十八相送”經典橋段,僅憑演員的身段、手勢、唱腔,就可以完成一個個場景的轉換,觀眾也相信它是真的。相反,當舞臺上真的出現大量實景,反而會讓人覺得很假。如若要表現一座山,就真的在舞臺上用石頭、黃土搭一座山,滿臺子都是黃土,那戲曲所特有的虛擬性、程式化和意境美會蕩然無存。
劉杏林老師在其設計的諸多戲曲舞臺作品中找到了戲曲舞臺空間的本源,虛實相生,透露著中國古典之美。舞臺布景并不是一味的繁多寫實,而是根據情景和人物內心的表達而生發的寫意空間,簡約而又不乏新意。在有限的舞臺空間里把布景最簡化,而空間的留白,更會讓觀眾產生無限的遐想。在《陸游與唐婉》中,舞臺詩意唯美,將“大寫意”的戲曲美學精神擴張到了極致。布景追求一種空靈、婉約的“無我之境”,舞臺左右兩側的兩道月扇門,既可視作傳統戲曲舞臺上“出將”和“入相”的上下場口,又將古典園林的意韻渾然天成地融入到劇情之中。在“題詩壁”的舞臺場景中,跨越時空的陸游與唐婉二人同時出現在舞臺兩側,這時紗幕上墨痕依稀的一行行詩文漸漸清晰,陸游的題詩與唐婉的和詩同時呈現并且交織在一起,詩的交融也暗喻了陸游與唐婉的心也緊緊地聯結在了一起。舞臺布景借物喻人,讓人稱絕。
一桌二椅
“一桌二椅”為戲曲表演的寫意性和虛擬性提供了基礎。既可作為不同場合的桌椅,又可指代山、樓、床、門等景物。通過不同的擺法和桌圍椅帔的不同色彩與紋樣,對劇情的地點和人物關系作出暗示或說明。可以說,在戲曲的發展史中,“一桌二椅”的創造是古代戲曲人智慧的結晶。
十場地方戲《桃李梅》劇中對“一桌二椅”這種假定性的運用有所缺失。假山就放一塊寫實的山石,審案子的公堂放上巨大的平臺和積案,閨房中設置真實的屏風。其實,利用舞臺道具的虛擬特性,兩把椅子摞起來同樣可以指代是假山石,兩個桌子組合可以成為公堂的積案。“一桌二椅”的假定性曾創造了多少舞臺智慧,傳統劇目《三岔口》抹黑搏斗的經典橋段中,“一桌二椅”可謂用得精彩,時而表示是任堂惠的床,時而是餐桌,時而是窗臺,并且根據情景和場景臨時組合,觀眾都能夠看懂并欣然接受。
張曼君老師曾為寧夏秦腔劇團排演的《狗兒爺涅槃》中,靈活運用了戲曲“一桌二椅”的假定性。她找到了一個切入點——長條凳。長條凳之間通過拼接組合,可以是炕,可以是門樓,可以是木橋,幾乎所有的場景都合理解決了。這是張曼君老師對“一桌二椅”假定性的傳承和發展,是一種對傳統戲曲舞臺空間藝術的回歸,其思維方式仍然是戲曲舞臺假定性的處理方式。有時只需要演員的一句自報家門,它就可以成為任何場景。只不過現在對這種假定性的運用慢慢在丟失,一些好的東西我們并沒有傳承下來。更多的戲曲舞臺空間場景的處理受現代話劇的影響,朝著更為寫實、更為直接的方向發展,相比之下,張曼君老師的舞臺呈現更為純粹,更為質樸,更接地氣,更有意境。
“絕活”
傳統戲曲舞臺上除了守舊,只有一桌二椅等砌末道具,空無他物,但只要主演(角兒)一上臺,馬上便景隨人移,氣象萬千。戲曲一定程度上是“角兒”的藝術,一位名角兒演員,往往可以力挽狂瀾,改變一個劇目甚至一個劇種的低迷處境。戲曲界以前實行的就是主演(角兒)挑班制度,說起梅蘭芳,就是承華社;說起程硯秋,就是秋聲社;說起馬連良,就是扶風社。每個角兒身上都有自己的“絕活”。十場地方戲《桃李梅》劇中,沒有看到讓人眼前一亮的“絕活”,甚是可惜。
要想成為角兒,這要求演員一定要有“絕活”。空曠的戲曲舞臺上,看的不是別的,就是演員的“絕活”。何謂“絕活”?我認為是演出中吸引人眼球的東西,并且要引人注目。聚焦在演員身上,就是通常被稱為“四功”的“唱念做打”。唱指唱功,念指具有音樂性的念白,二者相輔相成,構成歌舞化的戲曲表演藝術兩大要素之一的“歌”;做指舞蹈化的形體動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藝,二者相互結合,構成歌舞化的戲曲表演藝術兩大要素之一的“舞”。
說起來簡單,“唱念做打”是戲曲表演的四種藝術手段,同時也是戲曲表演的四項基本功,但是真正兼備“歌”和“舞”的戲曲人才鳳毛麟角,擁有其中之一突出的,就很是不易了。舞臺上,要么你唱得好,要么武功讓人叫彩,要么別的演員演同樣的劇目沒人能超過你,說得簡單點這就是“絕活”。別人沒有的,做不到的,同樣這也是這個演出的“看點”。2017年十一屆文華大獎的最佳表演獎第一名頒給了《焦裕祿》中焦裕祿的扮演者賈文龍,我認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賈文龍身上有“絕活”,讓這個戲有了看點。賈文龍身上不僅有功夫,唱得又好,這樣兼得“歌”和“舞”的演員十分難得,少之又少。劇中焦裕祿因為肝癌的疼痛忍無可忍的情景中,賈文龍用了程式化的翻跟頭來表現身體的疼痛,并且連翻了3個,西安大劇院整個劇場掌聲雷動,觀眾看到了他身上的“絕活”,他把劇中人物和行當真正地結合了起來。
不僅僅是戲曲,其實任何一部賣座的演出都要有“絕活”。國家話劇院和英國國家劇院聯合演出的舞臺劇《戰馬》即是如此。里面的傀儡戰馬就是這部戲的“絕活”和主演(角兒)。在這樣一部以“戰馬”為主角的作品中,英國國家劇院大膽地嘗試結合多種藝術形式,與南非木偶劇院(Handspring Puppet Company) 合作,選擇了一種源于非洲馬里獨一無二的工藝以及“實操傀儡”的方式,使得沒有生命的傀儡戰馬“Joey”在舞臺上展示了全新的生命與活力,這一前所未有的難度課題歷經了五年的磨合與試驗,終于成功。“Joey”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和豐富的表現力、震撼的視覺效果,征服了所有的觀眾。《戰馬》和其他的舞臺劇的創作有本質的不同。其他的劇目都是先有了劇本或者即興集體創作,然后導演等創作團隊跟進,完成整部戲的演出。但是《戰馬》是先有了這匹惟妙惟肖的傀儡馬這個“絕活”,之后所有的創作是圍繞著這匹傀儡馬來進行。可見“絕活”在舞臺上的重要性和決定性,觀眾驚嘆于舞臺上的“傀儡戰馬”。
二道幕與撿場人
新中國成立后,進行了以“凈化舞臺”為目的“改戲、改人、改制”的戲曲改革,一些不好的傳統的確要剝離,但有一些是否要傳承保留,也未可知。在觀看十場地方戲《桃李梅》劇時,有一個特別讓人不舒服的處理,就是舞臺上的二道幕在演出中不斷地開合,這貌似也是戲曲演出的常態,一種不可缺少的固定演出模式,觀眾似乎已經接受并習以為常了。二道幕的出現的確解決了大的場景切換的問題,控制住了演出的節奏,但卻嚴重割裂了戲曲的舞臺空間。其中有一場戲,燕文敏在空場和死對頭總兵方亨行巧遇時,新仇舊恨疊加在一起,拉開架勢本應該是大場面,但是為了遷換布景和道具,強行拉下二道幕,使得燕文敏和方亨行相互的爭斗卻在一個狹窄大約3米的前區展開。十幾個演員堆在一起,極不舒服。
建國以后,對傳統戲曲進行了“戲改”,去除了舊戲曲中的許多糟粕的東西,為了“凈化舞臺”,不再讓“撿場”人員明場在舞臺上出現,換景都要閉起二道幕進行遮掩。于是在演出中,二道幕就不斷地開開閉閉。過去傳統戲曲演出,搬移桌椅、布置道具,全由負責布場的“撿場”人員來完成。所謂“撿場”,就是演出中舞臺上的工作人員。他們負責在演出中,搬置道具、撒放火彩,幫助演員更換服裝、遞給茶水、毛巾等。并且“撿場人”可以在不打斷演出的情況下明場換景,因為戲曲舞臺的假定性默認為他們是不存在的(不是劇中的人物),觀眾也默許。
然而,我們舞臺上凈化去掉的“撿場人”在日本演劇中卻被完好的保留。類似于中國戲曲的“撿場人”,在日本叫“黑子”或“黑衣”,只在歌舞伎和文樂(音:wén lè,即木偶凈琉璃)中出現,而在日本的其它演劇形式中不存在。歌舞伎中的黑子相當于“撿場人”,身著黑衣戴頭套(但也有不著黑衣不戴頭套)負責幫助演員化妝、現場迅速更換衣服、遞送道具以及清理舞臺等,是作為隱形人出場的角色。除了著黑衣外,在表現水場面則著藍衣,白雪場面則著白衣,一般都泛稱“黑子”。筆者曾經看過一場歌舞伎的演出,“黑子”幫助身著黑色和服的女主演當眾明場瞬間換成大紅服裝,讓人驚嘆不已。這也成為這個演出的“絕活”和看點,讓人津津樂道。“黑子”在演出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日本的“黑子”除了是 “撿場人”,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傀儡手(操縱木偶的人)。在日本文樂中,“黑子”指的是操縱木偶的人。雖然有些文樂木偶只需要一個人操縱,但大部分的文樂木偶都需要三個“黑子”同時操縱,分為主操縱黑子、左操縱黑子和腳操縱黑子。一般這三個“黑子”都要著黑衣且戴頭套,但有威望的且受人尊敬的主操縱黑子可以不戴頭套不著黑衣,以真人面目示人,這樣的主操縱黑子被稱為“人間國寶”。“人間國寶”是文樂中最著名的演員,是至高無上的榮譽稱號。因為他們的技藝精湛,觀眾不會因他們的形象而分散對木偶的注意力,使得觀眾只會關注于木偶本身的表演,而忽略了傀儡手的存在。
中國戲曲演員的技藝不可謂精湛?“撿場人”的存在真的會干擾演出?傳統戲曲的演出不就是大家一邊喝茶,一邊吃瓜子,娛樂中聽戲。把“撿場人”凈化后產生的諸多舞臺美學問題,應該值得我們思考。
小結
戲曲應當是俗的藝術,不是所謂的高雅藝術,不要把它放在一個高的基座之上,它應該是流行音樂,是大街小巷大家耳聞能詳的東西。筆者曾有個親身體會:二人臺地方小戲興起于山西,但發展于內蒙古。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二人臺藝術劇院下鄉惠民演出,因為車輛拋錨演出遲到了。等到了地方,我們發現全村幾百人老老少少站在村口等著武利平老師的到來(梅花獎獲得者、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二人臺藝術劇院院長),《霸王別姬》里面追捧“角兒”的場面,我第一次感受到。戲曲需要接地氣,需要是草根文化。戲曲本身到底是什么?它需要找回它“最傳統”的純粹模樣,進而激活觀眾的情感體驗和生活體驗,探索它正確的、科學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本文為內蒙古自治區高等學校重點科學研究項目“原創民族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舞美創作理念與實踐研究”(項目計劃編號:NJSZ17661)的階段性成果。]
[1]蔡敦勇編.戲曲行話辭典[M].臺灣:國家出版社,2012.
[2]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M].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