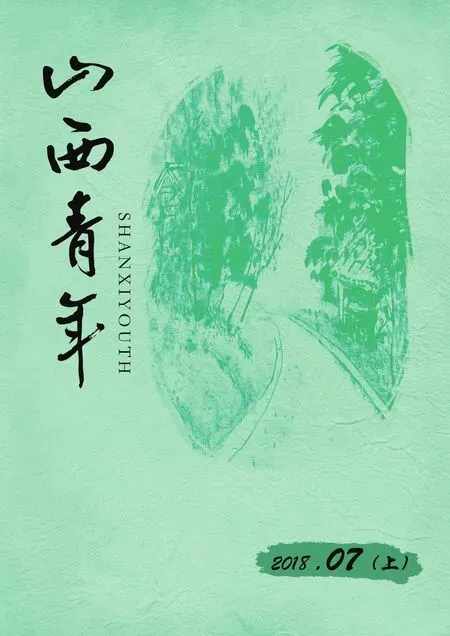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綜述
——基于政市關系視角
郭丹丹
(延安大學,陜西 延安 716000)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三去一降一補”以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的動態平衡。
一、背景研究
(一)理論基礎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到“供給側改革”。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直接目的是擴大有效供給以期適應新常態。
孫家良和趙星宇(2016)指出薩伊定律(生產、交換、分配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是消費)、供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因其特定時代背景、經濟適用條件有局限性。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理論。其理念是利用市場競爭規律實現供需均衡及產業提升,強調供給端與需求端協同以促使產業升級,其核心是針對不同問題使用不同工具進行綜合治理。
周燕(2017)從供需兩大學派爭議入手,以新供給觀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基礎。新供給觀代表張五常教授將薩伊定律與斯密分工理論結合,形成“產權界定—價格準則—降低交易費用—分工利益—經濟增長”式理論鏈,指出改革應解決“僵尸企業”、“產能過剩”、“勞動成本上升”及因此帶來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姜士偉(2016)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行政學思維的經濟學命題”,其關鍵是政府改革。婁成武(2016)認為政府體制機制有較強延續性而隨時間推進對經濟發展產生阻力。因此政府應注重放權,供需聯動并進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石瑛(2017)梳理西方經濟思想及經濟史發展脈絡,提出供給側改革主要針對‘滯而不漲’和供給過剩的難題。曾盛聰(2017)利用“生產性”方法論,集中關注政府公共生產職能,矯正公共服務范式泛化、極致化導致“訴求—滿足”“福利—消費”的消費主義偏執,將政府治理的理念矯正到“生產—服務”“產出—消費”相互制約、辯證統一的關系上來。他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公共生產的基本目標是社會生產最大化及產出的質的提升。
綜上所述,學界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前提不同,但其研究切入點多為供需經濟學派分歧或經濟實踐。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協同創新以實現經濟長效發展的一系列變革措施的總稱。
(二)實踐背景
根據《經濟轉型視角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論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基于我國環保形勢嚴峻、能耗高而能效低、低端產能過剩現狀,《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經濟工作的重要論述》提出,目前我國處于“三期疊加”階段。
1.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一是增長速度轉換。我國長期以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資金高投入為代價實現經濟高增長。經濟中高速增長是經濟規律與政策主動調整的結果。二是增長方式轉變。由粗放型要素驅動增長變為創新驅動增長。三是增長動力變化。我國人口紅利減少、外需拉動減弱及科技創新發展要求尋找經濟持續內生動力。
2.結構調整陣痛期。包括國企改革、第二產業內部結構性矛盾及投資結構調整帶來的過渡期企業競爭與產能減少的宏觀環境適應性變化。
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一是消化刺激政策依賴癥。政策依賴導致市場功能退化、社會創新減弱、企業投機增加及投資沖動。中央政府采取緊縮性政策以防經濟過熱,但地方政府產生財政壓力要求中央政府擴大信貸,由此造成我國宏觀政策陷入反復。二是粗放增長的經濟發展外部性即透支環境造成的社會成本需要消化。姜士偉認為,現代中國計劃經濟思想仍然存在,導致政府奪位于市場現象頻現,市場獨立性與完整性不足。供給側改革目的是還市場以獨立、自主權,實現政市關系平衡。
黃新華(2017)指出,需求管理政策邊際效果遞減,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出口、投資結構失衡,引發結構性產能過剩、高端技術產業短缺要求供給側結構進行改革。
綜上所述,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矯正我國長期需求側管理的刺激性經濟政策產生的負面效應及“三期疊加”經濟現狀的必然選擇。
二、相關研究綜述
(一)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總體研究評述
孫家良和趙星宇指出,市場失靈和政府職能轉變不足的不同層次疊加,需要制度變革以釋放市場活力。由于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缺陷,需要宏觀與微觀及社會政策共同作用以保證改革效果。宏觀政策穩定是保證市場預期及信用的基礎,微觀政策即通過減少行政審批、鼓勵“雙創”、制止投機激發市場活力,同時利用社會政策化解市場經濟下公民的社會風險。
周燕認為,供給側改革目的是使經濟實現質量提高。政市邊界不清所帶來的交易性成本是我國經濟發展困境根源。劉志彪(2017)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滿足服務需求、提高供給質量、完善市場決定性作用機制三個層次。政府應從微觀干預企業轉向高質量制度性保障。
姜士偉認為,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政府的回應性及有效性。政府改革能否建立起現代市場運行所需的政府體制是成功推進改革的決定性要素。因此,經濟結構和供需關系的變化及行政權力擴張導致資源配置扭曲要求政府以簡政放權、減少審批事項、清理規范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降低制度性成本的方式為企業發展創新營造良好市場環境。
曾盛聰認為,政府需要發揮彌補市場弱點和支持市場功能的作用,恰當運用政策工具與制度安排在宏觀維度進行資源與要素的合理調配與優化配置矯正結構性失衡。曹愛軍(2017)指出政府在干預經濟領域應明確職能,在民生領域需要政府主導。顏冠鵬與冉啟英(2017)認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現我國經濟新動力。官員晉升績效制、土地戶籍制度不健全、監管、稅收與社保制度不規范導致生產、房地產過剩。因此,應通過建設綜合性官員晉升制度、促進土地制度及戶籍制度公開化與平等化、完善金融監管法律法規及監管機構淘汰制、促進社會保障制度費率差異化實現“三去一降一補”。
綜上所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政市關系重構,關鍵是政府改革。企業以創新驅動經濟持久發展與政府還位市場并行以調整結構失衡,建設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路徑研究
周燕認為,當前“供給側改革”的路徑一是清楚界定政市職能,二是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邊界,發揮其比較優勢,形成特色性產業結構。
遲福林通過論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企改革、產權保護、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市關系,指出政府應簡化行政審批、推進監管及產權法制化,在保證國家安全及監管到位的前提下賦予企業自主權。陳斌開(2016)指出有為政府是有效市場重要條件和供給側改革主要動力,政府應堅定市場化改革、國企改革。政府需為市場提供透明、便捷性服務和有益于創新的產權保護。
姜士偉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以市場所需供給創新政府。政市再平衡的主要途徑是放松政府規制,即選擇性地放松和取消破壞政市平衡的制度壁壘。政府規制要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實現,營造公平開放的市場運行環境。
楊宏山(2016)認為供給側改革的根本是制度創新增加有效供給并釋放新需求,并借鑒深圳模式提出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利用信息技術等戰略性新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發展PPP模式改進公共服務供給的建議。曹愛軍主張通過協同治理,加強社會性公共支出推動公共服務供給多元與質量,使政府與市場利益相容且目標一致。石瑛從政府改革角度提出制定政府權責清單權力運行程序、及時公開并發布信息、優化行政決策議程等措施促進政市良性互動,實現優化供給結構與提高質量的長期性目標。
曾盛聰提出三種措施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政府要根據戰略計劃過程精準識別其應集中關心和運作的區域并將績效測量和評估反饋至下一輪戰略計劃實施中。加強政府在改革中對產業轉型進行政策資源傾斜與戰略引導。二是政府要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消除微觀主體間的沖突及負外部性。三是強化國有企業發展助推政府的公共生產。
三、結論
學界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措施因對市政關系認識邏輯不同而分歧。學者研究的共識是: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適應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的經濟新常態,建設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而進行的改革。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需求側與供給側聯動協調,并行推進。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通過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以擴大有效供給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此促進經濟的長效發展。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政府改革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市場創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與制度支持。同時,市場應發揮其創新力強的優勢形成良性競爭。二者相協調才能形成持久性經濟增長動力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建設。
[1]孫家良,趙星宇.經濟轉型視角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2]周燕.“供給側”改革中的政府邊界研究[J].學術研究,2017.7.
[3]姜士偉.供給側改革行動邏輯的行政學解讀[J].求是,2016.6.
[4]婁成武.中國政府改革的邏輯理路——從簡政放權到供給側改革[J].貴州社會科學,2016.7.
[5]石瑛.供給側改革視角下的政府職能轉變[J].長白學刊,2017.1.
[6]曾盛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政府公共生產[J].社會主義研究,2017.2.
[7]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 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0(02).
[8]黃新華,馬萬里.從需求側管理到供給側改革政策變遷的內在邏輯[J],新視野,2017.6.
[9]遲福林.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是深化結構性改革的關[J].行政管理改革,2017.2.
[10]劉志彪.深化經濟改革的一個邏輯框架——以“政府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探索與爭鳴,2017.6.
[11]劉志彪.政府的制度供給與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J].學習與探索,2017.2.
[12]曹愛軍.公共服務“供給管理”的邏輯進路[J].新疆大學學報,2017.1.
[13]顏冠鵬,冉啟英.供給側改革、全要素生產率與制度創新[J].商業經濟研究,2017.5.
[14]陳斌開.政府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J].人民論壇,2016.3.
[15]楊宏山.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在于制度創新[J].人民論壇,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