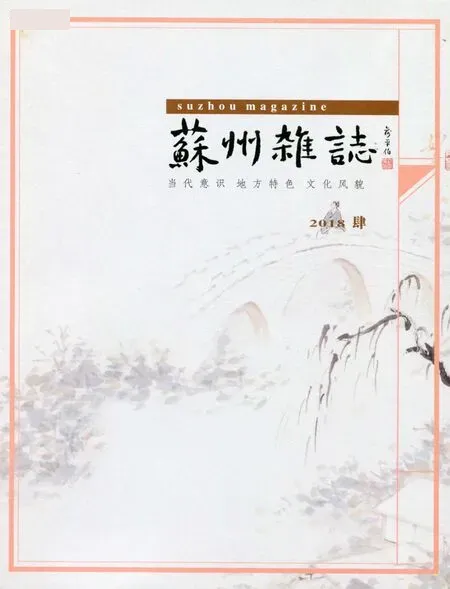1982年 陸文夫在江蘇師范學院的演講
朱子南整理
我們的文學事業分創作、理論批評、教學三部分。教學部分占了很大部分,直接影響到下一代的文學欣賞水平。文學欣賞水平是很重要的問題,直接影響到創作水平,而且影響得很厲害。過去,文學欣賞水平拖了我們很大的后腿,群眾輿論對創作有影響。文學水平高的一些作品,往往不被人重視,有些作品水平并不高,甚至很不高,卻引起了轟動,影響了作者和編輯。欣賞水平提高是逐步的,大學寫作教學擔負著重要的任務。在外國所謂暢銷書,許多是沒有學術價值的。我來講,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包括理論家、批評界。創作人員不是躲進小樓成一統,要社會各方面配合。
我從五十年代開始,摸索著寫點東西。五七年、文化大革命都沒寫,文革后才寫了個時期。要真正探討些東西要花力氣,要看很多書。現在一些討論常常在概念上爭來爭去,有些連概念也沒搞清楚。創作實在是沒經驗好談的,這個作品的經驗和那個作品的經驗常常是相反的。短篇創作更不好談。一個人的經驗就是他走過的彎路,彎路就是最好的經驗。我們現在往往只研究真理,不研究謬誤,實際上正確就是從錯誤中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研究謬誤產生的。下面講一點,但不是創作經驗。
前一段時間想到評價作品的問題,從生活到創作怎么構成?大家不知是否注意過一個現象,我們這里誰也沒有見過魯迅,更遠一點,誰也沒見過曹雪芹,但看了他們的作品后,就認識了他們,而且形象很吸引你。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作品,一個好的作品,哪怕是一個短篇,都應該看出作者其人。魯迅作品常用“我”,祥林嫂最后向“我”走來詢問有沒有靈魂的一段給人印象最深刻。我看到這里就覺得魯迅站在面前。“我”也是個人物。現在有的小說“我”不像我,作為闡明的工具,作為陪襯,或者故意把“我”壓得很低,像小丑一樣,這沒意思,“我”成了砝碼,砝碼很輕,稱起來的東西也重不到哪兒去。熟悉作家作品的人,對作家的了解有時勝過他的親人。有的人寫得很多但看不出作家形象。巴爾扎克像魔鬼一樣,對社會進行血淋淋的解制(剖)。柳青,看作品就好像看見一個老頭在那兒思考。《創業史》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梁生寶是一個真實的人。這些事實向我們提出了小說創作中的一個問題:每個作家他幾乎都在寫自己的歷史。這話并不奇怪,每個人生活在社會上都在寫自己的歷史,寫自己的歷史就是寫自己碰到的、經歷過的。你寫的不是自己,不能表現自己的話,那作品中就看不出你這個人來。看魯迅作品就看不出魯迅,看巴金作品就看不出巴金。這就牽涉到現在討論的“表現自我”的問題。有人說“表現自我”是不正確的,“自我表現”表現“大我”,是正確的,我覺得主要要看作家對歷史、對現實的評價,小說就從這里產生。有人說寫出小說是“點子”多,“點子”也要具體分析。生活中有些事看來小,都可寫成小說。我覺得這是從作家對歷史、現實、生活看法中來的,不從這地方中來,產生小說是很困難的。魯迅站在歷史的角度考察現象問題,就產生了《一件小事》和《阿Q正傳》,沒有對歷史的認識是不會產生的。
我們有一個時期對某些東西強調太多,如從生活出發、從真實出發問題。我不是否定它,但完全強調這一點,也不解決問題。某些青年作者常說自己作品完全真實,強調太過分,也要產生負作用。藝術上完全真實也是不可能的。完全強調真實就不好寫。我看主要的還是認識的正確。當然,認識的正確并不脫離生活的真實。小說的產生,來源于作家對生活中發生的事的思考,加上自己的知識向外延伸,再回過來。這就是生活的還原。人對生活中的事都有評價,這評價隨著知識的發展、歷史的內涵,有所發展,這就決定了作品的高低。一個人對生活沒有評價,生活的東西就凝結不起來。簡單講講主題,不能把主題想得太死。作品的每個細節都放在作家的評論眼光之下。魯迅對一件小事沒有評價是不能產生作品的。我們知道,生活本身是問題的一面。對生活的認識評價并借助你知識向歷史深度擴展,這對創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認識的問題解決不好,作品的高低在這里就區別出來了。《阿Q正傳》寫成滑稽戲,同一題材在不同的作家手里寫出不同作品,原因就在于此。
從形象出發形成概念,再從認識寫成形象,就產生了作品。就事論事的作品就不深刻。有些作品生動活潑,語言也好,可看起來沒大意思。認識不全面寫出來的作品也不全面。有篇作品寫老農民富起來后買錄音機,寫得簡單,再想想,就會深刻些,老農民是怕露富的,社會生活是復雜的,環環相套的。獎懲制度的推行要社會的配合,克服不容易。我們寫小說對生活現象要深入研究,對生活要有正確的認識。作品內涵深不深,不在于你寫得尖銳不尖銳。年青人火氣大,不能解決問題。創作的人對一些生活中的不良傾向不能熟視無睹,對生活無所謂就不能創作。我們要把問題前前后后都考慮進去,作品的內涵才會加強。搞創作的人要研究許多問題,研究未來,國外情況也要研究。研究后會在字里行間流露出來,這不是賣弄知識,賣弄知識不對。有人賣弄美學、音樂知識。寫音樂家,D大調,其實他自己也不懂。在作品中,也不能把知識赤裸裸表露出來,要還原到生活中去。寫農民,和農民一樣。趙樹理古典文學修養很好,但寫農民時不把這些拿出來,寫農民就是農民形象。還原到生活中情況如何,看出作家水平如何。還原生活要渾然一體。上面是講認識問題在創作中的重要性。
另一個問題是作家和作品中寫的人物要處于平等地位,這樣寫人物才會顯得親切。現在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作家和讀者要仰起頭來看人,另一種是俯視的,居高臨下的態度,這更不好。成熟作家的作品他們和人物都處于平等地位。小說最怕板起臉孔教育讀者,這樣感染力不大。要感染人,處于平等地位,不能以理訓人,要以情動人。三十年代寫勞動人民都是用人道主義,憐憫的目光。這樣向下看不好。今天不能這樣寫。寫什么人要和什么人站在一起,這樣才寫得出來,人物才是可親的。
創作中兩個事情最困難,一是認識不清,形成不了自己的認識;二是認識形成了,覺得沒什么好寫,原來材料遠遠不夠。但當向生活一靠攏,就好寫了。我寫《小販世家》就是這樣。過去的一些生活積累靠近了,就產生了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一般說人物總是逐步明確起來,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搭起來,產生制約關系后,才清楚起來。人物命運總是受作家支配的,說作品中人物命運不好控制,實在是由于作家后來改變了主意的關系,總受他們認識的制約。
教小說很難教,清楚點講,味兒沒了,不清楚講又講什么呢?所以很難講。好像我們的腦子,不打開,又不知道它是怎樣運動的,打開了,就完了。作品本身很復雜,理解的深度、厚度,有時也隨時代不同而不同。文化革命以后有些作品并不那么好,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在內,但因為它的影響比較大,反映了一段時期內人們共同的要求。作品的輸出接觸點不同,產生的反響也不同。文學作品多樣性,高標準的作品也是逐漸發展的。作品的深厚有時代因素,要經得起看,經得起時間考驗。
寫什么的問題實在不存在。我認為什么都好寫,只是不寫不熟悉的東西就行了。我認為存在的問題是怎么寫,各種問題都在怎么寫上體現出來。
寫小說最怕“搞運動”、“趕浪頭”。這“運動”不是中央提的,是我們自己搞的。粉碎“四人幫”以后,有這樣幾個階段。先是寫爪牙作亂,再寫老干部平反,第三階段寫知識分子受難。寫右派問題不是那么簡單,有的寫得很離奇。要好好領會一下知識分子的地位。作家總是對生活有深刻了解的,不了解語言就出不來。用認識代替藝術也不對,有的直接說出來了,說理過多,讓人物急急忙忙把意圖講出來,這就不好,不耐看。作品愈是不好,愈是不好講,我們在課堂里怎么辦呢?
讀者是跟人物走的,你給的僅僅是一些指示,每個人都要用自己生活的經驗去補充小說。高明的作家總是不寫干凈,給人留下補充的余地。這樣補充后,各人對小說的評價就不同了。我們講小說是講的一些基本概念,這一講就講死了。補充不是用道理,而是用形象。好的小說用幾筆就能引起人的想象,讓人擴展。寫干凈的小說是沒有什么看頭的。把一篇小說局限在一個問題上恐怕不好。作家認識是有限的,人們去補充才是無限的。
前一時期把小說作為解決一段時期內的問題的工具,這就不對了。小說也會引起社會的非議。落得太實了不行。題材問題上落得太實不好。有的說,這個小說是寫農民,那個小說是寫知識分子,實際上農民和知識分子是聯系在一起的,農村也有知識青年,不太那么好分。小說總是寫人生,寫社會,分得太死不好。作品不好尖銳,尖銳就是集中到那么一點。尖銳和深刻是兩回事。好作品能引起人們長時間的深思,即使是把小說的名稱和作者都忘記了,但小說中的人物還留在我們頭腦中。現在學校里有些人對國外很感興趣,什么荒誕派、意識派、印象派,對這些東西很感興趣,這也是可以的,他們感興趣點也是可能的,這是好的。但要多研究一些,慢點去肯定,慢點去落筆。文學總是繼承性,要割斷,要一下子就爆炸原子彈是不可能的。搞創作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一事當中,落筆太急不行。
有的作品太低了,理解太窄也不行。《賞嘗之下》就寫得比較全面。寫得太低不行。
寫小說不能沖動,愈是沖動,愈是不能寫。小說不是詩,情緒最激動時最容易偏激,這時就不能寫。寫小說是幾冷幾熱。題材在腦子里不是一天存在的,總是想了好長時間的,天天在想,甚至大便也在想。太匆忙的小說總是不太好。有的作品丟一個時期也可以。小說創作不受時空限制。
一個作家總是想把自己的生活體會、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告訴別人,讓別人有所選擇。要把文科作為自己終身的伴侶。成為作家的偶然性很大,當然也有必然性。我開始時就從來沒想過自己當作家,作品確實是自己感情的抒發,真正寫起來了,倒真正可以寫出作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