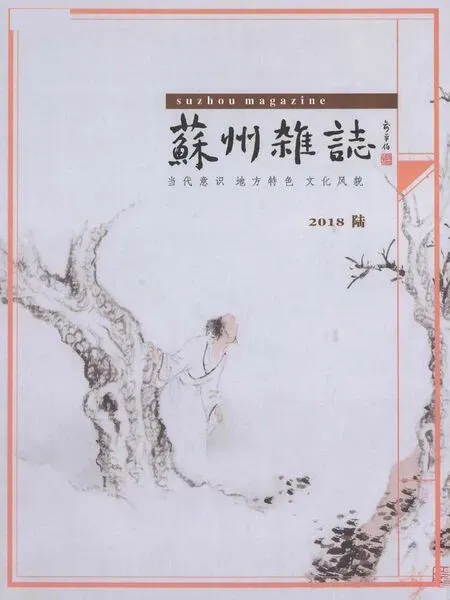東小橋隨記
朱子南
蘇州禁演評(píng)彈的一樁公案
見王汝剛先生《說書先生“打相打”》一文(刊2016年6月22日《新民晚報(bào)》),其中說到蘇州的流氓地痞為收保護(hù)費(fèi)而挑釁滋事,著名評(píng)彈藝人馬如飛上告官府,而官府的批文故意把馬如飛狀紙中所寫“說書雖非正業(yè),接近衣冠”一句,改為“說書雖近衣冠,終非正業(yè)”,以貶低藝人的社會(huì)地位。此說,與我聽到的有所出入。按理,馬如飛是不會(huì)把自己從事的藝術(shù)活動(dòng)說成“雖非正業(yè)”的。
同治年間,所謂“同治中興”以后,蘇州百業(yè)已漸趨復(fù)蘇,不幾年,又呈現(xiàn)一派繁華景象。評(píng)彈業(yè)界也名家輩出,在書場(chǎng)、茶室中的演出,吸引了眾多評(píng)彈愛好者前往,在休閑中欣賞說表彈唱俱佳的說書。故事也出在這里。
在寬僅丈余的干將場(chǎng)巷(今已拓寬為干將路),一天,小巷南北兩家茶室都有演出,都是名家出場(chǎng),有“打擂臺(tái)”的味道。這可吸引了眾多評(píng)彈愛好者,不但茶室內(nèi)座無虛席,在門口也擠滿了人聽書。本來不寬的小巷一時(shí)是擠得滿滿當(dāng)當(dāng),連行人走路也得一步步擠過去。恰巧,其時(shí)一頂官轎過來,即使鳴鑼開道,也轟不走正聽書聽得入迷的兩邊聽眾。這下,把坐轎的巡撫像現(xiàn)今堵車一樣堵在小巷里了。這可把巡撫氣壞了!回到衙門,就出了一道布告,其中有云:“說書雖近衣冠,終非正業(yè)”,這前一句是指評(píng)彈藝人都是穿著長(zhǎng)衫上臺(tái)的,有別于“短打扮”的工農(nóng)大眾,后一句則以“終非正業(yè)”為由,把評(píng)彈演出給禁了。這引起了軒然大波,蘇州人對(duì)評(píng)彈的愛好非止一日,也非止一代,自乾隆下江南,聽了王周士的說書,叫好不迭,還把王周士帶到北京,進(jìn)入內(nèi)苑演出。其時(shí),老百姓通過各種關(guān)系,向巡撫的幕僚游說,希望他們能在巡撫面前美言,以使收回禁演的成命。恰好,幕僚中也不乏評(píng)彈愛好者,有了輿論的支援,老百姓的請(qǐng)托,就在巡撫面前求情了。巡撫被說動(dòng)了,但面子也要保存,這才由幕僚顛倒了原布告的這句話,而成為“說書雖非正業(yè),接近衣冠”,而使評(píng)彈在蘇州再行開業(yè)了。
馬如飛是清同光年間的評(píng)彈名家。我記憶中聽說過有關(guān)他說書的一則軼事。一次,他演出《珍珠塔》,小姐上樓,有象聲詞“篤篤篤”表明一步一步上樓。要下樓了,也得“篤篤篤”下來。上樓有幾個(gè)“篤”,表明走了幾級(jí)樓梯,下樓也得有幾個(gè)“篤”,是一步也不能差的。老聽客聽得有幾個(gè)“篤”,記在心里了。否則,上樓走了十二步,有十二個(gè)“篤”,下樓多一個(gè)少一個(gè)都不行——這少出的一個(gè)樓梯到哪里去了?又會(huì)再造一層梯級(jí)?上樓馬如飛說了一段小姐心理活動(dòng)后,要下樓了,可把上樓時(shí)有幾個(gè)“篤”給忘了。老聽眾的挑剔可不得了,要影響聲譽(yù)的。急中生智,下樓時(shí),在幾個(gè)“篤”后,馬如飛讓小姐突然一滑,“哎呀”,然后再“篤篤”下來。這一滑,可能滑了一級(jí)或兩級(jí)樓梯,這就把“失誤”給掩飾過去了。
龔主任
龔主任并不是什么機(jī)關(guān)的主任,而是一家醫(yī)院的教授、主任醫(yī)師,習(xí)慣稱呼就是龔主任。
日前手上先后出現(xiàn)了幾個(gè)皮下出血的斑塊,過去也出現(xiàn)過,但這次卻是出現(xiàn)了好幾個(gè),什么原因?在我來說是“疑難雜癥”了,也為了女兒體檢報(bào)告單上有的驗(yàn)血指標(biāo)后箭頭或向上或向下,還有幾處檢查報(bào)告上寫有“隨訪”“定期復(fù)查”等字樣,怎么理解?體檢醫(yī)院是不會(huì)再有醫(yī)生給你解釋的。
怎么辦?決定去找龔主任釋疑。
在龔主任的辦公室外敲門之后,是他自己來開的門,他在電腦上看CT片子,是必須關(guān)了門,靜心、仔細(xì)審讀的。
我隨他走進(jìn)門去,走了有五六步吧,他讓我和我女兒在椅子上坐下。沒有等我開口,他就說了:你的腰椎間孔狹窄,才有這樣走路的步態(tài)。才走了五六步啊,他就作出了這樣的診斷。他建議我要少走路,而我以前總認(rèn)為腿腳無力是年紀(jì)大了的緣故,畢竟是86歲了,別人也勸我,要多走走路,不然腿腳更要退化,我也是如此想,每天還總想出去走個(gè)十幾二十分鐘的。經(jīng)他一指點(diǎn),以后可要注意少走路了。
請(qǐng)他看我手上的紅斑了。他說,這原因很多,或是食物引起,或是藥物引起,或是氣候變化引起,只能先觀察一段時(shí)間,看是否再大面積或多發(fā)性出現(xiàn)。到那時(shí),再去血液科檢查。龔主任又仔細(xì)看了我女兒的體檢報(bào)告書,對(duì)“隨訪”“定期檢查”等等作了解釋。
這已為我釋疑。但是,我總不能忘記,龔主任是曾解救過我危難的。那是2015年12月22日。在前一天,早上起床,突然發(fā)現(xiàn)左臂無法伸直,也無法舉起了。站著、坐著不太痛,就是無法躺下,躺下左臂關(guān)節(jié)處就劇烈疼痛,無奈,由我女兒陪去近在咫尺的一家三甲醫(yī)院診治了。醫(yī)生檢查了,說可能是肩周炎,按肩周炎給我開了藥。當(dāng)晚痛得無法躺下睡覺,是坐在床上過了一夜。第二天,22日,到另一家醫(yī)院神經(jīng)內(nèi)科打針。那是每六七天一定要打一針的。
我在神經(jīng)內(nèi)科打完針,走過龔主任的辦公室,陪我去打針的兒子說去看看龔主任吧。見到龔主任,我說了我的病情,他說,馬上住院!問住哪個(gè)科?答:神經(jīng)內(nèi)科。于是,兒子陪我又去神經(jīng)內(nèi)科,正好有床位,當(dāng)即辦了住院手續(xù)。經(jīng)過骨科等科的會(huì)診,確診為“臂叢”。住了8天院,對(duì)癥用藥,回家了。而這8天的前6天,我是每天坐著睡的;后兩天,才能半躺著睡。如不是龔主任的提醒,還不知道怎么熬過這一關(guān)呢!至今,我還是記著龔主任,也記著神經(jīng)內(nèi)科的溫主任、楚主任和護(hù)士長(zhǎng)、護(hù)士們,這次,是他們幫我渡過了難關(guān)。
又想起一件事。我?guī)н^的一名研究生小何的父親肺部不適,從徐州來蘇州準(zhǔn)備診治,帶來了8年前以及以后歷年在徐州醫(yī)院拍的所有CT片子。我陪小何去找龔主任,他看了片子,說從8年前拍的第一張CT片子來看,那時(shí)就可確定是肺癌了。在徐州醫(yī)院沒有看出來的病灶,他一下子就作出了結(jié)論。這就是水平!
近日,又去請(qǐng)教龔主任,為的是尿檢中出現(xiàn)蛋白尿,為3個(gè)+,那是腎損傷了。我的老同學(xué)林瑞章便是因腎衰竭去世的。龔主任建議我服用黃芪等中藥,囑咐了注意事項(xiàng)。作為CT室主任,要為患者全身作檢查,因而具備全科醫(yī)師的職能與技術(shù)。要交代一下,龔主任,大名建平。
宋云彬評(píng)張?jiān)屎统デ?/h2>
宋云彬(1897—1979),作為文史大家,他的學(xué)養(yǎng)不僅僅是文史方面的,他的圍棋技能,可以同高手決一高下;他的中醫(yī)醫(yī)術(shù),可以為人開方。他的昆曲演藝,可以合笛,與在昆曲表演上有相當(dāng)素養(yǎng)的張?jiān)屎偷瓤梢砸黄鹋那叱@在他現(xiàn)今留存于海寧市檔案館的日記(200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以《紅塵冷眼》為書名出版)中有記載。多才多藝,可以說是對(duì)那一代知識(shí)分子共同的評(píng)語。在宋云彬日記中還有葉圣陶唱昆曲的敘述。
1939年6月21日,農(nóng)歷五月初五,為端午節(jié),宋云彬時(shí)在桂林。生活書店備有粽子,舉行書店全體干事會(huì),邀請(qǐng)宋云彬列席。會(huì)后有余興,宋云彬“自告奮勇,歌昆曲《慘睹》一支”。由此可見,在那時(shí),宋云彬已習(xí)有昆曲,且可當(dāng)眾一曲了。1940年2月7日,為農(nóng)歷除夕,國(guó)新社邀請(qǐng)聚餐,開明書店也由漫畫家沈同衡等來邀,去吃年飯。宋云彬先赴“開明”,再應(yīng)國(guó)新社之邀赴新生菜館。餐后的聯(lián)歡會(huì)上,宋云彬扶醉“歌昆曲”,“醉態(tài)畢露”。那時(shí),國(guó)難當(dāng)頭,在困頓中,借此消愁吧。1949年3月2日,在由香港乘船北上途中,心情舒暢,以昆曲傳情,宋云彬與葉圣陶“合唱《天淡云閑》一段”。這心境,與拍曲《慘睹》,就有天壤之別了。而葉圣陶之善昆曲,在歷來介紹他的文章中所未之見。
1951年6月7日晚7時(shí),時(shí)在北京,張?jiān)屎汀⑼鯘h華來到宋寓,“唱昆曲,由沈盤生吹笛。”宋云彬唱了《牡丹亭·游園》。6月14日,張?jiān)屎秃退娜脧埑浜陀謥淼剿卧ⅲ瑥堅(jiān)屎偷摹扼@夢(mèng)》《番兒》,“甚可聽。”以宋云彬從不媚俗的為人與他對(duì)昆曲的欣賞水平,這“甚可聽”,是相當(dāng)高的評(píng)價(jià)了。王漢華唱《思凡》,宋云彬以昆曲的行家,有評(píng)論,“嗓音甚好,惜咬字未到家。”他自己一歌《游園》《驚變》,有自評(píng),“啞嘶不成聲,大可懊喪也。”這次昆曲雅集,王伯祥、王芝九、蔣仲仁、劉薰宇、計(jì)志中、盧芷芬、吳甲豐等“均來聽曲,頗熱鬧,九時(shí)半方散”。1951年11月30日,赴盧芷芬之宴,陸聯(lián)棠、周振甫、王伯祥夫婦、胡墨林(按,葉圣陶夫人)、劉薰宇、張?jiān)屎汀⑸虮P生均在座,餐后,沈盤生吹笛,宋云彬歌《游園》一折,“居然上笛,喉音甚亮。”一改前次嗓音的嘶啞,他也感到是“怪事”了。在那時(shí),作為一代知識(shí)分子,是有著相當(dāng)豐富的業(yè)余生活的。這反映出那時(shí)政治生活寬松,人們的心情輕松、愉悅。
作為文史大家,宋云彬?qū)デ械淖x音咬字是頗有研究的。1959年4月27日,在出席全國(guó)政協(xié)會(huì)議時(shí),會(huì)間休息,與一代昆曲名家韓世昌談昆曲,宋云彬問韓世昌《牡丹亭·驚夢(mèng)》一折“迤逗的彩云偏”之“迤逗”一向是否唱作“拖逗”?韓世昌笑著答復(fù):“從前趙子敬教我唱作‘拖逗’,吳瞿安教我唱作‘移逗’,我沒有法子,只好在趙先生面前唱‘拖逗’,在吳先生面前唱‘移逗’。”這引來宋云彬的打趣:“趙吳兩先生都在場(chǎng)的時(shí)候,你怎么唱呢?”韓世昌以大笑回應(yīng)。這在昆曲史上留下一段趣話。他以文史學(xué)家的功底,又以編輯朱起鳳《辭通》的學(xué)識(shí),告訴韓世昌說:“應(yīng)該唱‘拖逗’,此雙聲連綿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