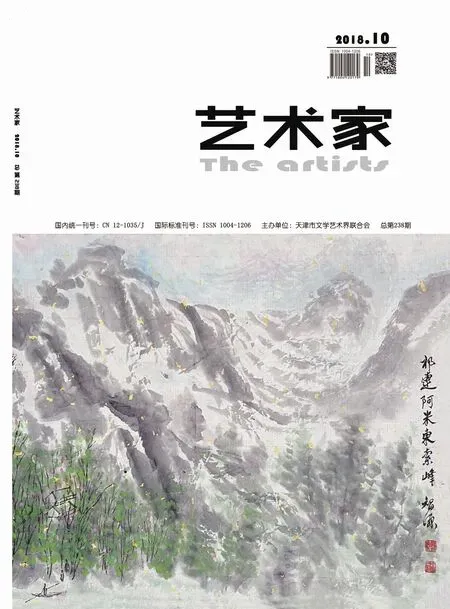深悟幻境 獨與道游—觀第七屆中國-東盟音樂周四川音樂學院“幻境”音樂劇場專場有感
□李光華 廣西藝術學院
2018年5月31日,四川音樂學院電子音樂與民族器樂“幻境”音樂劇場專場演出在廣西音樂學院主辦的中國-東盟音樂周如約而至。這場音樂盛會的精美呈現給筆者留下了精湛、新穎的映像,也給筆者帶來了美的享受。
一、音樂會簡介
本場音樂會是由以四川音樂學院民樂系青年教師為班底并吸納川內青年演奏家組成的成都現代室內樂團和四川音樂學院的電子音樂系共同打造的。樂團成立于2016年,這樣一支年輕的樂團有如此精湛的水平得益于眾多青年演奏家的加盟。據筆者所知本場音樂會的音響設備也是世界級的,為了本場音樂會專程將其從上海連夜運往南寧。本場音樂會在形式上十分新穎,將傳統民族器樂與現代的電子音樂相結合并將九個不同作曲家不同風格的九個作品串聯成一個整體。每個作品都有獨奏、重奏、合奏等多種不同的演奏形式,這種器樂劇場的演出形式在國內并不多見,卻十分吸引觀眾的眼球并受到一致好評。
二、構建“幻境”引人入勝
在筆者看來,本場音樂會最大的成功在于形式的新穎,這種新穎的形式來源于這場音樂會的“幻境”構建。音樂會在視聽上做文章,深層次地挖掘觀眾的視覺與聽覺感官,使觀眾能移情于境,融入音樂。整場音樂會在沒有舞臺燈光的情況下進行,在舞臺后面呈梯形擺放三面LED屏幕,會隨著音樂曲目不同變換不同的畫面。在舞臺上放置兩只重低音音箱,在觀眾席的兩側均等距放置六只音箱。曲與曲間用電子音樂連綴,曲與曲之間舞臺燈光不打開、演員不謝幕、觀眾不鼓掌,藝術家們換完場繼續演奏音樂。整場音樂會更像是一部劇場而整個音樂會的曲目之間卻并沒有內在的聯系,從而建立了他們所說的“音樂劇場”演出的概念。這一系列舞臺與表演的設計不斷地調整音樂表演者與觀眾的審美距離,使觀眾能夠迅速進入情境。
在本場音樂會中筆者最鐘情的是作曲家李琨創作并由青年打擊樂演奏家趙思智演繹的《玄響——民族打擊樂與八只音箱》,這首作品“以中國傳統哲學觀‘道’為創作緣起: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的本性就在于幽明之間,二者的交互構成了世界的總體特征。”這首作品用中國的民族樂器小鈸演奏,演奏者單用小鈸將音樂的強弱、音色的明暗、聲音的大小和節奏的快慢表現得淋漓盡致。更為玄妙的是小鈸的聲響通過電子設備的現場調試從音樂廳中的八只音箱中交替傳出,音箱中的聲響有的是演奏小鈸聲響的延續,有的猶如與小鈸聲響的輪唱,有的將音樂拉長扭曲……這一系列的電子音樂處理讓單調的打擊樂煥發了新的生機,聲聲玄響有時如蜜蜂振翅于耳邊、有時猶如幽谷遠處傳來的聲響。八只音箱與小鈸環繞于觀眾的四周,將觀眾放在音樂的中心,使觀眾的視聽變得更加立體,拉近了觀眾與音樂的距離,讓身處不同座次的觀眾都能夠獲得由這種立體的音源所產生的美感,讓聽眾醉心于這種幻境中。觀眾們不單單從舞臺上獲取聽覺上的享受,開始從音樂廳的四周捕捉音樂的余音。他們放棄一切雜念,只想單純地沉浸在音樂中去參悟玄響中的“道”。
三、傳統音樂傳承與發展的新方向
傳承與發展是所有文化繼承發展的難題,單純的傳承有可能造成陳舊的藝術形式與現代審美不相適應,單純的發展可能使得傳統的音樂在發展的過程中喪失傳統音樂的活力。傳承與發展的度的把握很難做到精準,但是四川音樂學院的這場電子音樂與民族室內樂的結合在這方面把握得十分到位。電子音樂手段的運用非但絲毫沒有破壞傳統音樂的美感,而且使民族樂器在音樂會中的表現力大大增強。在音樂會中,民族器樂古箏、琵琶因為電子音樂的傳輸,克服了民族樂器共鳴腔體小,無法發出大的聲音以適應現代大音樂廳的困難。
在民族音樂傳承與創作上,廣西本土音樂創作家莫軍生副教授的作品《花山印象》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首作品是為打擊樂、竹笛與電子音樂而作的,音樂中還使用了廣西獨有的樂器天琴。莫老師的作品中運用了很多中國傳統音樂的創作技法和廣西本土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本土的文化元素將筆者拉進了遠古的花山文化,筆者腦海中浮現出花山巖畫上的圖案;在作品中使用的打擊樂碰鈴敲擊后再手執繩索在空中搖晃,所產生的泛音聲波鳴于耳際,仿佛將筆者帶入遠古神秘的祭祀場景。莫老師根據本土音樂文化所創作的音樂作品是對這片土地的回饋,也是對講好廣西故事的一次完美嘗試。筆者認為這種從內容創作到表演形式上扎根民族音樂的演繹與闡釋無疑是中國傳統音樂傳承與發展的新方向。
本場音樂會不斷引起筆者對音樂審美的思考,也豐富了筆者對民族器樂的認知。中國-東盟音樂周不僅是中外音樂的平臺,更是中西文化的橋梁。四川音樂學院這場電子音樂與民族室內樂團“幻境”音樂劇場的專場演出受到外賓的一致好評,將中國音樂獨特的音樂文化和音樂語匯作一張文化軟實力名片傳遞給外賓,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