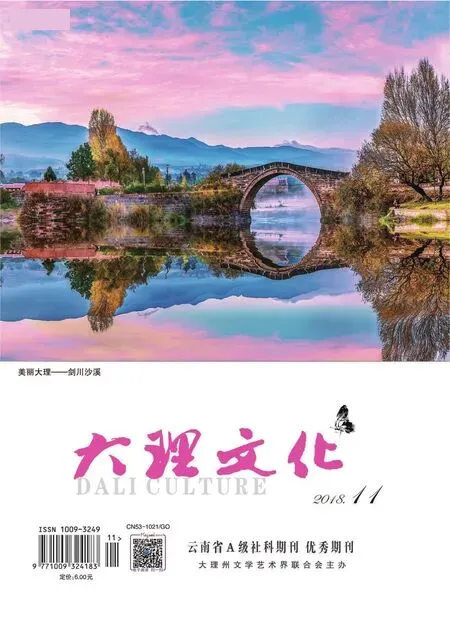泥土的奢華
—— 簡析《楊友泉小說精品選》
楊友泉是一位植根于農村泥土的小說家。他出生于祥云石壁村。石壁世代走老銀廠(緬甸),家家如此。進不了老銀廠,就進滇東、滇西、滇南、滇北,進西藏、青海、寧夏,賣土鍋。
穿草鞋,一擔擔挑著賣,大土鍋套小土鍋,小土鍋里套茶罐。“我的幾乎所有的小伙伴都是補鍋匠,鐵匠,銻匠,銀匠,金匠。”(楊友泉創作談)
楊友泉在序言中說:“這本書,就寫一個叫農民的人。……這個人,有時是個父親、農民工,有時是個寡婦、妓女,有時是個上門女婿,有時是個族長、補鍋匠,有時是個知天命的糟老頭……他們在各種艱險的環境里,拼命發長著,拼命向上著……他們的生命如同大地上的莊稼,一旦收割后,田野立即變得死寂,而在下一波生命來臨之前,我借著這稍縱即逝的寂靜,盡可能長地回顧一下他的音容笑貌,讓他卑微的生命盡可能長地在田野上空逗留、徘徊。”
植根于這片貧瘠的土地,他卻用自己的小說,彰顯了只屬于每一片卑微得讓人漠視的土地的奢華!
一、楊友泉的小說,是一種奢華的荒誕,這種荒誕來源于小說題旨的多重解構
在《松竹蘭梅圖》中,族長甘云松的女兒雪蘭遇害,引出棋盤村人的恐慌和對漢奸的甄別引發的種種離奇故事,而最終的結尾,卻是監視人甘紅梅家的所謂探子王國棟和族長在竹刑中“腸壁上的血水光華灼灼……讓它成為天地間獨一無二的主角。人們舉頭望時,就看到一顆拖著白尾巴的流星,從地上、從棋盤村村口、從竹叢里,劃過竹林,劃過滿天彩霞,箭一樣射向天穹。”這是一個民族封閉、愚昧的展現,也是那個時代人性善、丑的深刻揭示。
在《出師》中,補鍋匠楊培金忍受了饑荒年代的種種煎熬,終于出師了。可由于在喊到的第九千九百九十九口鍋中,有著雙方善意的作弊—一方求補鍋夠數,一方求女兒衣食——可是師道的規則又使他在出師后不得不違背雙方的盟約。他只能在一種極苦痛的自責中背棄了自己的誓言。“這個世界上唯一能把他從師門里逐出來的,現在,只有榛子……榛子會把砸鍋的事情說出去的……”所以,“只是一瞬,他就止了步。他不能帶她走了。”這既是補鍋匠的行業潛規則,更是一個道德的社會人遵從的信條;可這又不得不使他違背自己的承諾,辜負了一個善良的婦人彌留之際的托付和一個年幼的弱女子以生命為代價的期盼,使他不得安心!
《彈簧床》可能是謝莊那一代人永遠的記憶。“我”和謝龍為試坐龍城的彈簧床,開始引出了我們和謝支書、大雙、二雙在那個青澀年代的情感糾葛。愛情是美好的,可年輕的沖動,卻使得一切美好都脆弱得不堪一擊。最終,我們不是屈從于命運中那貧瘠生活的物欲壓迫,就是被自己那所謂的高貴的驕傲所折殺。青春逝去,我們之間,我們和那個年代之間,“我的掌心已經感覺不到他的熱度,冷颼颼的……因為我們中間,隔著厚厚的玻璃。”這里,流逝的,不僅僅是青春,感情,還有更深的失落。
在《疤痕》中,陳大勝額頭的刀疤,使他處處碰壁,無可奈何,就用磚刀修理了包工頭畢老板,卻得到了所有工友的支持。他等來了警察,卻是因為同住的小個子工友的盜竊而被關押。在與自己無關的事件中,卻因疤痕被重視;陰差陽錯地被證明自己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英雄,卻又在公安局長的“我看著這個疤痕就覺得邪乎,險些把一個好人弄漏了,以后工作要細心”的批示下入獄。他“只想過沒有疤痕的日子”,可是,這個疤痕,就只是額頭的疤痕嗎?
在《跟蹤》中,吳書鳳用大網把朱虎勒死,卻只有一個啼笑皆非的警告:“吳書鳳你不能喝酒,一喝酒就鼓弄漁網鐵錨,一鼓弄漁網鐵錨,捕魚逮獸的陷阱說下就下。這次你網了個歹人算你為鄉人除害,如果你網著良民你不也得搭上?”——意思就是,你弄死了人,警告你不許喝酒!——天大的笑話啊!
在《你得賠我田》中,楊德旺的拖拉機油倒成了茭瓜田的上好肥料,不知道科學家會怎么解釋?
無論族長甘云松還是刀疤陳大勝,無論是剁了小姐手腳的謝龍還是為自家的豬“花白”不遺余力的吳書鳳,故事都是荒誕的,不僅荒誕得真實,而且真實得超乎想象。對卑微地活著的“農民”,事情的真實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別人看到的表象。一切事物的發生、發展,似乎在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必然的結局,而這一切,都不是卑微的個體所能左右的。荒誕的不是故事,而是我們當下的存在。看似超越了現實的荒誕,卻是一種奢華的藝術。就是這種奢華,展現了作者的悲憫情懷。“作為一個作家,沒有悲憫情懷是成其不了真正的作家的。我們永遠要關注百姓的疾苦,只要還有人生活在不幸中,作家就有責任關注這種不幸。(楊友泉創作談)”我想,正是這種悲憫,使他植根于泥土,和近旁的蕪雜的生命同呼吸共成長,以超拔的大愛,隱忍人間!
二、楊友泉的小說,是一種奢華的色彩,這種色彩,來源于天地眾生在自己靈性的眼眸里的投影
在《惡之花》中,惡之“花”,不是小孩子的游戲,不是嬌艷的花朵,而是“翅膀上有兩只紅彤彤的大眼睛”的蝴蝶,“在陽光照射下,那紅彤彤的眼珠鮮艷得很,就像兩洞血。”與之關聯的,即是人性之花。“我”,保安,警察和殘疾的偷竊者及其妻子花兒、女兒翠和紅,就在一場殘酷的戰斗中展現了惡之“花”!是非對錯,人性的善惡,沒有輸贏,似乎誰都是殘缺的!
在《松竹蘭梅圖》中,雪蘭是高貴而純潔的:“她嫩生生地自豪,還很純真地箍在她剛剛發育的、靦腆的、緊繃著的筍一樣凸起的乳房上。她的背景還在不斷強化著這一切。她的背景是魂一樣細和輕的炊煙,炊煙后面是發呆的青山。青山高處……都是化不開的黏糊糊的黛,它們合力烘托、出賣著雪蘭。”就這樣的色彩,凸顯出一個美妙高貴的女子的圣潔,后來,“只看見雪蘭背后青得似乎要遁去的十九座山峰,以及雪蘭頭頂、左邊、右邊的釅得化不開的黛。黛,在一點點泯滅,凋敝。”悲劇由此誕生。
在《彈簧床》中,謝龍令人羨慕的朦朧愛情結束,“我”陰差陽錯地成為了大雙夜尿的守護者。“微風徐徐,月光把天地萬物繡成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附近高矮不一的松樹,卻像一把把柳葉刀,把半空中的月光齊刷刷割下,落在地上,形成了形狀不一的陰影。”這樣的光影里,“我們的青春就在這樣的混沌中掙扎著,困頓著,竊喜著,不聲不響地溜走了,什么也沒有留下。”
在《疤痕》中,陳大勝相親去了,“小路途經油菜花地,油菜花黃燦燦地把小路埋住了。走一段,小路被扯出一段;走一段,又被扯出一段。……過了一溜菜花地就見一個村莊隱隱約約伏在菜花間,繩子一樣的小路被腳步一截截逮出來。小路的一頭好像系在那個村莊的腰背上,就這么三逮兩不逮,村莊就在渺遠處拽了過來,而且越來越高大,越來越矚目。”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行走,要去天堂一樣美麗的村莊跟一個叫玉蘭的姑娘相親,陳大勝一家人的心情像金黃金黃的油菜花,又像細繩一樣的小路。這樣精美的景色和精美的心境,難道不是一種奢華的賜予?
環境描寫,場景交代,細節處理,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神來之筆。不僅僅是技藝的精湛,而是作者在嘔心瀝血地打磨著這個名叫“農民”的人啊!
三、楊友泉的小說,是一種奢華的唯美。這種唯美,是對人們內心最細膩的雕琢
就在楊天健(《煙壟邊上的人家》)澆煙水的早晨,“那霧長得毛茸茸的,鼻孔里馬上鼓脹了。”它“收集了溝里的青苔味、墑上的泥土味、田埂上的草青味、煙苗味、機耕路上的苦蒿味、水桶里的泥水味、湖面上的草腥味、男人的汗味——這天地間的味道,被太陽一口吸了進去,然后再慢慢吐出來,依舊把它放回這個壩子,這個壩子就平白多了一種醇厚。”這是一個唯美的早晨,也是一個唯美的季節,即將到來的耕耘后的豐收、生活的豐盈、戀愛嫁娶的期盼,就在這樣一個早晨展開。雖然后來有著保護神鳥白鶴的風波、有著澆水烤煙等現實的困挫,可生的希望,依然唯美。一個卑微的農民,“他覺得有一股力在腳底下運行著,他每挖下去一鋤,他就會被一種力推送進下一個波谷……”對,是波谷。可是,有白鶴的護佑,有愛情的祈愿,波谷之后,一定是重生的高峰!
寡婦水嫂(《寡婦磨》)和石磨之間,有著不可言傳的默契。諸多的石匠中,她只看中了銀生。“銀生是披著夕陽來的,像鍍了層金,從箐口一晃一晃,由一個金龜子那么大,變成了鳥那么大……水嫂就能認出來了。”“銀生在屋里晃蕩,安靜里還隱隱含著一點溫情。覆蓋在各種物體上的面灰,也慢慢退卻了那種漂白,增了種火焰藍。”在這里,高貴的景,似虛無的幻象,再自然而然滋長一絲恰到好處的風情,那種純粹的欲望,就至臻至美!所以,“銀生和水嫂都把對方當做填充物了……他們才覺得絕望不會再繼續蘇醒。”自然,美的極致中,靈與肉,混沌不堪而又激情飛揚!“天啊!水嫂在心里吶喊,這到底是最后一道防線,還是最初一道防線……”
當內心之美有如天地之純正,我們,即可遠離齷齪和污穢,無論是人,還是神!
四、楊友泉的小說,是一種奢華的靜謐。這種靜謐,既來源于內心靜觀萬象的超脫,又來源于對從紅土地中成長的民眾的諳熟
在他的小說中,沒有大是大非,沒有大奸大惡,沒有轟轟烈烈,沒有刀光劍影。他只是侃侃而談,把我們周圍的張三李四王五趙六牛七馬八的平凡遭際深情地縷析。“白豆烀臘豬腳”“草簾子”“雷楔子”“提籮”等等詞語,滇西北民眾不會陌生。這種從泥土中浸染而來的親切感,是他對這土地的深情回報。而每一個張弛有度的故事中,人們的每一句話的音言,每一個舉手投足的儀態,無一不是自然天成的本性。有時我不禁質疑,是不是那個鳳凰古城的大師突然言說起了滇西北往事與新傳?
我們都沒有故事,故事在民間。楊友泉的內心,充滿了最本真的悲憫。所以,他以一種民間的態勢,敘述著沒有故事的故事,而農民,就是我們這個即將蛻化的農耕國度中化石般的故事中的主角。
世事皆為美。唯能承天地之氣者,方為高尚。楊友泉是質樸的,隱藏于眾生的羽翼之中,用心靈之高潔與文字之拙樸,與夏夜的蟲唱蛙鳴一起彈奏屬于泥土的圣歌。
最卑微的心靈,才足以讓世人仰望。當浮華沉寂,楊友泉的小說,足以照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