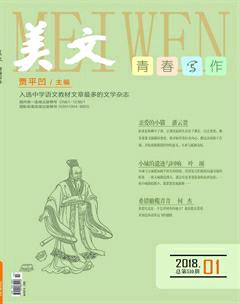智化寺里的守望者
賈沁蕾
我在雜亂無章的小胡同里尋到這座寺院。紅墻褪了色,像是洗過無數次的舊衣物,干巴巴的涂料凝固成薄片,彎出卷兒,懸在墻上,似乎輕輕一碰便會化成齏粉,消散在空氣中。起風了,我裹緊大衣,悄聲踱進這間院子。
今天,我采訪的是智化寺京音樂的第二十七代傳人——胡先生。在等待他的時間里,我漫無目的地覽著這里的一切,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審視。天氣陰涼,肥大的云團壓在寺頂,灰蒙蒙一片,未蒸發的積水淤在磚地上,載著簌簌辭柯的黃葉,從相異的角度看到相異的倒影——一邊是銀河SOHO,一邊是大智殿的高檐,風把倒影吹出皺褶,看不真切,我一時間竟分辨不出哪個才是這座城市的鏡像。
身后有人呼喊,我回過神來,才發現胡先生早已到了。
步入西廂房,也是他的辦公室,他草草收拾了零落的雜物,請我們坐下。空間本就不大,可用的板凳兩三把而已。我只得抱著書包站在一旁,不時動一動酸痛的腳。
一切就緒,采訪以稍輕松些的方式切入主題。我邊聽邊打量這個約莫三四十歲的男人。他衣冠樸素,眉眼間是與年齡不符的滄桑,沒一點我腦海中那種“國家級傳承人”的腔調和形象。我們聊京音樂的歷史,聊它的音樂性,聊它的情懷,卻終究不可避免地談及它的現狀。
胡先生指指窗臺上放置著的那幅裱起來的字——師父留給他的打油詩。“拙笙巧管波浪笛,難學易忘少人知,歷經五百二十載,二十七代得傳人。”他熟稔地背誦道。“我1991年12月4日到這座寺里來跟師父學習京音樂,中途從事過其他工作,等到2004年再回到這里,師父已經……”
長久的沉默,這個中年男人說至動情處落了淚,這樣激烈的情緒是我未曾料想到的。“他就一直等著我,1991年到2004年,整整十三年。”
“那您呢?您等到您的第二十八代傳人了嗎?”
又是沉默。片刻后,他緩緩開口:“還沒有,中途有幾個徒弟跟著我學,后來都走了。”
是的,這份工作正如同他的徒弟所講,“沒法養家”,就連身為傳承人的他,每月工資也不過兩千元而已。基本生活尚且沒有著落,談何傳承?談何推廣?
“‘申遺之后,國家給了兩萬的經費,”他補充道,“可是我還要收藏京音樂的樂器,你們看看上面那些云鑼,都是清代的,還有……”他一一列舉著,“都夠開博物館了。”“我以后就想開一間京音樂的博物館。”末了,他充滿希望地說道。
他有遠大的理想,想傳播京音樂文化,想開博物館。但是從他描述的現狀來看,理想遙遙無期。
等到一個傳承人,首先需要傳播京音樂文化,使它的所有魅力展現在公眾面前,才能吸引人,才能引導真正有興趣者深入研究學習,進而才會有人愿意兢兢業業地為京音樂奉獻一輩子。“然而事實卻是,我給老師們上課,希望他們學會后能教給學生們,可有些老師在聽課時睡覺。”胡先生無奈地說道。
“有沒有想過從主流媒體入手,把京音樂文化融入影視劇中?或者是通過公眾人物的影響力來宣傳京音樂?”
“我當然歡迎有這樣的合作機會啊!”
他用的是“歡迎”二字,為什么不是主動聯系呢?沒有渠道,所以只能守望。這就是殘酷的現實。他自認為走不通傳媒宣傳這條路,于是便從教育入手,認為這是最佳的對外宣傳方式,但將此要作為教學任務,強迫學生學習,我深知這種方式的不可操作性。
初三時,教科書上寫滿了“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什么樣的作文能得高分?寫中國傳統文化的。發下來的范文卷,一篇篇全是“茶道”“陶藝”“詩賦”“琴箏”,主旨無非都是傳承。我也跟風寫,寫“胡同”,寫“漢服”,無一例外得了高分,但我們真的深入研究過嗎?真的像寫出來的那般“癡迷”嗎?
和我們共同來到智化寺里的還有一群六七歲的稚童,他們聽了京音樂的表演,于是我特地采訪了他們。
“你喜歡聽嗎?”
“還行,就是有點兒刺耳。”這是委婉的表達。
“不喜歡。”這是我料想中的最不拐彎抹角的答案。
我又問他們:“你們知道剛剛聽的是什么嗎?”
搖頭,搖頭,搖頭。
我不忍心把這樣的現實轉達給胡先生。現實太殘酷了。
或許,胡先生能夠隱隱感覺到當中的無可奈何,但他不敢也不愿多想。
我轉身繞過一座座斑駁的大殿,向門口走去。太陽終是撥開了云層,天氣漸暖,那灘水終將慢慢蒸發。銀河SOHO的倒影不見了,大智殿高檐的倒影也不見了,這座寺院留不住它們,就像留不住我們一樣。
胡先生騎著單車,奔赴一場又一場教育宣傳,拐出寺門,消失在我的視野里。我仍是抱著最美好的希望和祝愿,愿這位智化寺里的守望者終有一天能夠等到自己的,也是京音樂的下一代傳承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