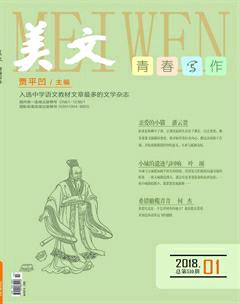浮生若夢
王倩
王 倩 任教于西安市鐵一中,所帶學生高考成績優秀。鄭州鐵路局骨干教師,西安市教學能手。2005年獲全國中語會“創新寫作教學與研究”課題成果展示會觀摩課一等獎;多篇論文獲全國、省市區級一等獎;參與編寫《唐詩鑒賞辭典》(中學版)、《“新課程”讀本》等書;參加國家“十五”“十一五”重點科研課題并獲獎。
情近中年,再讀豐子愷的《漸》,更覺心驚!

“在不知不覺之中,天真爛漫的孩子‘漸漸變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俠的青年‘漸漸變成冷酷的成人;血氣旺盛的成人‘漸漸變成頑固的老頭子。因為其變更是漸進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漸進,猶如從斜度極緩的長遠的山坡上走下來,使人不察其遞降的痕跡……”
年青時都夢想仗劍天涯,臨高山對大川,豪飲縱歌,仿佛這樣才不是“假裝在生活”。漸漸地竟覺得那不過是“灑狗血”的想象。胡適大師中年力求振作,他自言“偶有幾經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心境不無悲涼。凡俗如我,幾十年歲月飄忽而過,年少輕狂恍如舊夢,漸漸眷戀一啄一飲、一粥一飯里的溫暖,如若再有一點額外的奢望,也不過張可久筆下的“松花釀酒、春水煎茶”的清歡。
對半生游幕、落魄江湖的張可久而言,其中年心情大概如秋涼落葉,青蔥妍麗變成蕭疏荒冷,即使春風乍起,也吹不皺心中一池春水。皆言“春女思,秋士悲”,不遇之士也無法從容面對“姹紫嫣紅開遍”吧?春天再美,都是對他殘忍的提醒——你已漸老,春色已經與你無關。在他與春天有關的兩支 [人月圓]曲子里,我們可以讀到中年人的矛盾痛苦和由此而產生的感悟與生活選擇。在《春日次韻》里,我品味到一個被時光催逼,遭遇中年危機的男子不可排遣的愁苦;在《山中書事》里,我讀到他看破世情,繁華如夢后在山中覓得另一種清雅生活的恬淡安閑。這兩支曲子殊時殊地,趣味迥異,但它們之間卻有一種微妙的聯系。
春天,春天!多么柔艷旖旎的季節!張可久仕途失意,游宦無成,草木萌蘗、萬千芳菲的綺麗風物不過徒惹傷感。他該是在一個寂寥的日子里收到友人的一紙詩箋,輕薄的陽光透過窗紙,斜鋪在案上,案上羽毛般輕盈雪亮的箋上滿是春情春思,他既無事無聊,就按原韻寫一支和曲,于是就有了《春日次韻》。
這個春日,生葉催花的東風冷峭似箭,原應吹面不寒,此日這風卻有骨頭,硌得人生疼。身上羅衣輕暖,風來竟覺如未著衣。衣袂肅肅,像雛鳥奮力拍打翅膀,躲開風的侵襲。羅衫里,他單薄消瘦的身體也對著并不柔和綿軟的東風生出怯意。到底不再是少年了。當年青春正好,第一縷鵝黃染上高柳,第一簇蓓蕾綴上枝頭,他便雀躍不已,等不及風和日暖,便換上白色春衫,與友人相攜,于陌上去邂逅最鮮美的春天,那時,人生很淺,像一條小溪,一路歡歌。年歲大了,水流漸深漸靜默,游興慢慢消減,只愿意獨自安靜時想一點似乎可有可無的心事。
匆匆,太匆匆,楊柳枯復清,桃花謝再開,而人在塵世里消磨,在以為一切恒定如常的幻覺里,從生命的峰頂朝下走,抬頭時所見朗朗青天,已換作低頭看到的崎嶇小路、幽邃溝谷,流逝的并非時間,而是生命。偶爾臨鏡顧影,愕然發現綠鬢變作蒼發,在位卑職微,看不到出頭之日的境況下煎熬,只怕過不多久,“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古代文人雖沒有以色事人的女子“色衰而愛馳”的憂懼,但青春不再,心境自然灰頹。白居易在《漸老》一詩中也慨嘆:“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白發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歡趣。”無論唐時,還是元代,無論居高,還是處下,對生命原本懷有熱望的人,到了中年都會哀嘆華發早生,少年精神被塵事消磨殆盡。
華年已在身后,但作者還禁不住回望,那些不可復現的時光與做過的好夢也只能在春夢里將一個夜晚染綠。年既老,寢難安,漲如春潮的春夢片刻散去,只留“去似朝云無覓處”的惆悵。太邈遠的過去且不去想了,而近十年的漂泊生涯里,多少勞碌與困頓,多少無奈與辛酸,多少抑郁與不平,都只能任它們如浮塵般漸漸落定,沉淀在心底。用十年日子的愁苦,醞釀出微苦的詩,這也差可慰懷,但那一點詩愁終究成了心底的冰。
歲月不曾眷顧,何時何處不銷魂?春寒尚未褪盡,胭脂色的海棠看看已開過,枝上殘花伶仃可憐。暮雨瀟瀟,淋淋漓漓,淅淅瀝瀝,天地讓冷雨暈成深深淺淺的灰,如雪的梨花在灰色里倒是清麗可人,明人的眼目,只是朝夕寒雨冷風,很快只留雨打梨花、滿地碎瓊亂玉的凄涼蕭索。梁間沒有燕子溫存呢喃,勾起人無限悵恨,讓人想起燕子樓上的孤苦終了,想起蘇子的“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當下之張可久與往日之蘇軾皆為天涯倦客,見如此冷落清寂之景,也會同樣生出流年棄人、古今如夢、世事無常的浩嘆。
官場沉浮多年,總無法趕上大潮,立于潮頭之上。張可久的心靈極疲憊,何處可暫得憩息?文人們心里早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山中。那是想抖去一身塵世風塵的雅士們的“應許之地”。在山中,他們可以枕流漱石,可觀流云清溪,可與漁樵為友,更有“山花山鳥好弟兄”(辛棄疾《鷓鴣天》)。張可久也深感仕宦日久,光陰漸疏,對詩酒往還、縱情山水的山居生活產生深摯的眷戀。
從官場抽身離開,張可久并非沒有留戀與遺憾,但在他寫《山中書事》的時刻,他確實因“名不上瓊林殿,夢不到金谷園”([雙調·水仙子])而決心退隱,這不僅因為他意識到“春花秋月詩才,兩字功名困塵埃”([中呂·紅繡鞋])是他的命數,更因為他看到更龐大的歷史命運——“興亡千古繁華夢”。朝代更迭,正如春來春去,花開花落,此時繁麗滿眼,彼時卻如夢般散得杳無痕跡。張可久一雙慧眼穿透時光的層層障壁,終于確定盛衰無常,人生的得失榮辱也是一場場倏忽即逝的夢。他也曾游歷湘、鄂、皖、蘇、浙等地,也算走遍天涯,在荒煙蔓草間見過故冢殘碑,也曾吊古傷情。念及自己碌碌半生,卻只落得身處塵下,懷才不遇,他實在是倦了,厭倦了書劍飄零,厭倦了世態炎涼,厭倦了猜測上天何時會賜給他好運。endprint
他想起孔林高大的松柏,柏林森森,莊嚴肅穆。那個當年困于陳蔡“累累若喪家之犬”的孔子終能血食千年,香火不斷,但生前寂寞,身后的榮光也是虛妄。他想起吳王軒麗壯偉的宮殿,在極盛時也有“宮女如花滿春殿”的景況,但在幾百年前已是舊苑荒臺,草深木長,不勝悲涼,如今只怕見不到吉光片羽了。他想起楚王有地千里,南征開疆拓土,向中原問鼎之輕重,楚廟前也曾有巫覡歌舞,炫人耳目,而今安在哉?大概只有暮色中寒鴉萬點,徒增凄涼。
“微生盡戀人間樂”,張可久掙扎半生,更覺生命的微渺,要去尋一點身心靈皆放松的快樂。他迷戀的不是人間煙火,市井熱鬧,而是山中的詩意生活。我在《山中書事》的后半部分分明讀到文人畫的情趣意境,靜穆幽絕,又躍動著生命活力。與畫家們不同,張可久隱去了山水,直以心眼觀照樸素的生活,并以簡凈之筆將其呈于筆端:華屋大廈置于山中自是不倫,也與他的心性相抵牾,數間草屋可蔽風雨便好,正如淵明有“草屋八九間”,便可“審容膝之易安”。山中日月悠長,奔波時覺得促仄的光陰居然寬展有余,正好在萬卷藏書中神游,向古人先賢執經問道,或可砥礪切磋,欣欣然不知老之將至。原來閑下來的生活更豐富,也更輕盈。
很多年來,“山居”一直是我揮不去的念想,也曾在山野村居中暫住幾日,最終卻狼狽逃回空氣顏色很灰的都市。青山白云、秀林清泉、深谷險崖,自有隔絕紅塵擾攘的清幽雅韻,但無事可做、百無聊賴中勉強度日只會讓人覺得更寂寞。說到底,過于依賴社會化運轉而喪失了很多基本生活技能的我們,與古典的詩意真的是漸行漸遠。看看張可久的山中生活吧:山秀松茂,每至春初,便可采來松花花穗,揀、篩、曬后就可以得到滑潤微香的松花粉,市廛中人耐不得煩,山中無事,正好做這些磨人性子又頗有趣味的細事。以松花釀酒,“酒色淡黃清冽,酒味帶著淡淡幽幽的松花香味”,只一小口,似在松林間盤桓,清風吹襟,神魂染香。雨水后清明前,摘得幾籃茶的翠色新芽,趁著天晴風靜,慢慢焙好。日暖雪融,清溪里春水盈盈,茶葉制好,便可汲取溪中活水慢慢煎茶。燃起活火,等釜中水沸如魚目,“颼颼欲作松風鳴”(蘇軾),再沸時,涌泉連珠,三沸騰波鼓浪,投茶于釜,“松風入鼎更清新”(謝宗可),一甌春色,一懷春意,心中不平事盡向毛孔散,肌骨盡清。
詩書茶酒,如此簡單、簡樸,卻是多少人心向往之的理想生活。英雄夢斷,不再奢求聲名不朽,看破窮通無定,人情世態炎涼,生命真正進入“不惑”,認識到自我的有限性,只想著醉于芳樽、恬于自然,“石林高臥聽松聲”(《浣溪沙·感舊》),“青山勸酒,白云伴眠,明月催詩”(張養浩[中呂·普天樂]),恬淡自守,自娛自慰,正是戀戀清歡。
在異族入主中原,文人受到歧視和苛待的元代,仕路通達而成為達官顯貴者罕有,絕大部分文人或不問仕進,棄絕官場,或為微官小吏,在困頓中掙扎。張可久屬于后者。他深悲人生失路,深知富貴榮華如泡影,深曉功名不如閑中樂,但他“看得破,忍不過”,“贏了清閑,當了繁華”不過是激憤之詞,他直到懸車之年還求取昆山幕僚的職位,棲隱林泉是不得已而為之,“松花釀酒,春水煎茶”的閑適里藏著抑郁不平。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人終究敵不過時代,敵不過時間。張可久在無助與凄惶中依然保持生活的興趣,還有能力感知種種清心的歡愉。在風塵里追趕命運的我們,亦可以“不念八九,常思一二”,得一份安寧自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