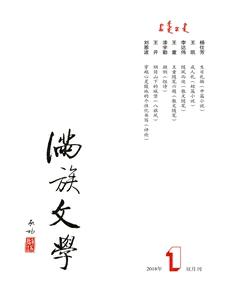煙筒山下的城堡
王開
以奴隸之名
在《戰(zhàn)績輿圖》中,阿哈伙洛城根本就沒有標注,這顯然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為六祖城的其他城址在其中都有說明。阿哈伙洛,現(xiàn)被簡化為“二伙洛”、“阿伙洛”,至于滿語讀音,想必也該有挺大變化的。因為史籍記載的疏漏,同樣也導(dǎo)致后人界定阿哈伙洛具體方位的困難,曾經(jīng),它被考證在興京城南的加哈河谷,但是根據(jù)《滿洲實錄》中的六祖城圖,它被畫在覺爾察城以西,呼蘭哈達以北的蘇子河南岸。上世紀90年代,地方史研究人員經(jīng)多次實地踏查,基本上確認了阿哈伙洛城所在。
阿哈伙洛城,在永陵鎮(zhèn)阿伙洛村南山一座面北的坡地上,平面呈橢圓形,具有東西長、西北窄,朝向蘇子河和西出三關(guān)的道路。據(jù)當(dāng)時考證,此城分上下二層臺,上層長約20米,寬約15米。東端筑一4米高的大圓臺,下層長約30米,寬約25米,邊緣筑有土木石墻。城的東南連山,北、西各以山崖為屏,城南隔一小山,城東300米又順山挖了一道大壕。實際上,在比這稍早的時間里,這座城的范圍更大一些。綜上所述,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阿哈伙洛城仍然是清晰可辨的,但是,隨后它就被新一輪的土地大開發(fā)所破壞,到了20世紀末期,阿哈伙洛城幾乎無跡可尋,只剩下天然的地理輪廓。
明代的阿哈伙洛城,居住著六祖之一的二祖劉闡。劉闡又譯作劉諂,約嘉靖元年(1522年)出生于佛阿拉城,少年時隨家遷居赫圖阿拉。劉闡這個人在史書中著墨不多,想必是身份等級不高,也沒有太突出的作為,因而記述較少。但他的居住地有一個獨特的標記:奴隸山溝。阿哈,在滿語中是奴隸的意思,伙洛,意為山溝。如此看來,劉闡當(dāng)時屬于奴隸主,管理著部落中的若干奴隸。極有可能,他的城堡里沒有多少自由民,而以奴隸為主。
女真社會進入奴隸制應(yīng)在明中葉,一般是家奴,但根據(jù)阿哈伙洛這個名稱來看,顯然劉闡管理的是一群為數(shù)眾多的奴隸,那么,這些奴隸是哪里來的?《朝鮮李朝實錄·燕山君日記》中說“野人之俗,不相為奴”,就是說,女真人有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相互間不為奴役,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阿哈伙洛的奴隸來自女真族群內(nèi)部,從而使我們把視線放到女真民族之外,即與建州比鄰的朝鮮和大明邊境。據(jù)朝鮮史料《朝鮮李朝實錄·燕山君日記》記載,“彼人得我國民一名,其價牛馬七八,又有的一人之價,牛、馬多達二十余頭”這說明,女真社會存在劫掠朝鮮邊民,使之淪為奴隸倒賣,而且根據(jù)搶劫來人的質(zhì)量高低論價,價低者可值七八頭牛馬,價高者則更加可觀。正因為這種高利潤,才使女真人愿意去鋌而走險。至于女真搶劫明邊的事情,史上更是屢見不鮮,他們除了搶劫財物,還搶劫人口。那這些人口也自然地就被倒手買賣,從中漁利。這兩種渠道,應(yīng)該也是建州女真獲得奴隸的主要來源。
但劉闡擁有這么多的奴隸,未必就是靠他個人力量獲取的。綜合六祖的情況來看,劉闡并沒有像索長阿那么聚富斂財不擇手段,也沒有覺昌安頭腦的靈活,心思縝密,他可能相對是個保守型性格,不善創(chuàng)業(yè)而善守業(yè),于是他被兄弟們推舉,負責(zé)管理整個建州左衛(wèi)的奴隸。否則的話,寧古塔六貝勒中實力較強的就不是覺昌安,也不是索長阿,而是劉闡了。
被建州女真圈在阿哈伙洛里的奴隸,首先要失去人身自由,然后是自己的姓氏,而同一叫做“阿哈”,嚴格來說,這只是個帶有屈辱性的稱謂而已。但隨著后金崛起,劉闡地位身份的提高,這些奴隸的地位也相應(yīng)有了變化。大清建立以后,他們的后裔被定位為“包衣旗人”,這個包衣,就是阿哈覺羅的演替,且其中不乏借著主人的權(quán)勢飛黃騰達者。而阿哈覺羅也以特殊的群體姓氏,成為滿族八大“穆昆”之一,載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劉闡的阿哈伙洛城堡,和其他五祖城的共同之處也是有的,那就是主要從事漁獵生產(chǎn),兼農(nóng)業(yè)種植。在阿哈伙洛城堡山下即是蘇子河,城背依煙筒山、鳳凰嶺,一年四季,捕魚、打獵、采摘,再運到撫順馬市販賣,換取生活用品。四周肥沃的土地開墾出來,種上黍、谷子等等,保證了糧食供應(yīng)。
劉闡這一支人不是十分興旺,他只有三個兒子,長子陸虎臣(也寫作祿胡臣)、次子瑪英格(也寫作麻寧格)、三子門圖(也寫作門土)。劉闡本人也受長兄德世庫影響,反對四弟覺昌安繼承祖業(yè),因此兄弟不睦,子孫輩也是矛盾叢生。比如努爾哈赤起兵以后,劉闡和索長阿、德世庫等常給努爾哈赤下腳絆,甚至搞暗殺等非常手段,要毀滅努爾哈赤。大約隆慶年間,劉闡去世。到了天聰九年,皇太極賜劉闡子孫為覺羅,系紅帶子。
三祖的領(lǐng)地
在《武皇帝實錄》中,河洛噶善又稱作河洛剛善。河洛也讀作伙洛,意為山溝;嘎善,意為村莊,河洛噶善,即山溝里的村莊。
河洛噶善城的考證頗為困難,可以說幾經(jīng)周折才認定的。首先,這座城很早就已經(jīng)不叫原來的滿語,然后是相關(guān)記載有誤,加上后期的考證者不通滿語,地理方位又不熟悉,導(dǎo)致錯上加錯。比如20世紀30年代時,日本人黑田源次、稻葉巖吉、高橋匡四郎等先后到新賓實地考察,還發(fā)表了不少論文,但據(jù)后來的當(dāng)?shù)匮芯空甙l(fā)現(xiàn),日本人所得的結(jié)果大多是錯誤的,而且錯的離譜。高橋匡四郎說永陵啟運山支脈一座小山崗是河洛噶善城,稻葉巖吉說煙筒山西面一塊突起地是河洛噶善城。建國后,我國學(xué)者劉選民又考證嘉哈河毗連的哈實瑪河谷地是河洛噶善城。直到20世紀九十年代,地方學(xué)者多次踏查、綜合分析,才認定了河洛噶善城遺址。
河洛噶善城是五祖福滿的第三子索長阿居住地,他的城距赫圖阿拉西北約18華里,離永陵鎮(zhèn)錯草溝北約10華里。頭道砬子?xùn)|南約2華里的腰堡東山,村里百姓稱那里為古城子。因為當(dāng)時女真人生活水平低,建筑技術(shù)更是落后,所以整座城以土木石為主,禁不起歲月風(fēng)塵的洗禮,如今只剩下南北長36米,東西寬42米的模糊輪廓。
現(xiàn)在看索長阿這個人,應(yīng)該是六祖中除覺昌安以外最具頭腦的。史籍記載,他很善于做生意,經(jīng)常率領(lǐng)手下諸申參加撫順馬市貿(mào)易,用人參、松籽、木耳、蜂蜜、馬、貂皮、鹿皮等,到馬市換取靴襪、鍋、碗、犁鏵等生活生產(chǎn)用品,再從中賺取差價牟利。但在那個時代,明王朝為限制女真民族發(fā)展,邊界貿(mào)易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允許參加的,一定要有明王朝特別頒發(fā)的通行證——敕書才行。因此,當(dāng)時各部落之間搶奪敕書的爭斗經(jīng)常發(fā)生。不過,索長阿喜歡聚集財富的方式也不止于正常貿(mào)易,有時候,他還采取非常手段斂財,甚至為此故意殺人,也得罪了臨近部落董鄂部。endprint
有一次,董鄂部酋長的兒子額爾機瓦給薩克達部酋長巴斯翰巴圖魯?shù)拿妹孟缕付Y,行到阿布達里崗,被托漠部的人殺掉,奪走聘禮。因為托漠部的人作案時,直呼其中一人“阿哈納”,被額爾機瓦的人聽到,逃回部落時就報告了董鄂部酋長克撒。克撒想,建州寧古塔貝勒寶實的兒子曾經(jīng)向巴斯翰妹妹求婚不成,是不是他們嫉妒生恨,害了我兒子呢?可是克撒沒有證據(jù),便高價懸賞捉拿殺害兒子的兇手。
這件事情傳到哈達部落酋長萬的耳朵里,哈達是大部落,萬本人強悍,一直有擴張地盤的心,他想借著這件事讓董鄂部降服于自己,于是,跟克撒說,殺你兒子的兇手我知道是誰,可以幫你殺了他復(fù)仇,但你以后要聽我指揮。克撒心知哈達萬酋長在落井下石,心中暗恨,他也不太信哈達萬酋長的話,認定這樁兇殺案是建州部所為。不過,克撒又想讓哈達萬與建州結(jié)怨,自己坐收漁利,就對哈達萬酋長說,如果你能抓到賊犯,必須讓我親自審問,事情確實如你所言,我加倍付你金帛。
信息傳到建州,索長阿動了心思,他想,既然董鄂部懷疑我們干的,一時也解釋不清,莫不如將計就計,還能拿到懸賞。索長阿就派人跟克撒說,你兒子是我手下的人殺的,你若把金帛給我,我就把他們殺了。克撒當(dāng)然不會輕易上當(dāng),心里琢磨著,哈達萬說他知道兇手是額吐阿祿部下所殺,你又說是你部下所殺,你們兩家還不都是為賞金而來,糊弄我嗎。這樣一來,克撒就惱恨哈達部和建州部,但他不敢惹哈達部,就把火朝著相對弱勢的建州發(fā),派兵攻打?qū)幑潘惱账鶎俚臇|南二路。此時,寧古塔六貝勒居住地分散,相互救援時間太長,兩家交手,建州部吃了大虧。
這次教訓(xùn),使寧古塔六貝勒醒悟過來,大家集會研究,兄弟六人的聚居地不能過于分散,大家要“聚居共相保守”,防止敵人來攻擊。但這個提議遭到索長阿次子武泰的反對,他認為,大家住的太近,放牧場不好辦。不如去向他岳父哈達萬酋長借兵,教訓(xùn)董鄂部,讓他們再不敢欺負建州。武泰的意見得到采納,哈達萬酋長也因上次的事情忌恨董鄂部,很痛快地答應(yīng)建州的請求,組成聯(lián)軍,攻打董鄂部。結(jié)果,董鄂部不敵,損失慘重。但是,戰(zhàn)勝的建州并沒有得到便宜,反而被哈達萬酋長獅子大開口,狠狠勒索一番,導(dǎo)致部落元氣大傷。
嘉靖末年,建州右衛(wèi)都指揮王杲日強,控制了通往清河、撫順馬市的交通要道,此時,索長阿和四弟覺昌安隸屬于王杲,聽從調(diào)度。王杲是個強悍的人,仗著部落強大,常干些犯邊搶劫,入馬市索賞的事情。作為屬下的索長阿,自然也跟著王杲興風(fēng)作浪,成為他的左右手,因此,大明邊關(guān)官員稱之為“建州賊首”。其實以索長阿的精明,唯恐朝廷懲罰他,就背地偷偷給邊關(guān)進貢,表示悔過。這件事情,記錄在《東夷悔過人貢疏》中。到萬歷三年(1575),王杲被明王朝處以極刑,建州立時陷入群龍無首的危險境地。寧古塔六貝勒又商議,依靠誰能繼續(xù)生存下去,索長阿提出,董鄂部強大,不如就近依附。覺昌安卻很冷靜,提出了一個更可行的建議,就是依附明王朝。
努爾哈赤起兵初期,引來很多仇家,想要殺死他。家族內(nèi)部也因此分為兩派,一派是支持努爾哈赤的,一派是反對努爾哈赤的,反對派中態(tài)度最激烈的,就是索長阿的四子龍敦。龍敦聯(lián)合長祖德世庫、次祖劉闡、三祖索長阿、六祖寶實之子孫“對神立誓,亦欲殺太祖(努爾哈赤)以歸之” (《清太宗武皇帝實錄》卷1,頁4)。這里的歸字,當(dāng)為歸順圖倫城主尼堪外蘭。當(dāng)時,尼堪外蘭受到大明邊官扶持,風(fēng)頭正勁,大有一統(tǒng)建州的氣勢。
但是努爾哈赤卻不這么看,在他的復(fù)仇計劃中,尼堪外蘭是一定要鏟除的。萬歷十一年(1583)夏天,努爾哈赤聯(lián)合納林部落準備攻打尼堪外蘭,龍敦知道后,唆使納林部落酋長諾密納的弟弟破壞盟約,結(jié)果,到了發(fā)兵之際,納林部落違約。萬歷十二年(1584)初,龍敦唆使努爾哈赤的異母弟弟薩木占率人截殺了努爾哈赤的妹夫噶哈善,引起努爾哈赤的極端憤怒。之后,又策劃了一系列暗殺努爾哈赤的陰謀,但是努爾哈赤命中注定有驚無險,龍敦的陰謀屢屢落空。不甘心的龍敦兄弟又生詭計,不久,龍敦的兩個哥哥綽氣朱阿古和履泰勾結(jié)哈達部,搶劫了努爾哈赤所屬的瑚濟寨,然后跑得無影無蹤。這一次,努爾哈赤忍無可忍,發(fā)兵討伐龍敦長兄履泰的兆嘉城。龍敦得到消息,事先派人報告,讓哥哥早有防備,即使這樣,履泰仍敗在努爾哈赤手下。但因履泰是努爾哈赤長輩,雖失去城主身份,卻受到厚待。
索長阿的兒子們每每與努爾哈赤作對,但他家族的后代卻對努爾哈赤忠心耿耿,跟隨努爾哈赤沖鋒陷陣,被努爾哈赤授以象征家族榮譽的紅帶子。
索長阿本人大約于萬歷十二年(1584)去世,葬于永陵。順治十一年(1654),擴建永陵時,鑒于他家族的數(shù)次背叛,其墳?zāi)贡蝗υ趯毘侵狻K熬幼〉暮勇甯辽瞥且驗樵诤請D阿拉城西,人們就稱之為覺羅西屯墓。
赫圖阿拉千曲水
努爾哈赤苦心經(jīng)營佛阿拉十六年,傾注了很大精力,也耗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但最終他放棄了這座城堡,走向祖居地赫圖阿拉。努爾哈赤整體遷移到赫圖阿拉的原因有多種,但主要的還是佛阿拉地理空間狹窄,盛不下他日益膨脹的心,再有就是佛阿拉無法提供充足的水源,迫使他一進入枯水季,不得不每天派專人下山取水,浪費了人力資源,也不利于生活。于是,努爾哈赤動了回歸祖地的念頭。
赫圖阿拉在滿語中是“橫崗”的意思,現(xiàn)實中,它也的確如此:一座高大的土臺,四周寬闊,視線不受阻礙,河流蜿蜒,交通暢達。對于步入發(fā)展階段的努爾哈赤而言,這是再理想不過的定居場所,前后左右,進退自如,即可做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載體,又能擔(dān)負起練兵、商貿(mào)等重任。此外,赫圖阿拉也是努爾哈赤的感情歸屬地,這座土崗沉淀著太多的記憶,使他難以忘懷。
赫圖阿拉最早出現(xiàn)大約于明正統(tǒng)五年(1440),當(dāng)時的女真社會外受朝鮮、韃靼欺負,內(nèi)部缺少領(lǐng)軍人物而四分五裂,更有董山及其叔叔凡察率領(lǐng)的建州左衛(wèi)在斡木河艱難度日,不得不向朝廷提出申請,要投奔居于呼蘭哈達山下的李滿住。這個申請獲批后,董山與凡察便率部進入李滿住的居住區(qū)。當(dāng)時,李滿住居于佛阿拉城,董山與凡察就在附近建設(shè)了赫圖阿拉城定居。董山這一支人枝葉繁茂,到了福滿這一代,又有六個兒子,這六個兒子成年后,覺昌安得以繼承家業(yè),仍住赫圖阿拉城,其余兄弟五人就圍繞赫圖阿拉城各建城堡。endprint
努爾哈赤在祖先的基礎(chǔ)上擴建赫圖阿拉,他修建了內(nèi)城和外城。內(nèi)城從1601年開始興建,幾乎動用了國中的全部力量,遷入內(nèi)城后,才又騰出手建外城。顧名思義,赫圖阿拉的內(nèi)城住著努爾哈赤本人及兒子大臣們,外城住著他的精兵強將。據(jù)史籍記載,赫圖阿拉一共分十三門,其中北門屬于鐵匠的居住區(qū),這些人專門負責(zé)制造鎧甲武器,南門外則專門負責(zé)制造弓箭。農(nóng)業(yè)和養(yǎng)殖業(yè)也隨之發(fā)生較大進步,到了1616年前后,努爾哈赤開始下令飼養(yǎng)家蠶,種植棉花。內(nèi)城南門里也開辟成商業(yè)大街,燒鍋、油坊、肉鋪、皮革店、當(dāng)鋪等排列成行,熙熙攘攘。
女真民族信奉天地神靈,到了努爾哈赤時代,更加注重宗教在人心中的力量,他在赫圖阿拉先后修建了地藏寺、顯佑宮,薩滿神殿等,方便屬下不同民族出身的將士和人民到那里祭祀,他本人更是每次出征前親自舉行隆重儀式,祭拜天地諸神,保佑旗開得勝,凱旋歸來。東城門外還有囤積糧草的地方,據(jù)說有房舍八十多間,努爾哈赤尤其重視糧草工作,任命十六位大臣和八個巴克什專門管理。
努爾哈赤修筑完善了赫圖阿拉城,為稱汗做好了基礎(chǔ)準備,萬歷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爾哈赤在此舉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建立后金政權(quán),建元天命。關(guān)于努爾哈赤登基的細節(jié),《太祖武皇帝實錄》做了記載:“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及八旗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眾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進表章,近侍衛(wèi)阿敦、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額爾德尼跪上千,宣讀表文,尊上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貝勒諸臣,行三跪九叩首禮。上復(fù)升御座,眾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慶賀禮。建元天命,以是年為天命元年”。努爾哈赤在大典上焚香告天,指的就是廣受后人傳播的“七大恨”,這等于一篇戰(zhàn)斗檄文,向族人發(fā)出作戰(zhàn)的號令,向明王朝下了挑戰(zhàn)書。從此,赫圖阿拉隨著努爾哈赤的后金國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成為一個民族自強奮斗的象征。
努爾哈赤稱汗之后,馬上展開了疾風(fēng)驟雨似的攻勢。他先是周密籌劃,計攻撫順,數(shù)天時間掠走人畜財物三十多萬,極大地震驚了明王朝。然而,大明君臣還沒緩過勁兒來,努爾哈赤又席卷清河,接著攻陷開原、鐵嶺、沈陽,一連串的旋風(fēng)式攻擊令大明王朝慌了手腳,不得不坐下來,認真商討對策,最后決定派兵剿滅努爾哈赤。但是這個計劃因兵力集結(jié)和軍需物資的調(diào)配問題一直拖延,直到1619年才算有了眉目,進剿大軍開拔遼東,意圖合圍赫圖阿拉。努爾哈赤這一邊,早已制定好應(yīng)敵對策,他絕不能讓敵人堵在家門口作戰(zhàn),而是主動將隊伍拉出去,采取各個擊破的方式,一口氣吃掉了明王朝的三路大軍,僅有李如柏望風(fēng)而逃。這一仗,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大戰(zhàn)”。正是有了這一仗,轉(zhuǎn)變了后金與明王朝的戰(zhàn)略關(guān)系,增強了努爾哈赤向遼河平原進軍的信心。戰(zhàn)后,努爾哈赤很快將國都搬遷到界藩城,這一決定,意味著女真民族由森林走向平原的進步,是他們追求文明富裕的勇氣。
天命六年(1621),努爾哈赤率八旗軍攻陷沈陽、遼陽,以及遼河以東大小城堡七十余座,為了在遼沈地區(qū)站穩(wěn)腳跟,他又下令修遼陽城,名曰東京。但是,他很快又發(fā)現(xiàn),沈陽的綜合優(yōu)勢遠遠大于遼陽,又不顧眾人反對,修建了盛京城。
赫圖阿拉作為清王朝的發(fā)祥地,女真民族奮發(fā)圖強的精神圣地,深受歷代清帝尊崇。皇太極繼位后,于天聰七年(1633)在赫圖阿拉設(shè)立滿、蒙、漢駐額兵,轉(zhuǎn)年又尊為“天眷興京”,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情。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皇帝升興京城總管為“理事通判廳”。到光緒三年(1877)清政府盡管已走向窮途,仍然升格赫圖阿拉的行政級別,改理事通判為興京撫民同知,并將辦公地址移至新賓鎮(zhèn),興京城守尉改為興京協(xié)領(lǐng),仍駐扎赫圖阿拉城,保護著它。
赫圖阿拉以它特有的神韻與氣質(zhì),贏得了清帝的敬仰,也成為他們屢屢歌頌的對象,在清史上,每位回鄉(xiāng)祭祖的皇帝都為它寫下詩篇,紀念祖先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表達自己不辜負祖先的決心。清帝返鄉(xiāng)祭祖的人,首開先河的當(dāng)屬康熙,現(xiàn)在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寫赫圖阿拉的詩,就是他在第二次東巡時所寫:
靄靄興王地,風(fēng)云莫可攀。
縈洄千曲水,盤疊百重山。
瞻拜園陵肅,凝思大業(yè)艱。
蔥蘢松柏茂,瑞鳥滿林間。
從康熙這首詩中可以看到,他回到祖先奮斗之地,滿懷的虔誠,字里行間也透露出當(dāng)時赫圖阿拉的景色,松柏繁茂,群鳥飛翔,綠水潺潺。身處這樣的地方,少年得志的康熙怎能不豪情萬丈呢!
乾隆是清帝中返鄉(xiāng)祭祖次數(shù)最多的人,他平生兩大愛好,一是寫詩,二是瓷器,可以說,他的東巡,是一路走,一路詩,這些詩不一定都是頂級的,卻是考證沿途建筑、風(fēng)俗、人情等情況的珍貴資料。乾隆第一次東巡就寫下兩首興京詩,其中一首《興京疊五言十韻》詳細回顧了薩爾滸戰(zhàn)役的情景,贊嘆祖宗奠定千秋基業(yè)的智慧和勇敢。第二首詩《興京》既有故國父老深情的感動,也有自己初來的急切和不愿離去的依戀,同時還有告誡后人的叮囑:
姬室于豳日,炎劉起沛時。
一人方締造,四海遂為基。
皇澗猶然在,皋門尚可思。
屏藩堪示固,宮室不言卑。
往者爭雄際,同歸出眾姿。
秋風(fēng)經(jīng)故國,膏雨遍新陂。
父老迎鑾輿,村官衛(wèi)羽旗。
初來尤切切,欲去更遲遲。
言念皇圖纘,端維厚德垂。
凜乎同馭朽,告戒后人知。
乾隆第二次東巡,寫下的興京詩更多,內(nèi)容涉及也更廣泛,他的隨行大臣們也紛紛賦詩和韻,以示對興王之地的崇拜。這些詩中,有寫顯佑宮的,有寫永陵的,有直接寫興京的,寫赫圖阿拉的等等。到嘉慶和道光兩朝,兩位皇帝也是極盡所能,贊美祖先發(fā)跡之地,大臣們也是一起附和,表達敬仰和忠心,而且他們和乾隆一樣,似乎對顯佑宮情有獨鐘,如乾隆第四次回鄉(xiāng)時寫下一首《謁顯佑宮》:endprint
顯佑為天佑,亦由人合天。
設(shè)無開創(chuàng)德,莫作覬覦先。
絳節(jié)朝群宿,金蓉侍列仙。
瓣香泯別祝,綏履福農(nóng)田。
嘉慶的《謁顯佑宮》寫道:
祖德合天心,于昭寶命臨。
興京初肇祀,上帝永居歆。
致敬抒虔祝,升香達寸枕。
承天守大業(yè),兢惕懔難諶。
總之,不管是清帝,還是清帝的隨行大臣,都將赫圖阿拉作為圣地來朝拜的,赫圖阿拉的歷史地位,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它在清史乃至中國史的研究工作中,是不可繞過和忽略的。
桑樹已成往事
在滿語中,尼瑪蘭是桑樹的意思。顧名思義,那里曾經(jīng)長滿桑樹,由此可以想見,這片土地是多么的肥沃,動植物多么繁茂,才吸引來六祖之一的包郎阿安家落戶。《盛京通志》中,如下記載尼瑪蘭城:“在興京城東北三十五里,與章京河俱出納魯窩集西流,于興京門之北入蘇子河。”《大清一統(tǒng)輿圖》中,又這樣描述尼瑪蘭城:“蘇克素滸河支流,加里庫與張陰河之間有尼瑪蘭河在興京之東北。”這里所說的尼瑪蘭河,指的是今永陵鎮(zhèn)錯草溝的錯草河,它發(fā)源于興京城東北的山脈中,距蘇子河三十五里,溝口距赫圖阿拉3華里。
尼瑪蘭城的具體位置在永陵鎮(zhèn)嘉禾頭道堡村,村邊的小河岸有兩座城,緊挨著錯草河的是山城,建在河西的小山頂上。另一座是平地城,上世紀90年代,尚可見城的走向,四周筑有土石墻,墻外有三面2米寬的壕溝,說明當(dāng)時城主人很重視防衛(wèi)。城內(nèi)的建筑遺跡,直到上世紀末期仍依稀可辨,只是因為被圈在百姓家的菜地里,大多夷為平地。百姓家也是滿族,在此居住有七八十年的時間,據(jù)他家人回憶,尼瑪蘭城為圓形,占地70平米方圓,以前還能撿到一些青花碎片。
歷史上,包郎阿本人應(yīng)該是六祖中最本分老實的,他既不像覺昌安那樣擅長謀劃,又不愛像索長阿那樣出風(fēng)頭招災(zāi)惹禍,他安心于耕種漁獵,過著自給自足的平民生活,這可能是他的現(xiàn)實追求。包郎阿因為少作為,史籍對他著墨不多,但根據(jù)尼瑪蘭城的城名及四周情況,可以推斷出,包郎阿當(dāng)時開墾了不少土地,種植谷黍,保證糧食供給。當(dāng)然,捕魚和狩獵也是他的主要活動內(nèi)容,明中葉以后,遼東地區(qū)的捕魚工具已相當(dāng)豐富,人們發(fā)明了各種魚叉、漁網(wǎng)并大量使用。從尼瑪蘭城出土的箭鏃刀矛分析,包郎阿也是喜愛狩獵的人,而城外的高山恰好為他提供了廣袤的狩獵場所,他可以不費什么力氣,就能捕獲到虎、豹、熊、獐、鹿和狍子等大型野生動物,野雞野兔河貂水獺青鼠之類的更是不在話下。在當(dāng)時社會,人參和貂皮就已經(jīng)價格昂貴,女真人正是靠著這天然的物產(chǎn)或進貢明王朝博取皇帝歡心,或用來到馬市交換所需商品。同時,也因為交換過程中的不公平,與明邊軍發(fā)生摩擦與矛盾。包郎阿也無一例外的遵循了用物產(chǎn)交換必需品的生活模式,但前面講過,他是個地位不顯,沒什么雄心的人,他可能都沒有敕書,只是采獵回來立即就賣掉了。這個說法,當(dāng)然沒有直接證據(jù),不過可以從其他方面反饋出來。
在現(xiàn)存的清史資料中,沒有一條包郎阿及其部落到遼東漢人區(qū)或朝鮮邊境搶劫的記載,說明他不具備雄厚的經(jīng)濟和武力的實力,換句話說,日子過得窘迫。但他的忠厚性格,使得與四兄覺昌安關(guān)系融洽,這種良好的家族關(guān)系一直維持到兄弟倆的子孫輩。兄弟倆之所以比其他兄弟格外走近,或許是多受覺昌安的照顧,畢竟,覺昌安繼承祖業(yè),又頭腦精明,生活上比弟弟富裕的多。一個相當(dāng)明顯的事實是,努爾哈赤起兵以后,大祖、次祖、三祖及六祖家族害怕他連累自己,就到寺廟里發(fā)誓,要聯(lián)合鏟除努爾哈赤。這次陰謀中,唯有五祖包郎阿家族沒有一個人參與。努爾哈赤起兵后,與他堅定地站在一起的,仍然是包郎阿家族的人,他們不顧性命,隨努爾哈赤東征西討。1586年正月,努爾哈赤三祖父的兒子龍敦唆使人謀殺了努爾哈赤的妹夫噶哈善,努爾哈赤悲憤異常,一定要去尋找尸體,這時候,又是包郎阿家族的人站出來勸告,他就是包郎阿的次子巴孫巴圖魯,他攔住怒火沖天的努爾哈赤,說,你不能去!那些人本來就是想殺你的,你這一去,不等于自投羅網(wǎng)嗎?巴孫巴圖魯?shù)囊环挘古瑺柟嗝托眩苊饬艘淮螣o謂的犧牲。
包郎阿育有四個兒子,長子隋痕,次子巴孫巴圖魯,三子對秦,四子郎騰。在他的子孫后代中,功勛卓著者有曾孫拜三,拜三長子顧納岱、顧納岱的兒子莫洛宏。
包郎阿本人約卒于萬歷十年(1582)左右,他先葬于煙筒山和蘇子河北岸的山下永陵。順治十一年(1654年),清王朝擴建永陵,他的墳?zāi)贡蝗υ趯毘侵獾臇|北角。這個做法,后世角度看,有些失禮,淡化了包郎阿家族當(dāng)年隨太祖出生入死的并肩戰(zhàn)斗之情。天聰九年(1635)正月,即將登基稱帝的皇太極為鞏固政權(quán),正式將女真民族定名滿洲族,從此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誕生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同時,他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會發(fā)展的政令,重新冊封了皇室成員的稱號,在這次冊封中,包郎阿家族的人被稱為覺羅,系紅帶子,其后裔載入覺羅族譜。
珠子山的舊主
在新賓滿族自治縣網(wǎng)戶村西南,有一座小山包,猶如一顆珠子鑲嵌在驛馬河與蘇子河交匯處,其山西北有南砬嘴山,東南有鷹嘴砬子山,遠遠望去,兩山好似龍頭,正對著珠子山,當(dāng)?shù)匕傩招蜗蟮胤Q之為二龍戲珠。
珠子山距網(wǎng)戶村東北的北砬背山很近,兩者遙遙相對,好像有著說不盡的心事。事實上,珠子山和北砬背山確實淵源很深,明代,它們承載了建州女真風(fēng)起云涌的往事,象征著親人間的仇怨。
當(dāng)年,建州左衛(wèi)都督福滿共有六個兒子,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后金,他們被統(tǒng)稱為“六祖”,其中,寶實是福滿的小兒子,按年歲排序,就是六祖了。寶實,在清史中又寫作寶石、豹石。大約生于明嘉靖五年(1526)的佛阿拉城。寶實出生的年代,也是建州女真比較弱勢的年代,他們的父親福滿還沒有相對顯赫的地位,一家人和部族一起,在山城佛阿拉過著貧困的生活。寶實成年后,父親福滿已經(jīng)升任建州左衛(wèi)都督,家中境遇發(fā)生很大變化,但比之臨近的董鄂部、渾河部等等,實力仍然處于下風(fēng)。雖然實力不足,建州左衛(wèi)范圍內(nèi)還是說了算的,于是,小兒子寶實結(jié)婚成家時,福滿給小兒子劃了一塊地盤,許他到那里建城堡居住,這就是珠子山,城,叫章嘉城,也寫作章甲城。endprint
寶實身為章甲城的城主,亦稱酋長,實際按現(xiàn)在眼光來看,頂多也不過是族長或村長罷了,而且管理的人數(shù)也不多,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女真族的人口也才區(qū)區(qū)幾萬人。章嘉城,應(yīng)該是托章京河之名而起。章京是清代的官名,早期為武官的稱呼,后來取消限制,應(yīng)用到文官中,如軍機章京、總辦章京、幫辦章京、額外章京,還有派駐新疆、蒙古等地的官員,也有章京一級的官員。鑒于此,明代的建州女真部不可能存在“章京”這一朝廷的高級別官員。但也有人提出,章京河,應(yīng)該也不是原來的河名,能給這一提法做出證明的,是《盛京通志》的一段話:“章京河,國語章京官員也。城東北三十五里,源出納魯窩集,流入蘇子河,亦作阿津”。阿津,滿語是鰭蝗魚的意思,這說明,阿津河曾經(jīng)水流豐沛,游動著成群的鰭鰉魚,岸邊生長著茂盛的水草,景色十分優(yōu)美。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福滿對小兒子的偏愛有加了。因此,引申出章京河就是阿津轉(zhuǎn)音的提法,不過由于年代的久遠,究竟兩個詞的原始發(fā)音是否接近,還是有待考證的。
關(guān)于章嘉城的確認,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當(dāng)時的地方史研究人員根據(jù)《戰(zhàn)績輿圖》記載的“興京城東北有章嘉城,在章京河畔。”和《盛京通志》記載的:“章京河在興京城東北三十二里”,及《滿洲實錄》中關(guān)于六祖城的描述:“在興京東北,蘇子河北岸,距蘇子河曲折處不遠的山谷之口“,經(jīng)實地考察,認定今網(wǎng)戶河就是章京河。網(wǎng)戶河入蘇子河口西北約300米處的腰嶺子?xùn)|端的珠子山就是寶實的領(lǐng)地章嘉城。
珠子山下現(xiàn)有一村屯曰西石場,北鄰網(wǎng)戶村,山西北坡有一磚瓦廠,村北是老砬背山,南距蘇子河約250米,章京河就是由城東的陡崖下流入蘇子河,城西南距赫圖阿拉城約3.5公里。山上是一座平面方形的小山寨,東、北、南三面陡峭,難以攀緣,惟西面是東西走向的漫崗,有利于行走運輸。城內(nèi),東西殘存約50米,南北寬30米,東北角是城門,沿城門向西,地勢漸低,因而修了一條長20米,寬2米的門道,通向山下。由于珠子山早已被當(dāng)?shù)匕傩臻_墾,只能分辨出上述一些痕跡,不過,遺憾中也有令人難忘的,那就是城外至城內(nèi)尚存一條引水渠。女真人喜歡住在高處,利于防衛(wèi),但高處的一個實際問題就是飲水,所以,北砬背山上的房基遺址到底是誰居住,還不太好確定,畢竟,在北砬背山上是找不到水源的,也沒有引水工程的痕跡。
章嘉城和其他五祖城及北砬背山城一樣,均為土木石結(jié)構(gòu),這種建筑格局一出于森林民族的建筑水平低下,二受制于經(jīng)濟水平的落后,城內(nèi)遺存的明青花瓷片也說明了這一點。寶實雖然得父親偏疼,占有較為優(yōu)勢的一塊地,但一大家子依靠漁獵采集,墾殖土地,所得收入仍微乎其微,擺脫不了大環(huán)境下所致的窘迫,他家也因貧困娶不到媳婦的事情記入史籍。
建州左衛(wèi)早期,雖然福滿生了六個狼虎弟兄,可他們還是一幫子窮哥們,不被鄰居部落所看重,甚至有時遭受羞辱。寶實年長后,他的二兒子阿哈納到了娶妻年齡,他家向薩哈達部巴斯翰巴圖魯?shù)拿妹们蠡椋瑳]想到人家嚴詞拒絕,理由只有一個:你家太窮。這話給任何一個人,都帶有明顯的鄙視態(tài)度,寶實聽著難受,卻只能默認。后來,董鄂部的酋長克撒的兒子也向薩哈達部巴斯翰的妹妹求婚,巴斯翰當(dāng)然一百個愿意,他看中的,是董鄂部的強大,想攀個高枝借光。然而,克撒的兒子額爾機瓦卻在求婚路上遭人截殺,釀成一樁血案。克撒便疑心建州寶實嫉妒這樁婚事,策劃了這起暗殺,懷恨在心。偏偏索長阿財迷心竅,私底下派人跟克撒謊稱知道是誰殺死他的兒子,以此為由企圖索要懸賞。哈達部落萬也來湊熱鬧,想借機逼董鄂部歸順自己,這樣子,幾方糾結(jié)在一起,克撒不敢惹哈達部落,可他不怕建州,就出兵把建州狠狠教訓(xùn)一下。建州吃了虧,自然也不甘罷休,聯(lián)合哈達部反擊董鄂部,寶實為了給自己和兒子洗冤,也是舉家上陣,義無反顧。
阿哈納是不是截殺董鄂部的兇手很難說,但這個人是很有些仗義性格的。王杲強盛時,常率人犯邊,搶劫明邊民財物,萬歷二年(1574),遼東總兵李成梁大兵壓境,王杲被迫放棄經(jīng)營多年的古勒寨,逃到阿哈納家里躲藏起來。李成梁隨后來追,危急時刻,阿哈納穿上王杲的衣服,假冒王杲幫助他逃出明軍包圍,救了王杲一命。但王杲終究沒有擺脫厄運,被李成梁押解進京,處以極刑。
王杲死后,就依附誰繼續(xù)生存的大問題,寧古塔六貝勒開會研究,寶實主張依附王杲之子阿臺,只有覺昌安目光遠大,提議依附明王朝并得到眾人同意。寶實對四兄覺昌安頗有意見。當(dāng)然,這僅僅是史料記載的,他們之間一定還存在其他矛盾,比如在繼承祖業(yè)問題上,朝廷賞賜物資分配等等,這些都為努爾哈赤起兵設(shè)置了障礙。
寶實生有四個兒子,長子康嘉、次子阿哈納、三子阿篤齊(阿都棲)、四子多爾郭(朵里火棲),兄弟四人與父親一起反對努爾哈赤,參與了堂子廟起誓發(fā)愿要消滅努爾哈赤,之后,與德世庫、劉闡、索長阿家的人采取威脅、孤立、暗殺等諸多手段,想加害努爾哈赤,結(jié)果一一失算。
寶實大約于努爾哈赤起兵前后去世,天聰九年(1635)正月,皇太極即將正式登基稱帝,他對國政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一項是家族內(nèi)部的冊封,在這次冊封中,寶實的子孫被詔令為覺羅,系紅帶子,以示宗室血脈的親疏。
〔特約責(zé)任編輯 李羨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