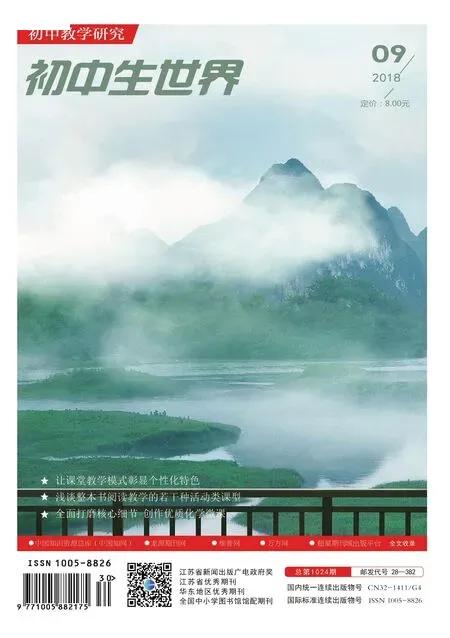我和小董的作文教學故事
■張 旋
小董個頭不高,其貌不揚,如果她不張嘴說話,你看不出她是從粉墻黛瓦、杏花春雨的江南來到我們這個偏僻的蘇北小鎮學校借讀的女生。事實上,無論是課上還是課下,她似乎都不大言語,所以我一開始都不知道新學期的二班里還有這樣一個外來生。
第一次注意到她是開學兩個星期之后的事情了。改到她的作文,我頓時被她的才氣深深吸引。這顯然是一位頗具語言天賦的孩子,并且一定對寫作有著特殊的愛好。她可以寥寥幾筆就將一些平常的人和事勾勒成一幅極具情味的圖畫。在一篇叫作《成長》的作文里,她用這樣的語言描繪自己的童年時光:
記得小時候,我是個特別沉默的孩子。我不喜歡和別的小朋友在一起玩,也不羨慕她們擁有漂亮的公主裙和五顏六色的糖果。那時,我們家還沒有搬到市區,在我房間的落地窗外有一大片田野。我總是抱著膝蓋坐在地板上,看著黃綠色的田野和遠處如水墨畫一般的青山,身邊放一個裝滿清水的杯子,往往一坐就是很長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篇寧靜得足以讓人心動的文章,那么優美的景致,那么沉靜的氛圍,還有那么老成的心境!我決定在班上讀它,順便認識一下這位似乎還有幾分憂郁的作者。
這堂作文課上得出奇地好。朗讀她的文章時,我發現這個叫小董的女生靜靜地趴在桌子上,不時露出羞澀的笑。我不知道此時她在想些什么,但能感覺到她內心那種抑制不住的快樂。其他同學也都靜靜地聽著,與平時的無精打采截然不同。
這之后,我對小董的關注就逐漸多起來,在班里讀她作文的頻率也逐漸高起來,因為她的作文寫得那么的好,讓你根本無法拒絕。她是那么敏銳,能發現咖啡的味道“低調而飛揚”,星星的光芒“微弱卻溫暖”。她是那么體貼,能感受到爸爸讓自己認識到“對大自然、對天空的愛,對生命的敬意”,媽媽讓自己“在書中找到另一個可以自由地笑、大聲地哭泣的天地”。她是那么有見識,讀張愛玲、亦舒、安妮寶貝,也讀蘇童和海子。尤其是海子,她視之為偶像并為之深深著迷。她甚至也用詩歌的方式表達對這位天才詩人的深情祭奠:“你平靜地臥在鐵軌上/灰云覆蓋著你的臉龐/你的瞳孔中被放大的悲涼/一如你曾經飄滿雨水的村莊/你將緊緊禁錮的希望/播種在你靈魂歸宿的地方/我只想知道現在的你/是否還面朝大海,是否還春暖花開/是否還在將你公元前或公元后的微笑/不斷尋尋覓覓又不斷返航……”
我漸漸發現,作文課讀她的文章,成了我和同學們共同的期待,而這個班級的作文水平也漸漸有所提高。有一次,小董的同桌在一篇作文中寫下了這樣的話:
她隨手一動就可以寫出很漂亮的句子,我真羨慕她可以寫出那么好的文章。或許是因為長久地膩在一起的緣故,現在的我也對寫作滿腔熱情……她不僅會寫,還會唱,真是了得。她的歌很好聽,很悅耳,很迷人……我想,如果我是男生,一定會情不自禁地愛上她……
有一天午餐后,小董的姐姐特意來跟我說,小董非常喜歡我的課,在家在外都常常念叨著。我當時只是一笑置之,并不當真,因為我也經常對我孩子的老師說此類討人喜歡的客氣話,無非是想讓老師對孩子多一些額外的關照。但是又有一次,我辦公室的另一位同事也告訴我,小董確實喜歡我的課,因為我對她作文的認可。她告訴我說,這孩子以前的語文老師很看不上她,說她的作文陰暗憂郁,使得她很是郁悶。而轉到這兒上學才一個月,她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精神愉悅,學習上進。這位老師再次告訴我,小董喜歡我的課,吃飯、洗手、睡覺時都有可能談及我的課。這下子我不由得不信,我可能真的改變了一個孩子,不光是她的作文,也許還包括她的人生態度。我覺得,她喜歡我,未必是因為我的教學水平有多高,我的課有多吸引人,而是因為她在我這兒找到了自信的緣故。
我也因此明白,為什么她的作文中還有很多諸如“成長是一道明媚的憂傷”這樣與她的年齡很不相稱的灰冷的句子。
在后來的一篇名為《綻放》的作文里,她終于吐露出了自己的心聲: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我聽聞,你始終一個人。”很長時間里,當別人問及我初二那一年的感受時,我都會用這句話來回答。
那一年真的發生了太多事情,盡管現在回想起來,我會嘲笑自己當時為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而苦苦地掙扎,但依然會感受到尖銳細小的疼痛——畢竟很少有人能坦然忘卻過去的傷痛。語文老師諷刺我的作文是“私人寫作”,批評嘲笑作文中那些“黑暗和壓抑的文字”。自下半學期起,她從來沒給過我的作文高分,經常用冷冷的語氣叫我重寫,說我缺乏中學生應有的青春活力;還讓我最好不要再在校報上寫浪費時間的文字,而應該去提高在她看來并不怎么樣的語文成績。
鋒利的話語如同匕首一樣深深淺淺地刺刮著我,使我動彈不得,無法呼吸。我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很灰暗,是那種感覺不會再亮起來的灰暗。
……
我終于明白她的文章中的那些“憂傷是嵌在心里的不可名狀的灼熱”,以及“像一只孤獨的野獸一樣將自己藏起來,然后默默地舔舐傷口”的句子是怎么來的,以及這些句子背后的不為人知的心理創傷。
對于這樣一個敏感的、好不容易在作文中袒露內心的女孩子,我沒有采用通常的做法——找她談話,也沒有詢問她的過去,或者說一些安慰的話,更沒有試圖給她開一個所謂的“藥到病除”的良方,我只是一如既往地在課上朗讀她的作文。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將近兩個月。一天中午,小董突然敲門走進了我的辦公室,向我索要電話號碼。像所有庸俗的故事的結局一樣,她告訴我她要走了,要回到她自己的家鄉去讀書。給了號碼后,我拿起筆,在她的作文本上最后一次寫下我的寄語:“你的文筆是那樣的好,因為有了你,班級才有了靈魂和榜樣,而你卻說要走了……”我之所以用這樣的溢美之詞,是因為我覺得,她需要帶著一樣東西上路,那樣東西叫作“自信”。
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作文教學培訓會上,在談及如何解決學生作文“不想寫”的問題時,我舉了小董的事例,同時引用這樣一句話:“我們培養一個人,就是培養他的自信;我們要摧毀一個人,也就是摧毀他的自信……賞識導致成功,抱怨導致失敗。”我認為,這句話適合于培養學生的作文興趣,同樣也適合造就健康的人生。
我真誠地希望,我的這位只有兩個月緣分的弟子,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夠在自信的天地間,經得住每一次坎坷、每一場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