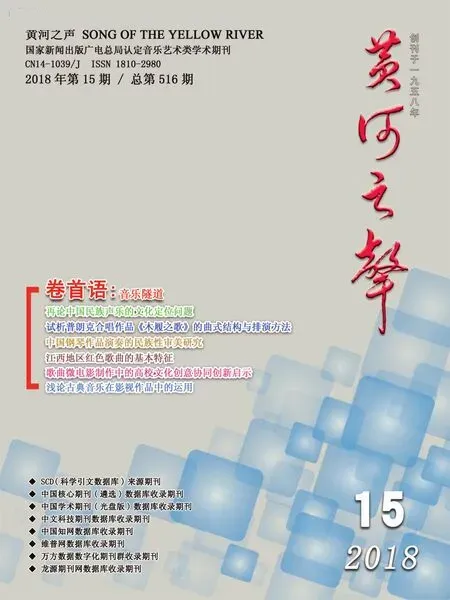達(dá)爾克羅茲體態(tài)律動(dòng)方法下的視唱練耳的視覺(jué)化*
徐 欣
(佳木斯大學(xué)音樂(lè)學(xué)院,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達(dá)爾克羅茲教學(xué)體系的教學(xué)內(nèi)容從節(jié)奏發(fā)展到了視唱練耳。因?yàn)檫_(dá)爾克羅茲在解決他在學(xué)生中發(fā)現(xiàn)的問(wèn)題時(shí)感覺(jué)到學(xué)習(xí)音樂(lè)、感知音樂(lè)、表現(xiàn)音樂(lè)需要具有敏銳的聽(tīng)覺(jué)以及堅(jiān)實(shí)的音樂(lè)技能。課堂實(shí)踐的內(nèi)容也從1907年以后發(fā)展為節(jié)奏律動(dòng)、視唱練耳、即興三個(gè)部分。訓(xùn)練的目標(biāo)是為了發(fā)展聽(tīng)覺(jué)與感知和聲進(jìn)行的能力。聽(tīng)覺(jué)的能力和對(duì)音樂(lè)樂(lè)句的分析能力最后會(huì)應(yīng)用于音樂(lè)“體驗(yàn)—表達(dá)”的環(huán)節(jié)成為以體態(tài)律動(dòng)方法進(jìn)行音樂(lè)學(xué)習(xí)的工具。
一、節(jié)奏律動(dòng)
“自動(dòng)”的行為方式建立在穩(wěn)定的精神境界和流暢的外化表現(xiàn)的基礎(chǔ)上,同時(shí)對(duì)旋律中的音符的回應(yīng)要求盡可能地詳細(xì)而不遺漏音樂(lè)中的任何信息。通常課堂中的體態(tài)律動(dòng)教學(xué)方法的音樂(lè)需要即興演奏的變化來(lái)提供。手臂、腳步、肢體的伸張姿態(tài)表示每一個(gè)音符的進(jìn)行,而旋律的韻律就能自然地表現(xiàn)為不僅僅是動(dòng)作組合而是真正的體態(tài)律動(dòng)組合。在形成完整、自然“體驗(yàn)—表達(dá)”之前,建立放松的、自動(dòng)的音樂(lè)“體驗(yàn)—表達(dá)”經(jīng)歷是極為必要的。對(duì)于體態(tài)律動(dòng)教學(xué)方法而言這是一種嘗試來(lái)充分挖掘一切本能的行為方式,從而表達(dá)整個(gè)思想意識(shí)和音樂(lè)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系。所有音樂(lè)教育工作者都認(rèn)為自然的音樂(lè)體驗(yàn)是喚醒人類音樂(lè)感知、音樂(lè)學(xué)習(xí)技能、掌握音樂(lè)要素、體驗(yàn)音樂(lè)感染力的最佳方式。在體態(tài)律動(dòng)這種方法中存在著循序漸進(jìn)的、嚴(yán)謹(jǐn)?shù)慕虒W(xué)步驟,即從如何建立自然的內(nèi)部和外部環(huán)境開(kāi)始。這種方法的層次是自由的并將這種自由滲透到每一個(gè)人的思想和行為反應(yīng)中去。這些練習(xí)是教師備課時(shí)的設(shè)計(jì)繼而在課堂中得以實(shí)施的結(jié)果。音樂(lè)建立了課堂中人與人之間的連帶網(wǎng)絡(luò),平衡意識(shí)也經(jīng)常能夠帶來(lái)優(yōu)美的視覺(jué)效果,同時(shí)這種平衡意識(shí)也包含了聽(tīng)覺(jué)與視覺(jué)、運(yùn)動(dòng)覺(jué)之間的關(guān)系。
節(jié)奏練習(xí)、旋律練習(xí)、卡農(nóng)練習(xí)、視譜演奏、即興和聲應(yīng)用連接等都是主要用于發(fā)展這些能力的教學(xué)材料。準(zhǔn)確和完善的系統(tǒng)必然存在科學(xué)的終極目標(biāo),這些目標(biāo)的完成取決于教學(xué)內(nèi)容的系統(tǒng)性以及教學(xué)方法的科學(xué)性,即所有的練習(xí)都應(yīng)具有明確而有意義的教學(xué)目的。在階段性訓(xùn)練中通過(guò)有目的的教學(xué)材料和方式來(lái)掌握音樂(lè)“體驗(yàn)—表達(dá)”所需要的技能,再通過(guò)系統(tǒng)化的課堂實(shí)踐來(lái)安排構(gòu)成音樂(lè)“體驗(yàn)—表達(dá)”的網(wǎng)絡(luò),從而修建起整個(gè)直覺(jué)的緯度并形成相應(yīng)的參照標(biāo)準(zhǔn)。當(dāng)這些技能受控于大腦且肢體能夠游刃有余地運(yùn)動(dòng)時(shí),學(xué)習(xí)的范圍便可以拓寬到其他內(nèi)容以發(fā)現(xiàn)音樂(lè)“體驗(yàn)—表達(dá)”和體態(tài)律動(dòng)表現(xiàn)中的問(wèn)題:在“學(xué)習(xí)技能—積累音樂(lè)體驗(yàn)—獲得音樂(lè)能力”的過(guò)程中存在多個(gè)過(guò)渡階段。這些過(guò)渡階段包含了所有肢體體驗(yàn)所需要的各種生理和心理技能。音樂(lè)“體驗(yàn)—表達(dá)”的體態(tài)律動(dòng)途徑有其模式化的標(biāo)度,用以評(píng)估體態(tài)律動(dòng)的質(zhì)量和進(jìn)程,以運(yùn)動(dòng)覺(jué)作為聽(tīng)覺(jué)練習(xí)的工具、以視覺(jué)效果作為檢驗(yàn)的標(biāo)準(zhǔn)。
二、視唱練耳
與體態(tài)律動(dòng)相結(jié)合的視唱教學(xué)最為顯著的是以動(dòng)作的細(xì)微差異和身體平衡的移動(dòng)變化來(lái)表現(xiàn)音階中音級(jí)與音級(jí)之間的關(guān)系、旋律中音符行進(jìn)的過(guò)程等。運(yùn)用體態(tài)律動(dòng)來(lái)調(diào)控和表達(dá)音高和節(jié)奏等音樂(lè)內(nèi)容,有效地加強(qiáng)音樂(lè)“體驗(yàn)—表達(dá)”的效果。在重音出現(xiàn)節(jié)奏變化的練習(xí)中體態(tài)律動(dòng)的應(yīng)用更為突出,視唱的練習(xí)用肢體細(xì)微的動(dòng)作變化、身體在空間中的移動(dòng)作為主要的方法。和普通的視唱方法相比所產(chǎn)生的不同就在于這種視唱的視覺(jué)外化形態(tài)更為突出、直接和具象。旋律組合帶有表情的漸強(qiáng)、漸弱的走向加人重拍等元素可以將旋律劃分為多個(gè)樂(lè)句,也可以作為判斷節(jié)拍或者曲式結(jié)構(gòu)的重要依據(jù)。體態(tài)律動(dòng)的方法可以表現(xiàn)為,如用手臂在空間中滑過(guò)的路徑,來(lái)表達(dá)出旋律的樂(lè)句劃分和節(jié)奏型等。“小組合作”的體態(tài)律動(dòng)可以表現(xiàn)出音樂(lè)的曲式結(jié)構(gòu)、復(fù)調(diào)中主題出現(xiàn)的位置等,如每一次主題的出現(xiàn)便表現(xiàn)出同樣的律動(dòng)組合,不同聲部交替出現(xiàn)的主題也能通過(guò)多人的小組合作予以表現(xiàn)較大的曲式結(jié)構(gòu)。對(duì)于聽(tīng)覺(jué)訓(xùn)練特別是節(jié)奏聽(tīng)覺(jué)訓(xùn)練中,肢體動(dòng)作的反射最為便捷地反映了旋律的特點(diǎn),對(duì)于旋律的漸強(qiáng)、漸弱等肢體的起伏猶如優(yōu)美的線條,具象了流動(dòng)的旋律。身體的運(yùn)用是可以被無(wú)窮地挖掘的,除了用簡(jiǎn)單的原地動(dòng)作、造型表達(dá)起伏和平衡以外,對(duì)空間的利用能夠使旋律的表情特征更為豐富。動(dòng)作的力度也能表現(xiàn)音樂(lè)節(jié)奏、表情的強(qiáng)度等等。
三、結(jié)語(yǔ)
音樂(lè)的教學(xué)方法也是在發(fā)現(xiàn)問(wèn)題解決問(wèn)題的過(guò)程中形成起來(lái)的。視唱練耳要注意不同的音樂(lè)元素,這些音樂(lè)元素在音樂(lè)旋律中會(huì)同時(shí)出現(xiàn),因此視唱練耳不僅僅是捕捉簡(jiǎn)單的一種信息而是要通過(guò)為單獨(dú)信息設(shè)計(jì)的視唱練耳練習(xí)來(lái)連接各種音樂(lè)元素之間的關(guān)系,最后形成在音樂(lè)進(jìn)行時(shí)聽(tīng)辨盡可能多的音樂(lè)信息的能力,這種聽(tīng)覺(jué)的主動(dòng)性就是聽(tīng)覺(jué)意識(shí)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