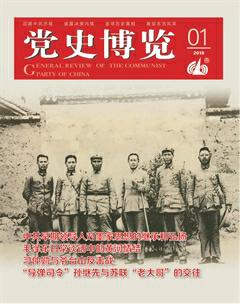“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
周炳欽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所做的《論持久戰》的著名演講中,曾以“戰爭和政治”為題,深刻闡述了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其中提出的“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等論點,成為毛澤東戰爭觀的重要名言。
辯證認識戰爭與政治關系的精彩篇章
戰爭,一直是人類關注的一個社會現象。在階級社會中,當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一出現時,更加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從而產生了各個階級對戰爭的不同看法和認識,形成了不同的戰爭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識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爭觀理論,即毛澤東軍事思想中的戰爭觀理論。
戰爭是什么,是個古老而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此前,在中國共產黨1936年12月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時,毛澤東曾給出了這樣一個科學而明確的定義: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
毛澤東揭示了戰爭與私有財產及階級之間的內在聯系、戰爭與政治斗爭的相互關系,從而說明了戰爭并不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永恒現象,而是一種歷史現象。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不僅對這些觀點做了進一步的闡述,指明戰爭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而且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的哲學原理,深化了對戰爭與政治關系的認識,為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理論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這是毛澤東通過考察戰爭與政治的普遍性,對戰爭與政治的一致性的認識。他說: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
這就是說,在戰爭與政治這個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中,政治屬于普遍性的范疇,戰爭屬于特殊性的范疇。要深刻認識作為個性的戰爭,必須從戰爭與其他各種社會現象的聯系中考察和研究戰爭。戰爭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同社會的經濟、文化、科技等諸多因素有著廣泛的聯系,但其中最本質的聯系是政治;戰爭絕不是單純的軍事行為,而是由一定時期內種種復雜的社會政治關系引起的,是帶有政治性質的行為。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這是毛澤東通過考察戰爭與政治的特殊性,對戰爭與政治的差別性的認識。他說:
“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于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干凈,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種緣故妥協了,但是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戰爭與政治之間既相一致,又相區別,即戰爭與政治相比,有其特殊性。毛澤東把“流血”與“不流血”作為戰爭與政治的根本區別。這表明,戰爭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爭,而是一定階級用以解決某種政治矛盾和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在階級斗爭以非暴力的斗爭形式和手段,不能解決階級矛盾或難以實現其政治目的時,便訴諸武力,導致戰爭。據此毛澤東認為:
“基于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種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敵的戰略戰術從事攻擊或防御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于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
毛澤東關于戰爭與政治關系的論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理論寶庫。
軍事理論升華源自兼收并蓄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理論上做出超越前人的創新,這源于他在實踐中對理論的追求和探索。他說: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于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這些過去的戰爭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著重地學習它。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的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著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著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為了肅清“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錯誤,毛澤東不僅領導全黨系統地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而且為此“發憤讀書”,除大量研讀馬列主義的哲學著作外,還下功夫研讀了古今中外的軍事論著。通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得以升華為理論概括。
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說:
“左”傾教條主義者說我照《孫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話,“倒激發我把《孫子兵法》看了,還看了克勞塞維茨的,還看了日本的《戰斗綱要》,看了劉伯承同志譯的《聯合兵種》,看了《戰斗條例》,還看了一些資產階級的。總之,激發我來研究一下軍事。”endprint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談話時又說道:
“后來到陜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那時看這些,是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此外,在現存面世的文獻中,還發現有毛澤東在寫作《論持久戰》之前的《讀書日記》。《日記》記錄了他從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的讀書情況。其間,他先后讀了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此前,他還讀了蘇聯和中國哲學家的著作,并留下了很多讀書摘錄和批注。
從毛澤東關于戰爭和政治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運用,對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汲取,以及對列寧思想的深化。
在世界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克勞塞維茨在馬克思主義誕生前,最早較全面而深刻地闡述了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他在《戰爭論》一書中,運用德國古典唯心主義辯證法,系統總結了歷次戰爭特別是拿破侖戰爭經驗,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經典命題,提出了“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政治還是孕育戰爭的母體”;“如果說戰爭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它“不是寫外交文書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等著名觀點。
列寧在1915年研究哲學和戰爭問題時,曾認真地閱讀過《戰爭論》,而且還做了萬余字的讀書筆記。列寧極為重視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與政治關系的論述,并在“戰爭是政治的工具”的第八篇第六章上批注:“最重要的一章。”其后,列寧在文章中高度評價并多次引用克勞塞維茨的重要觀點。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文中說:“‘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這是軍事史問題的偉大作家之一克勞塞維茨所下的定義,他的思想受胎于黑格爾。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堅持的觀點,他們把每次戰爭都看作當時各有關國家(及其內部各階級)的政治的繼續。”他在《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文中又指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這是造詣極高的軍事問題著作家克勞塞維茨說過的一句至理名言。馬克思主義者始終把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戰爭的意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來考察各種戰爭的。”1916年,列寧在《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一文中,又進一步做了這樣的概括:“怎樣找出戰爭的‘真正實質,怎樣確定它呢?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毛澤東在“戰爭和政治”的論述中,沒有直接引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而是引用列寧著作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觀點,并對后一論點特別加注說明。可見,毛澤東主要是通過列寧的有關論述,來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克勞塞維茨論述這一問題的豐富內涵的。毛澤東之所以未直接引用克勞塞維茨的觀點,應是因為克勞塞維茨未能科學地揭示這一命題中對政治范疇的認識,即把政治解釋為“是整個社會的一切利益的代表”,認為戰爭只不過是對外政策的繼續的國家間的關系。列寧對克勞塞維茨這個命題中的政治范疇做了批判的改造,明確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在階級社會中,“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毛澤東認識到列寧與克勞塞維茨在這一命題上的本質區別,依據馬列主義的階級政治觀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明確做出戰爭的定義后,又提出“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的著名論斷,進一步闡明了政治與戰爭的辯證關系。
對《戰爭論》一直記憶猶新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關于“戰爭和政治”的論述,雖然未提到克勞塞維茨和直接引用《戰爭論》中的文字,但《戰爭論》這部軍事理論著作,還是給了毛澤東以深刻的影響和諸多的啟迪。在他的《論持久戰》中,不僅在關于“戰爭和政治”的關系,而且在戰爭的目的、戰爭的蓋然性等方面,都汲取與發展了《戰爭論》中的思想。
關于這部著名的軍事理論著作,還曾留下了毛澤東請人找尋和自己學習及組織研究的故事。
1937年底,為編寫“抗日戰爭叢書”,研究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曾讓在身邊工作的郭化若去找《戰爭論》等書。12月28日,他寫信給郭化若說:
“你寫戰略,應找些必要的參考書看看,如黃埔的戰略講義,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在莫主任處),德國克老斯偉資(后譯為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蔣百里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其它可能找到的戰略書,報紙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論戰爭的文章通訊亦須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來看。……”
毛澤東讀《戰爭論》,是從1938年3月18日開始的。他在《讀書日記》中記載了逐日閱讀情況,至31日讀到第167頁。4月1日從第168頁看起,但之后日記便中斷了。
據有關當事人的回憶,在撰寫《論持久戰》之后,毛澤東還曾在延安專門組織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繼續研究這部軍事名著。
郭化若回憶說:
1938年9月間,毛澤東約了十來個人,在他自己的窯洞里開哲學座談會,每周一次,參加的有許光達、陳伯鈞、郭化若,后來又有蕭勁光、蕭克等將軍,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這期間的座談會上,專門請何思敬講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學”內容。
徐懋庸也回憶說:
當時專門請何思敬講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學”內容時,由于何思敬照著德文原著隨譯隨講,講得實在不太高明。每次講完出來時,將軍們既不滿意,我們也覺得索然無味。然而,毛澤東卻聽得很認真,還拿著一支紅鉛筆,在一個本子上不時地記錄。我們對這種態度和精神非常驚奇,因為不管何思敬講得如何不好,毛澤東都能從何思敬傳達的原著的話里,吸收到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意義。
參加這個小組學習的莫文驊回憶:
《戰爭論》的學習討論采用邊讀邊議的方法。當時只有一本書,是國民黨陸軍大學出版的文言文譯本,譯文又很粗劣,讀起來很不好懂。后來由何思敬同志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介紹研究一章,并發了講義。記得當時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同志說:克勞塞維茨的作戰指揮實踐不多,但集中兵力問題講得好。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和講話中,多次談到《戰爭論》,對其中的名言仍是記憶猶新。如1960年5月27日,他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當蒙哥馬利說:“我讀過你關于軍事的著作,寫得很好。”毛澤東謙遜地答道:“我不覺得有什么好。我是從你們那里學來的。你學過克勞塞維茨,我也學過。他說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繼續。”
毛澤東關于戰爭與政治關系的這些論述和他的思想脈絡,對我們認識戰爭的根源和本質,把握戰爭自身的特殊規律,正確指導戰爭,有著重要的啟發。
2013年7月15日,習近平在軍隊一次重要會議上談到關于戰爭的指導問題時,依然強調了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觀點: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籌劃和指導戰爭,必須深刻認識戰爭的政治屬性,堅持軍事服從政治、戰略服從政略,從政治高度思考戰爭問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