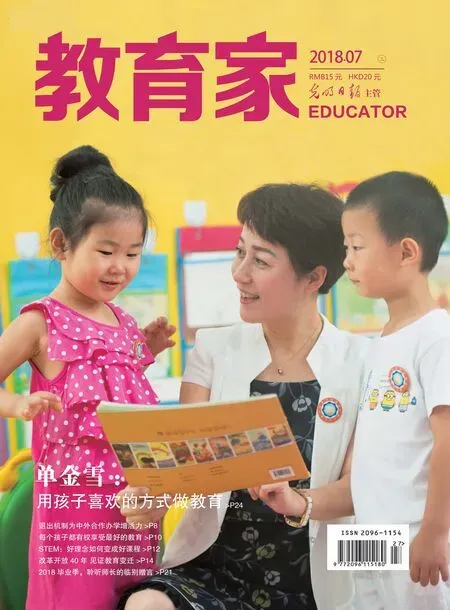從故鄉到故鄉
1993年9月,廣東省廣州市,王增剛背著沉重的行囊在經歷過步行、汽車、火車、公交交替進行近七個晝夜的長途跋涉后,終于來到了他要報到的學校——廣東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門口。他的行囊里裝有四季的衣服,有他愛不釋手的小說,有親人殷切的期望以及自己想給姥姥鑲一口好牙的小愿望——這就是他報口腔系的初衷。姥姥當時剛過六十,牙齒已多半脫落,說起話來滿口撒風。那時當地專業的口腔醫生寥寥無幾,集市上專事鑲牙的曾給姥姥鑲過一口,可她戴過之后把牙花都硌破了,所以索性不戴了,每天只能以軟食充饑。
王增剛來自于山東省壽光市,他的通知書是大隊書記在鑼鼓隊的簇擁下送到家里的。這其實是他第二年參加高考,那還是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時代。王增剛的父親是名建筑工人,每天在工地上“汗珠子滾太陽”地忙碌著,為了將來供給王增剛上大學,在王增剛上高一的時候,他就把抽了十多年的煙戒了。可是結果很意外,第一年高考,得知王增剛落榜的那一天,他父親像是被秋風勁吹的樹葉,頹敗不已。他坐在大門口的馬扎上,大口大口喝著一瓶“高粱紅”燒酒,任由四合的暮色將自己漸漸吞沒。漫長的沉默后,他對王增剛吐出一句話:“還是跟著我到工地干活吧!”
王增剛的命運在這里走到了一個分岔口。最后還是他母親把他推向了另外一條路。在當看到王增剛在父親的“規劃”里一言不發,她一改往日的唯唯諾諾,“孩子要是想去復讀,咱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他去讀!”母親是個地道的農家婦女,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盼著自己的孩子們能夠走出那片世世代代為之生存的鹽堿地。
復讀的一年更為艱苦,這段日子被記錄在王增剛的姐姐、作家王麗的散文里,“后來我看《塔鋪》,看到書里那些試圖想通過努力改變自己人生命運的農村青年,自然而然會想起弟弟,想到他在熄燈之后躲在廁所的燈下奮發夜讀的情景。而在當年,高考是改變農村孩子命運軌跡的最佳途徑,復讀對于弟弟來說,是破釜沉舟,只有這一次機會了。生活一向節儉的母親在弟弟周末回家拿咸菜時,悄悄往他書包里塞上一袋蜜汁包裹的‘琥珀桃仁’,‘這個能補腦’,母親慈愛的臉上帶著神秘。其實,即便被剛上小學的妹妹看到,她也不會爭搶攀要,在棗花暗香浮動的季節,弟弟的高考已經成了全家人的使命,神圣而鄭重。”
大學生涯轉瞬而過,王增剛畢業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姥姥鑲了一口能咬得動冰糖的得勁好牙。返回廣州后,2009年,他獲得副主任醫師職稱,完成地市級研究課題2項,在國家級刊物發表5篇論文。在廣州安家落戶數年后,他回到老家開設了當地第一家個人所辦的有專業資質的口腔診所,主張實用主義,盡可能用智齒替代假牙,還在當地論壇開設專業帖子答疑。
25年時光改變了很多,王增剛的母校招牌換成了中山大學,他的家鄉名稱從山東省壽光市大家洼鎮河套村改成了濰坊市濱海經濟開發區大家洼街道河套村,他家鄉的鹽堿地已不再是一望無際的曠野,而變成了樓群聳立的化工新城。然而,總有一些東西不會不變,例如他始終熱愛母親做的菜的味道,那其實是對家和家鄉的眷戀,正是這眷戀,讓他離開故鄉又回到故鄉,最終扎根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