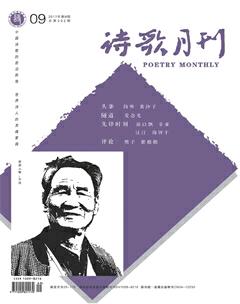讀詩筆記
簡明
1
人類需要孜孜不倦地探索兩個未知空間,一是人類自己的內(nèi)心;二是人類生存所必須而對的宇宙;心靈的無限向度,給人類自己提供了無限的探索性和可能性;而宇宙的無限容量,把一切強大的內(nèi)存,都變成了宇宙自己的內(nèi)存;內(nèi)心與宇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對微觀與宏觀相匹配的超級感應物;內(nèi)心的未知空間有多大,宇宙的未知空間就有多大;內(nèi)心與宇宙之間的排斥與兼容,如同兩臺不同性能、型號、年代的計算機;它們相互在程序上的試探、破解、溝通與交融,其實就是人類對自我、進而對未知空間的新發(fā)現(xiàn)、新拓展和新認知。
2
閱讀是人類的文明求證。可以毫無夸張地說,一個民族的閱讀史,實際上就是這個民族的文明史。而寫作,則可以說成是另外一種、或更高層次的閱讀——心靈的修行。音樂、繪畫、詩歌,是人類文明的悠遠天空;科學、宗教、法律,是人類文明的堅實大地;繁衍、生存、進化,每一個優(yōu)秀的民族都必須懂得:要像傳承自己的文字和優(yōu)秀基因一樣,敬仰人類文明的一天一地。
3
詩歌不是小說或散文的“袖珍版”,長句式不是,短句式也不是。小說劃分為長篇、中篇、短篇,這種劃分是文學藝術早期的不潔或“實用主義”,可能與“古話本”的取費標準相關,即:以小說的長短或以“實”計量;散文效仿之。詩歌有自己源遠流長、獨成系統(tǒng)的詞牌區(qū)分,縝密嚴格,只論高下,不論長短,以“意”計量。
4
盡管玄學中可能摻雜著人量的詩意成分,但詩歌絕非語言的玄學。詩意只是人類瞬間的非分閃念,這些稀奇古怪的念頭,只有找到語言這個五彩繽紛的附著體,如同靈魂找到了肉身,才不至稍縱即逝,這種境遇就像孩子把他們的涂鴉粘貼在白墻上。
5
詩歌不是語言的“意外”,而是“意外”的語言。
6
回憶是一種反向想象。反向想象不是重新經(jīng)歷曾經(jīng)的體驗,而是重新體驗曾經(jīng)的經(jīng)歷。重新經(jīng)歷曾經(jīng)的體驗,你得到的依然是舊有的;而重新體驗曾經(jīng)的經(jīng)歷,你將收獲全新的認知。
7
詩性是人性的閃電,而不是道德的碩果——詩性,是更高層更純粹意義上的道德,詩性照亮人性,超越人性,指引人性。詩性是人性稍縱即逝的燦爛,是人性獨一無二的浪漫;在人性的天空中,詩性絕不會選擇朗日和風時出現(xiàn),在暴風驟雨來臨前,詩性才會橫空出世。
8
在感受到的所有現(xiàn)象中,透進一束思想的光亮,這就是所謂的洞察。釘子和蚊子,就是這樣做的。
9
詩人不是講故事的能手。一個好詩人充其量只是一個好故事的引子,如同酒頭之于佳釀,如同藥引之于湯藥與病灶;詩人更擅長發(fā)現(xiàn)或者“激活”一個故事,然后由別人去講述。
10
詩歌看歷史的三個層次是:近距離看,能看到急流;中距離看,能看到河流;遠距離看,能看到開闊——思想的脈絡。
11
最深刻的距離不是——上下,而是——前后;這是因為:上下往往標記著幻境中的距離;而前后提示的是——現(xiàn)實中的急所與利害。
12
英國詩人艾略特(1888-1965)在一次偶然的閱讀中,讀到美國偵探小說之父愛倫·坡的小說《幽谷》中的幾句詩:“在那里等我吧,我一定不會,/忘記到幽谷中,和你幽會……”。詩句中憂郁的節(jié)奏,令艾略特非常癡迷。艾略特說:我從此找到了抒情的基調(diào)。直到艾略特寫出了《荒原》和獲得194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四個四重奏》,他一直把那次的閱讀往事,視為“鬼魂附身”。
13
法國詩人夏爾·波德萊爾(1821-1867)以象征派詩人領軍人物的頭銜蜚聲世界。波德萊爾發(fā)現(xiàn):“大名鼎鼎的詩人,早已割據(jù)了詩歌領域中最華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別的事”。1857年,波德萊爾出版了《惡之花》,震驚世界,《惡之花》一舉成為“頹廢派”詩人的圣經(jīng)。法蘭西帝國法庭以“有傷風化”和“褻瀆宗教”雙罪起訴波德萊爾,并查禁了《惡之花》。但是波德萊爾的聲譽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遺憾的是,波德萊爾的私人生活,給他帶來無盡的麻煩,他患有梅毒,沉迷鴉片,成為波德萊爾無法完成宏篇巨制人作品的障礙,最終摧毀了他的天分。
14
詩歌只承認名詞和動詞,不承認諸如形容詞等其他詞匯,形容詞是字與字之間的比喻,不過是名詞和動詞的混合體。正如真正的算術,只有加法和減法,乘法不過是加法的重復,除法不過是減法的重復一樣。
15
樸素是一種內(nèi)力,它用最普通的方式深入人心,卻極少人能夠做到;如同人人都知道直線是最便捷的傳遞路徑,但未必人人都能在語言敘述過程的曲折中找到直線。
16
詩歌的“自由體”是一劑敘述毒藥,它就像一架在高空中失控的飛機,誰都無法阻擋它向地而的俯沖;這部失控的說話機器,不分晝夜,喋喋不休,渴望打動所有靠近它的人。形式制約力的失靈或變相縱容,可能帶來的后果是:泛濫的毫無節(jié)制的表達,垃圾語言的傾泄,以及虛無飄渺的內(nèi)容。
17
詩歌成于句,而非成于篇,詩歌謀句不謀篇。所以,煉句是詩人的基本功。
18
沉默證明的是:我已經(jīng)說過了,或者現(xiàn)在還不到說的時候。沉默也是一種發(fā)聲——在閃電之后,這種奮不顧身的朝前追趕的聲音,更具備穿越的欲望和傾軋的能量。
19
如果一個詩人活著,請賜給他天才;如果一個詩人死了,請賜給他時間——時間是最偉大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