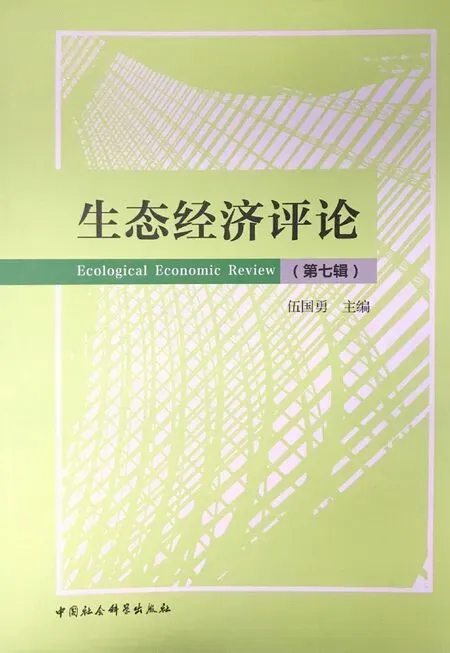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鄉村研究文獻回顧與展望
韋 瑋
內容提要:對比20世紀早期的中國鄉村研究,本文梳理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部分中國鄉村研究,重點分析我國鄉村研究中的追蹤研究、歷史記憶、社會變革和鄉村移民幾個方向的研究,這些研究直接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鄉村的很多現實問題,并提出了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中的 “鄉村”研究趨勢。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研究中國社會的必然要研究中國的鄉村社會,如費孝通先生的 《鄉土中國》揭示了中國鄉民社會中 “生于斯、死于斯”“禮、序、差序格局”的中國農村基礎社會結構、該書成為了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典范之作。在20世紀社會人類學研究中,西方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主要為四種研究范式:從市場維度研究的施堅雅范式、從文化與權力維度研究的杜贊奇范式、從宗族維度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從經濟維度研究的黃宗智方式①鄧大才:《超越村莊的四種范式:方法論視角——以施堅雅、弗里德曼、黃宗智、杜贊奇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這四種范式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解讀了中國鄉村社會,成為當時中國鄉村研究的主流范式。
中國早期的鄉村研究可分為漢人社會和少數民族社會的研究,漢人研究中有費孝通的 《江村經濟》、林耀華的 《金翼》、楊懋春的 《一個中國倒村莊:山東臺頭》、楊慶堃的 《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村落》等等;少數民族研究有林耀華的 《涼山夷家》、田汝康的 《芒市邊民的擺》、許烺光的 《祖蔭下》等這些早期中國鄉村研究中民族志都是成為中國村落社會研究的一個個里程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政治環境的影響,西方學者無法進入中國做研究,大部分對中國對研究采取了迂回策略,轉戰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研究中國社會,比如像武雅士、芮馬丁、王斯福、郝瑞等人對中國漢人社會民間信仰的研究。①陳剛:《西方人類學中國鄉村研究綜述》,《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科學社會版)2010年第3期。在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進入了全面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特別是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對外開放,許多西方學者開始到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包括我國的許多學者也開始從新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鄉村社會。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關于中國鄉村研究的主要集中在追蹤研究、歷史記憶、社會變革和鄉村移民這幾個大的方面,內容涉及土地改革、集體化、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創傷,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變遷等,展示了在鄉村社會變革的時代下,鄉民們的各種反應,表現了中國社會在社會改革的過程中,社會結構從鄉村的 “社群”開始向城市 “網絡”變化的趨勢。
一 中國鄉村研究中的追蹤研究
追蹤研究,其實質就是在不同的時間點對同一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多用于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中。追蹤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多有出現,這里面比較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是莊孔韶的 《銀翅》,《銀翅》是對其老師林耀華先生 《金翼》一書進行的跟蹤研究,但其并不是僅僅復制性地研究了當時林耀華先生所研究的田野點,而是在田野民族志和理論創新上都有新的開拓②周泓:《20世紀中國社會史的人類學研究——莊孔韶 〈銀翅〉筆談》,《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確立了一條追蹤研究前輩重要田野調查點新的學術實踐路線,并將之擴大化;周大鳴的博士論文 《鳳凰村的變遷》是對葛學浦 《華南農村生活——家族主義社會學》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的追蹤研究,《鳳凰村的變遷》對鳳凰村的人口特征,婚姻家庭、經濟生產、民俗信仰、宗家制度、村落政治等從20世紀初進行追溯,做今昔的對比,既有歷時性研究內容對比,也兼具了人類學理論方法上的創新。
21世紀初期,北京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與云南省展開合作,對社會學、人類學學者在抗戰期間研究重鎮 “魁閣”工作的調查點進行 “再研究”,系統地、有計劃地組織幾位北大人類學系博士研究生跟蹤研究了早期的幾本云南經典民族志,如梁永佳的 《地域的等級:一個大理鎮的儀式與文化》針對許烺光先生的 《祖蔭下》所研究的大理喜洲進行再研究;張宏明的 《土地象征——祿村再研究》是對費孝通先生、張之毅先生等人的《云南三村》中的 “祿村”的再研究;褚建芳的 《人神之間:云南芒市一個傣族村寨的儀式生活、經濟倫理與等級秩序》是對田汝康先生的 《芒市邊民的擺》關于德宏洲 “那木寨”的再研究,這是學界一次集中性有計劃地對前人的研究進行 “再研究”的學術活動,一方面揭示了幾十年來的社會文化變遷,同時也進行了人類學理論和方法上的探索和反思,王銘銘也撰寫了 《繼承與反思——記云南三個人類學田野工作地點的 “再研究”》一文對這次 “跟蹤調查”進行了總結。
同時也有一些跟蹤研究的論文,如周大鳴、高崇①周大鳴、高崇:《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研究——廣州南景村50年的變遷》,《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4期。對楊慶堃 《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村落》(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的跟蹤研究,對當地改革時代的所形成的城鄉接合部社區進行研究;劉志揚、駱騰 《從革命到改革》完成了對J.帕特夫婦東莞茶山研究 《中國農民:一場革命的人類學研究》(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的追蹤研究等,這些文章完成了對中國社會變遷的分析研究,歷時性的分析了革命時代中國到改革時代中國的鄉村社會,中國的鄉村在中國社會改革的過程是如何卷入世界資本市場中。
二 中國鄉村研究中的歷史記憶研究
記憶研究一直是心理學研究的重點,在認知心理學里認為記憶是被“圖式”決定的,這種圖式是個人過去經驗與外在世界印象集結所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傾向。個人的經驗與外在世界的印象,同時也強化和修正個人的心理構圖,人類學、社會學學家們從記憶中來研究,分析形成記憶的個人經驗與外在印象的社會歷史,它們是如何建構社會記憶的。
景軍的 《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村歷史、權力與道德》開啟了國內學者關于鄉村研究的新視角,從社會歷史記憶的角度來解讀中國鄉村社會。作者從社會史開始,梳理了記憶的社會基礎,解釋社會記憶的理論性,分析社會記憶中集體記憶、官方記憶和民間記憶的三種研究取向,揭示了記憶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重要的意義。 《神堂記憶》通過孔家人關于1960年那個動蕩的冬天記憶敘述,開啟了中國近代鄉村 “社會記憶”的深刻研究,以村民們的口述史來回顧村莊,乃至整個國家社會的革命與改革,其中包括了國家、歷史、權力、道德之間的關系。圍繞20世紀5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的復蘇兩條時間主線考察在毛澤東時代國家發展激進模式下的鄉民遭受的苦難和農村改革后重建恢復宗教價值和儀式知識的過程。①景軍:《神堂記憶:一個中國村莊的歷史、權力與道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6頁。從個人境遇、村莊的逆境、村民對災難的處理以及村莊的文化復蘇來講述了一場與官方不一樣的鄉村歷史故事,以及大川村的村民是如何運用記憶來重構他們的社會關系。
繆格勒 (Erik A.Mueggler)的 《野鬼的時代》(The Age of Wild Ghosts-Memory,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采用另外的一種述說記憶的方法來表達國家和中國少數民族之間的權力關系。在云南楚雄直苜村,繆格勒發現了當地彝族的記憶認知模式是交疊的時間和互相包含的空間觀念:兄弟和姐妹之間的關系構成的生產單位是整個親屬關系的基礎;糧食生產周期、人生育循環、聯姻關系構成當地人獨特的宇宙體觀②吳喬:《人類學家的眼、哲學家的腦、文學家的嘴——評讀 〈野鬼的時代〉》,《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彝族人認知記憶的方法是另外的一套文化體系,與他們生命周期、親屬關系等密切相關。繆格勒描述了一個發瘋的老男人,他狂亂和怪異的行為,還有一群狂舞的彝族老女人,他將當地人的噩夢與鬼魂映射為國家權力的代表國家干部,隱約式的表述策略,透過當地彝族人身體、房屋、祭祀、記憶去看待歷史。將個人經驗與社會規則的敘述有效同時張開,從偶然性的夢境與確定性的社會制度相結合這種認知記憶方式的角度來解釋鮮活的生命經驗與有規則的社會是如何結合起來。
用記憶這個視角去研究歷史,研究社會,是歷史人類學的一個有效的研究路徑,記憶是沒有時間緯度的、是被壓縮的,以這種方式去研究歷史,這就要求在研究過程中,把感覺的東西和理性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把生活中所發生的不可言說的事物和社會規范結合起來分析,尋找之間的關聯點來進行敘述,這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后人類學從結構性的研究轉向人的真實生活、內部視角、身體經驗去感同身受,從當地人的經驗去看歷史,從記憶去看村落歷史和國家社會發展的研究趨勢。
三 中國鄉村研究中的社會變革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處在一個急劇轉型的時代,鄉村通過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產到戶,土地集體化向土地私有化轉移,人們的觀念也開始發生了轉變,鄉村集體生活開始逐漸地變為了私人生活,鄉村的空間關系也不再局限于土生土長的土地,可能通過流動置換為另外的一個空間關系,正如我們所說的城中村,中國鄉村的社會變革是有目共睹的,對因社會變革所帶來的鄉村變革的研究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去理解鄉村,理解社會,理解中國的發展。
把閻云翔的 《禮物的流動》和 《私人生活的變革》兩本書來進行對比閱讀,就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國農村人際關系在時代面前發生的悄然變化。在 《禮物的流動》中所描寫的村民們互惠人際的關系在 《私人生活的變革》中已經不一樣了,村落的家庭已經從大家庭生活方式改變為了小家庭的生活模式,剛結婚的青年夫妻均紛紛要求各自的小家庭獨立,脫離于大家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生活是為了自己的小家庭謀福利,打破了傳統宗族家庭中的親密程度,宗族的規模被大大削弱,社會的組織的緊密性也遭到破壞,同時老人贍養的方式也開始產生了變化,不孝順的現象在中國的農村并不少見,宗族的約束力在減弱,鄉村的人際關系在社會變革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被改變。
改革中的鄉村,外出務工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的被打破后,農民通過勞動力的流動來到城市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關系體,這種關系是建立在地緣上的,有時也是建立在親緣上的。項飚的 《跨越邊境的社區:北京 “浙江村”的生活史》從1984—1995年時間歷程上給大家展現了一個浙江移民的生活歷程,其形成、結構運作和周邊的關系,開始提出了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的 “新社會空間”①項飚:《跨越邊境的社區——北京 “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張鸝的 《城市里的陌生人》采用列斐伏爾的 “社會空間”理論來解釋北京郊區溫州人聚集的“城中村”的空間關系,改革開放后,從鄉村來到城市人們由傳統的農民變成了個體經營者,他們在城市邊緣創造出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社會網絡,傳統的空間關系與社會關系在這群農村流動人口中發生了身份等級的變化,在城中村里面 “空間、權力和身份變遷相互交織,重塑國家—社會關系”②張鸝:《城市中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絡的重構》,袁長庚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當地人與外來人口對住房空間關系的置換,流動人口中衍生出來的代理管理者,以及國家應該如何應對這種新生社區的種種問題在這個“城中村”中上演了中國改革時代的空間與權力、合法與非法、國家與社會網絡利益矛盾交融劇幕。
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建設,改革時代中的鄉村城鎮化問題越來越突出,在朱曉陽老師關于昆明螺螄灣地區農民土地問題的研究中指出,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農民、國家、開發商和商戶形成了利益的矛盾體,帶來了很多的社會問題,農民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土地價格在不斷上升,農民轉讓的土地并沒有給村民帶來本質上的利益,農民因城鎮化建設直接變成市民,生活質量還下降,螺螄灣新舊商戶和開發商之間的矛盾,政府的決策管理等等在這片曾經的鄉土上造成了大大小小的沖突事件③朱曉陽:《魚肉昆明螺螄灣——一場權力—資本的歡宴》2009年12月8日,新浪博客(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0 fzdy.htm l)。,這些是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問題的一個個縮影。
四 中國鄉村研究中的鄉村移民
隨著農村地區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以后,農民從 “生于斯、死于斯”的土地解脫出來,或進城務工,或庫區、生態移民等,從農村遷入城市,農村人口在不斷地發生遷移,甚至流向海外,這些遷移有的是主動的遷移,而有的是被動的遷移。
庫區移民、生態移民,是中國農村非常典型的一種移民現象,因為國家建設或者生態環境保護需要,將村民們從他們土生土長的土地中置遷到另外的一個環境中生產,其中產生的文化適應問題、生產生計變遷等種種問題都是鄉村的實際問題,如程瑜對從三峽庫區遷入廣州羅博、三水的移民從語言、環境和生產方式等的不適應來進行人類學分析,并提出相關的對策研,①程瑜:《廣東山峽移民適應性的人類學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馬小平對寧夏南部山區移民到黃河灌溉區的人群進行了研究,探討生態移民對移民者社會方式、族群文化宗教信仰的影響,尋找文化適應和生態移民社區重建之間的可持續發展②馬小平:《人類學視野下生態移民的文化變遷》,《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20世紀中期,國內外政治局勢的緊張,東南亞排華反華浪潮起伏,很多海外華僑被迫從移民國回到了歸屬國,國家在接收這些華僑的安置上,以及他們歸國后的文化適應、發展問題都是近年來也是一個研究的重點。如黃禎禎的 《重構家園——人類學視野下一個移民鎮的成長軌跡》就研究了從越南回到廣西北海的疍民,如何在國內重建自己的家園,以及他們的身份認同問題。③黃禎禎:《重構家園——人類學視野下一個移民鎮的成長軌跡》,碩士學位論文,廈門大學,2008年。林綺純也對廣東的印尼歸僑農場進行研究,針對國家、家鄉和歸屬三個關鍵詞對他們歸國后的情感認同、社區發展的問題進行闡述。④林綺純:《國家、家鄉與歸屬——對廣東省英德華僑茶場歸僑的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中山大學,2015年。
我國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文化歷史上存在著長期的海外移民經歷,對海外流動具有特殊精神需求,而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的禁海和政治因素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一傳統,所以在改革開放后,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海外流動的恢復變得越來越頻繁。如在 (Cosmologies of Credit)①Julie Y.Chu,Cosmologies of Credit: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stination in China,Raleigh: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這本民族志中,(Chu)以福建龍巖的移民為個案研究,分析改革開放后中國沿海的農村海外移民與其僑鄉的關系。開篇以一位即將準備非法偷渡的女性村民為描寫,生動地刻畫了她對偷渡美國的美好夢想和現實的殘酷,為何在這樣的殘酷情況上,仍然抱有對偷渡的極大熱情,這種復雜性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渴望,更有物質上的需求,同時也與中國社會歷史、海外華人流動和全球化勞工流動的背景密切相關。
五 “流動”的鄉村
隨著我國的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化,周大鳴指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大的轉變就是從地域社會到移民社會的轉變”,提出中國的城市從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轉型發展②周大鳴:《城市正從地域性社會向移民城市轉變》2015年4月28日,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a/20150428/43650001_0.shtm l)。,這個概念同樣也可以體現中國農村社會的轉變,從中國農村深化改革后,人口的流動是非常頻繁,可以呈現出中國的農村越來越趨于一種 “流動”的狀態,而這種流動也有別于上面所說的遷移,農民工的流動,城鎮化建設中的農民流動,西部往東部流動,東部往海外流動,這樣的 “流動”更具雙向性和靈活性,流動的主體,即鄉民們,他們在主動地發揮他們的行動實踐能力。
今天 “Diaspora”在學術研究中是一個流動寓居的概念,這個概念也許可以借鑒用來研究中國 “流動”的鄉村。全球化和Diaspora中,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一種單項的流動模式了,我們逐漸地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僑鄉與僑居國之間的關系和移居者們的社會關系網絡,他們在流動過程中整合出來的文化和經驗。人口的移動不是一個單維度的靜態研究研究,涉及了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是在一個多維度里面的靜態分析,流動中的Diaspora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流動,他們也開始主動在發揮著他們的行動實踐,Diaspora變成了一種靈活的公民身份,這種實踐空間在個人、團體、國家不同層面中互動,這也變成了一種趨勢。在全球化概念中的Diaspora,我們通常把其在一種跨國論中來討論,強調一個國家的主權,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做這樣的嘗試分為兩個空間概念討論,在現代性、全球化條件下的一種作為跨國的Diaspora和一種國家內部的Diaspora?如果可以國家內部的Diaspora,中國的國內的農民工流動為一種典型分析研究,他們同樣迫于全球化發展的壓力背井離鄉外出打工,這兩種時空范圍的Diaspora是如何起源?各自特點與經驗,相互間的影響,在Chu的書中就已經有提到,當龍巖的人移居到美國,而中國內地其他群體又移居到了他們的家園里,這種相互的關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將會怎么樣的發展,或許是我們人類學可以思考的一個新角度。
六 結 語
趙旭東在鄉村研究中提出了從 “問題中國”到 “理解中國”的概念,他認為把鄉村當作問題來研究的思路是不對的,從本質上就認為鄉村是有問題鄉村,這會對我們的鄉村研究帶來偏見①趙旭東:《從 “問題中國”到 “理解中國”——作為西方他者的中國鄉村研究及其創造性轉化》,《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作為一名研究者,應該明確看到的是從鄉村的本質去理解鄉村,去認識真正的鄉村本質,才能做好鄉村的研究,回顧80年代以來的鄉村研究的這幾個方向,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隨著社會的變遷,鄉村不可能是不變的鄉村,鄉村的變化是延續性的,是內外因素所改變的,做好中國的鄉村研究,做好中國研究,就必須能夠認識鄉村的變化性,從多角度來理解鄉村,認識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