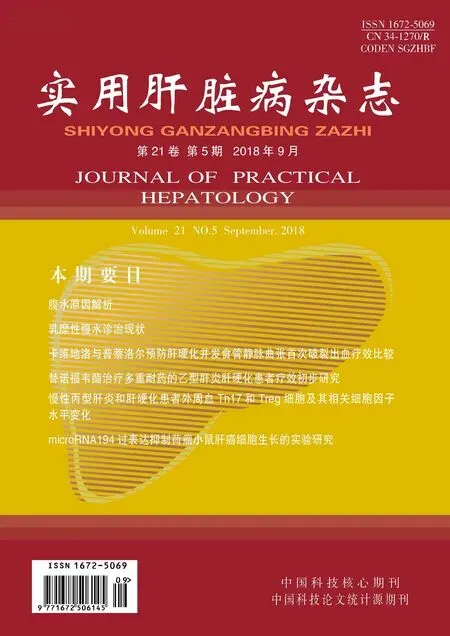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自身抗體檢測及其臨床意義研究現狀*
姜宏達綜述,周海舟審校
據估計,全世界有2%~3%,即約1.7億人感染了丙型肝炎病毒(HCV),全球每年新發HCV感染病例約3800萬,且近年來呈現遞增趨勢[1]。 HCV感染不僅會引起肝臟炎癥壞死,并且大部分丙型肝炎患者會轉變為慢性病毒感染,肝纖維化引起機體內環境紊亂,最終發展成為肝硬化,甚至肝細胞癌。肝臟纖維化的過程不僅僅只是反復慢性炎癥作用的結果,近些年的研究表明HCV感染不僅可觸發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也涉及自身抗體的出現,而肝纖維化的發生發展也可能與此相關。HCV可能參與破壞了機體對自身抗原的耐受性,從而引發自身免疫反應。在HCV感染者中已經揭示了一些與肝臟慢性感染相關的肝外表現,其中大多數可以通過免疫學機制介導,而不是與肝外組織直接感染有關。
直到近些年,聚乙二醇干擾素α(pegIFN)與利巴韋林的聯合治療降低了藥物的吸收速度和腎臟對其的清除率,從而能在治療期間保持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濃度。因此,該治療方案被認為是丙型肝炎治療的標準治療(PR)[1]。干擾素可能誘發自身免疫性疾病或惡化預先存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2]。因此,在治療前篩選出自身抗體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可能是干擾素療法的相對禁忌證。
在慢性HCV攜帶者中經常會發現非器官特異性自身抗體(non-organ-specific autoantibodies,NOSA)陽性[3],特別是抗平滑肌抗體(SMA)和抗核抗體(ANA)等。 在這種情況下,主要應該關注的方面應該是區分自身免疫性肝炎(AIH)與病毒性肝病,因為這些將影響后續針對不同情況的患者治療方案的選擇[4]。
近些年,許多文獻陸續介紹了HCV感染患者甲狀腺功能異常和抗甲狀腺抗體的高檢出率。 此外,基于IFN治療的主要和常見不良反應是治療期間甲狀腺疾病的發生和發展。據研究報道,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包括Graves病、甲狀腺炎和原發性甲狀腺功能減退癥等[5]。
從臨床觀點來看,自身抗體的存在引起學者們懷疑患者在接受治療之前就可能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可能是由基于IFN治療丙型肝炎引起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亂。本文將重點回顧丙型肝炎患者的自身抗體的發生率、這些自身抗體陽性的臨床意義,以及針對這些情況推薦的處理方法。
1 NOSA
1.1 自身抗體檢出率 NOSA首先被描述為自身免疫性疾病,現在經常被發現于慢性HCV攜帶者血清中[6]。它們的檢出率因地區而異,效價被認為是有意義的分界點。最常見于慢性丙型肝炎的自身抗體是SMA,其發生率變化很大,范圍在4%~78%[7]。在幾項研究中,在4%~54%慢性HCV感染患者血清檢測到了自身免疫性肝病和其他炎性疾病的標志物,即ANA,在另幾項研究中[8],ANA作為自身免疫性肝病和其他炎性疾病的標志物,也在4%~54%的慢性HCV感染患者血清中被檢測到[9]。在NOSA中,抗肝腎微粒體-1(LKM1)檢出率較低,其檢出率介于0%和13%之間[10]。關于NOSA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在HCV感染患者中與AIH中存在的交叉現象。在AIH患者中,盡管NOSA的檢測不是特征性的,但仍然是診斷的標志。然而,大多數慢性丙型肝炎和NOSA陽性患者卻不符合AIH的診斷標準。雖然這組人群中AIH的實際發病率尚不清楚,但估計只有少數人存在這種交叉現象。應用糖皮質激素和硫唑嘌呤等免疫抑制劑可以治療AIH患者,但一般來說,對于慢性HCV感染患者,不推薦這樣的治療方案,因為它通常會增加病毒血癥的嚴重程度[11]。而且IFN-α通常不推薦用于AIH患者的治療,因為這種治療產生的免疫刺激可能導致疾病的惡化。因此,慢性HCV感染與AIH之間需要進行仔細的區分,其臨床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1.2 組織學特征 有人提出,對于疑似慢性丙型肝炎(CHC)/AIH交叉現象的患者,其治療必須從主要病因的確定開始,從而能夠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12]。雖然沒有單一的組織學特征表現作為確定CHC或AIH的特異性,但已經針對每個個體描述了不同的組織學模式。AIH患者更可能有嚴重的小葉間壞死和組織炎癥,碎片狀壞死,多核肝細胞和廣泛的肝實質塌陷區域等,而CHC患者更可能有膽管損傷、膽管損失、脂肪變性和門脈管內淋巴細胞濾泡的產生等。然而,在CHC患者中已經發現了一種界面性肝炎(一種原因不明的自身免疫性肝炎的組織學特征)的組織學表現。在這種表現中門靜脈周圍的再生結節經常是不能被認為提示免疫性損傷,因為它是再生肝細胞被更強烈的炎癥反應作用的結果,而這種炎癥反應的結果在其他肝病患者中也是可以觀察到的。
過去,文獻對慢性丙型肝炎的治療給出了具體方案。當CHC患者出現NOSA和AIH的組織學特征時,許多科學家將皮質類固醇(有時是硫唑嘌呤)作為一線治療方法。在這種情況下,盡管病毒血癥的程度可能明顯增加,但是血生化學和組織學的改善仍得以實現。這些患者在生化緩解期和接受類固醇治療時是否應進一步接受IFN-α治療,目前也在討論之中。今天,盡管有大量的研究結果,但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存在NOSA的意義仍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些學者已經在血清NOSA陽性的CHC患者發現了其他一些血清肝臟損傷標志物的變化,可反映潛在的肝臟病變的嚴重程度。有人提出ANA的檢測可能有助于預測肝纖維化是否快速進展。然而,之前的報道未能證實NOSA陽性和NOSA陰性患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組織學差異。
1.3 抗病毒治療方案 就抗病毒治療結果而言,抗病毒治療對CHC患者的療效與NOSA的存在呈負相關關系,特別是對于非1型HCV感染者。相反,在大多數早期研究中,體內ANA水平并非能作為其預測因子。目前,α-干擾素治療已經排除了自身免疫性肝炎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被認為是有效的。NOSA陽性個體在IFN-α治療期間發現血清ALT水平顯著升高。有些病例可能因為藥物治療的中止而使血清ALT水平降低,有研究稱IFN-α治療可引發AIH,并且患者因此而出現免疫抑制的表現。自身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是高滴度ANA患者于IFN-α治療時的另一種可能的并發癥[13]。
在治療期間,血清NOSA滴度可能會升高[14,15],或者在某些情況下血清NOSA也可能會消失,轉變為陰性。此外,在治療前NOSA陰性的CHC患者可能在治療期間產生了自身抗體[16]。α-干擾素治療期間NOSA滴度的增加與持續病毒學應答率(SVR)低相關。在治療期間,建議仔細監測肝臟生化和NOSA水平。應每3個月篩檢一次自身抗體,每月監測血清ALT水平。 在治療期間,如出現自身抗體滴度升高,ALT正常,應該監測,而不必太擔心。 ALT升高應謹慎對待,特別是如果自身抗體滴度高,因為他們可能反映自身免疫的產生,后者損傷了肝細胞。在這些病例中的鑒別診斷應該包括藥物肝毒性(通過IFN-α或在治療期間可能已經服用的其他藥物)或其他病毒合并感染。考慮到上述情況,盡管事實上沒有臨床試驗對這個問題進行具體的評估,但無IFN-α方案是NOSA高滴度和組織學結果提示CHC/AIH交叉現象合并癥患者的合理選擇[17]。
2 抗甲狀腺抗體
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AITD)是以免疫自身耐受性喪失為特征的一組疾病,其最常見的疾病包括Graves病和橋本氏甲狀腺炎[18]。AITD的特征是存在抗甲狀腺自身抗體(TAAb),例如抗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抗體(TPOAb)、抗甲狀腺球蛋白抗體(TGAb)和抗促甲狀腺激素(TSH)受體抗體(TRAb)等[19,20]。
橋本氏甲狀腺炎是AITD最常見的臨床表現。該病通過亞臨床甲狀腺功能減退癥【TSH水平升高,正常游離甲狀腺素(fT4)水平)或臨床上明顯的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升高的TSH,降低的fT4)】。一些患者出現甲狀腺腫。該病基于甲狀腺功能減退癥狀和TPOAb和/或TGAb的存在而得出診斷。Graves病是以甲狀腺毒癥為特征的自身抗體介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Graves病是由TRAb直接刺激甲狀腺上皮細胞引起的[21]。臨床上有甲狀腺機能亢進癥癥狀和甲狀腺腫。Graves的眼病可能比較明顯。實驗室檢查顯示血清TSH水平降低,fT4升高,游離三碘甲狀腺原氨酸(fT3)升高,而TRAb降低[22]。血清TRAb檢測在甲狀腺機能亢進癥的鑒別診斷方面非常有用,其敏感性和特異性均高于90%。
2.1 抗甲狀腺抗體檢出率 甲狀腺自身免疫是HCV感染的共同特征。據研究表明,慢性HCV攜帶者TAAb高度流行,多年來從4.5%提高到25%。TPOAb和TGAb的檢出率分別為5.4%~30%和從0%~37%[23]。如此顯著的變化可能歸因于所使用的不同檢測方法,和/或這些研究中針對的是不同地域、種族、年齡和性別人群。碘攝入或其他感染因子等環境輔助因素也可能在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的發展中作為重要因素而存在。TAAb在女性中更常見,并且其檢出率隨著年齡而增加。TAAb的存在并不總是反映出AITD的存在。許多個體可能無癥狀,表現為正常水平的甲狀腺激素水平。TAAb的存在可能表明亞臨床甲狀腺疾病和發展為臨床甲狀腺疾病的風險在增加。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甲狀腺功能異常的患病率為3.6%~23%[24]。在IFN-α治療患者中TAAb檢出率波動范圍較大,可能存在幾種可能的解釋,包括用于測試TAAb的各種試劑、定義血清陽性的參考值和所研究患者的種族存在差異等。在血清TSH或甲狀腺激素水平與自身抗體滴度之間沒有觀察到相關性。盡管如此,慢性HCV感染患者AITD(即橋本氏甲狀腺炎、萎縮性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和Graves病)的高患病率通常與體液性甲狀腺自身免疫相關(血清TAAb水平高于正常值)。
2.2 IFN-α治療的風險 甲狀腺疾病的風險除了目前要關注AITD之外,也要監測血清TAAb陽性的CHC患者在IFN-α治療期間發生甲狀腺疾病的風險。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IFN-α治療中反應性TAAb的出現可作為甲狀腺功能異常的高風險因素[25]。在這方面,聚乙二醇化IFN似乎具有與標準IFN相同的作用[26]。IFN-α的劑量和持續時間不影響IFN-α誘導的甲狀腺炎的發展,也不影響病毒學應答。盡管一些學者持否定意見,但一些研究表明治療之前NOSA陽性的HCV感染患者使用干擾素治療丙型肝炎可以誘導TAAb的產生,或者引起TAAb水平顯著升高。血清抗肝腎微粒體-1(LKM1)檢測陽性結果也可能使接受IFN-α治療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更容易發生AITD。α-干擾素治療后繼發性TAAb陽性的發生率從1.9%到40.0%不等。除了免疫介導的甲狀腺功能障礙外,值得注意的是在IFN-α治療期間,約50%患有甲狀腺功能障礙的患者卻未檢測到TAAb。這一發現表明了IFN-α可能對甲狀腺細胞有直接的毒性作用,而并無免疫因素的參與。臨床上,還有兩種非免疫因素的甲狀腺炎即破壞性甲狀腺炎[27]和非自身免疫性甲狀腺功能減退癥[28],由于并未涉及本文闡述的內容,故不在此贅述。
IFN-α誘導的甲狀腺炎是接受IFN-α治療的患者的主要臨床問題,例如甲狀腺毒癥之類的并發癥尤其嚴重。如果患者不經常進行TSH和fT4水平的篩查[29],甲狀腺功能異常的癥狀很容易被誤認為是抗病毒治療的不良反應。IFN-α撤出治療后AITD的可逆性是有爭議的。最初,由IFN-α誘導的甲狀腺疾病被描述為可逆的[30]。后來證明,在超過三分之一的治療患者中,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可能會持續存在。雖然已經證明Graves氏甲狀腺毒癥可能不會在IFN-α撤出后逆轉,但最近一組研究表明CHC患者在基于IFN-α治療過程中出現的甲狀腺炎,治療后病情均有所恢復。中止IFN-α治療6個月后也觀察到遲發的甲狀腺功能障礙。也許監測甲狀腺疾病可以在隨訪癥狀消失6個月后停止,這剛好與檢測SVR 相一致[31]。
2.3 治療方案的調整 據研究,α-干擾素治療不會加重先前存在的甲狀腺疾病。盡管在干擾素治療前已經在應用治療甲狀腺疾病的藥物,患者在抗病毒治療過程中可能需要增加先前應用的藥物劑量,但IFN-α治療完成后,劑量可減少。發生甲狀腺功能減退癥時,應及時進行甲狀腺素治療[32]。橋本氏甲狀腺炎很少成為IFN-α過早終止治療的原因。在有癥狀的甲狀腺毒癥病例,只有在咨詢內分泌學專家之后,才應該考慮拒絕干擾素治療。如果懷疑有甲狀腺毒癥,且TRAb陰性,應對患者進行甲狀腺影像學掃描檢查。應該密切隨訪以便發現新發的甲狀腺功能減退,臨床研究表明這些甲狀腺機能亢進癥患者數周后可能會發生甲狀腺機能減退癥。
無論臨床癥狀如何,所有患者在開始IFN-α治療前都應進行TAAb(TPOAb、TGAb和TRAb)和甲狀腺功能(血清TSH和fT4)篩查。在TAAb陽性患者中,考慮到IFN-α治療的潛在益處和甲狀腺疾病的高風險,必須作出謹慎的選擇。無IFN-α方案可能更適合于這類患者[30]。在無TAAb的患者,在IFN-α治療期間必須系統檢測甲狀腺功能和TAAb是否存在,尤其是女性更應該密切關注,臨床研究表明該病在女性發病率較男性更高[31,32]。
總體來說,自身抗體的檢測在慢性HCV感染個體的隨訪和在確定治療方案的選擇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自身抗體陽性的患者需要仔細考慮應用無IFN-α方案才是可行和安全的方案。可根據血清自身抗體水平決定檢測的時間間隔,以1~3個月檢測一次為妥。但在高位人群,可以考慮縮短檢測時間,以防止遺漏而造成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