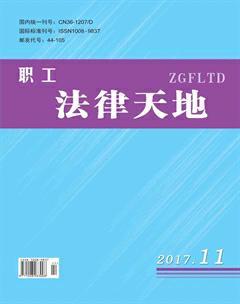淺談法人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類型
姚瑞強(qiáng)
摘 要:對自然人而言,非財(cái)產(chǎn)損害作為與財(cái)產(chǎn)損害相對立的一個(gè)概念,其損害的客體應(yīng)該是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相對立的人身權(quán)。人身權(quán)由人格權(quán)和身份權(quán)構(gòu)成,故對自然人非財(cái)產(chǎn)損害侵犯的客體應(yīng)該是人格權(quán)和身份權(quán)。本文對法人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作了類型化的整理,并希望能對司法實(shí)踐中確立法人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制度有所裨益。
關(guān)鍵詞:非財(cái)產(chǎn)損害;精神損害;法人人格權(quán);類型化
一、關(guān)于法人是否存在非財(cái)產(chǎn)損害
損害賠償法上所謂的損害可分為財(cái)產(chǎn)上損害與非財(cái)產(chǎn)上損害,也有人稱為物質(zhì)損害與精神損害。財(cái)產(chǎn)上損害是指于賠償權(quán)利人財(cái)產(chǎn)上所發(fā)生的損害,凡一切財(cái)產(chǎn)上不利的變動均屬之,它不但包括財(cái)產(chǎn)的積極減少,亦包括財(cái)產(chǎn)的消極不增加在內(nèi)。與此相對,非財(cái)產(chǎn)上損害是指賠償權(quán)利人財(cái)產(chǎn)外所受的損害。關(guān)于其二者的表述方式,“財(cái)產(chǎn)上損害之用辭比較一致,非財(cái)產(chǎn)上損害之用辭,頗為多樣。例如,德國民法使用的是“非財(cái)產(chǎn)上的損害”,日本民法使用的是“財(cái)產(chǎn)以外的損害”,瑞士民法典在對人格權(quán)受侵害的訴權(quán)作規(guī)定時(shí)使用了“撫慰金”這一術(shù)語,法國民法則籠統(tǒng)的使用”損害“這一概念。與此相對,我國則使用了精神損害這一術(shù)語。曾世雄先生認(rèn)為,對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shù)奶接憫?yīng)以全部構(gòu)架為重,過分強(qiáng)調(diào)個(gè)別辭義對于全部構(gòu)架之剖析未必有益,所以不必過于拘泥于辭句,以免因辭害義。筆者對曾先生的看法深表贊同,究其實(shí)質(zhì)而言,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與精神損害都是相對于財(cái)產(chǎn)損害而言的,二者雖然用詞不同但其內(nèi)涵與外延卻基本相同,所以區(qū)別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與精神損害賠償并無任何實(shí)益。但“精神損害”這個(gè)詞容易產(chǎn)生哲學(xué)上“精神”與“物質(zhì)”二元對立的觀念,進(jìn)而認(rèn)為與精神損害相對應(yīng)的就是“物質(zhì)損害”,所以為了防止誤解,在本文中筆者采用“非財(cái)產(chǎn)損害”這一概念進(jìn)行論述。
綜上所述,狹義說認(rèn)為法人是沒有精神痛苦的,因而不存在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shù)膯栴}。廣義說認(rèn)為法人雖無精神痛苦,但因?yàn)榇嬖谥窭娴膿p失,所以也存在著非財(cái)產(chǎn)損害。實(shí)際上,狹義說是用生物學(xué)的觀點(diǎn)來理解法律上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的概念,錯(cuò)把生物學(xué)上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與法律上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混為一談。相比之下,廣義說對非財(cái)產(chǎn)損害的內(nèi)涵的界定更為準(zhǔn)確和科學(xué),并且從理論上和實(shí)務(wù)上都擴(kuò)大了非財(cái)產(chǎn)損害的賠償范圍,允許法人請求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這更加符合現(xiàn)代侵權(quán)行為法的發(fā)展趨勢,因此應(yīng)當(dāng)為我們所接受。
二、法人非財(cái)產(chǎn)損害的類型化
1.侵害法人一般人格權(quán)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
我國臺灣學(xué)者王澤鑒先生認(rèn)為:“所謂人格權(quán),指一般人格權(quán)而言,即關(guān)于人的價(jià)值與尊嚴(yán)的權(quán)利,性質(zhì)上是一種母權(quán),衍生出了個(gè)別人格權(quán)。”由此可見,一般人格權(quán)處于一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與具體人格權(quán)相比,具有主體的普遍性、權(quán)利客體的高度概括性、權(quán)利內(nèi)容的廣泛性和權(quán)利性質(zhì)的基本性。最初設(shè)立一般人格權(quán)的《瑞士民法典》第28條,性質(zhì)上即為一種一般條款,發(fā)揮著一般條款的制度功能。而法人的一般人格權(quán)是法人作為民事權(quán)利主體所享有的人格不受侵犯的權(quán)利,是以與法人的財(cái)產(chǎn)利益相對應(yīng)的法人人格利益為基礎(chǔ),與法人人格權(quán)密不可分的權(quán)利。法人的一般人格權(quán)起到保證法人作為民事主體在民商事交往中享有的法人人格獨(dú)立及法人人格平等的作用,因此是首先需要保護(hù)的客體。在當(dāng)今社會中,法律對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呈現(xiàn)出不斷擴(kuò)張的趨勢,具體體現(xiàn)為:①人格權(quán)越來越受立法者的保護(hù)。②人格權(quán)的范圍不斷擴(kuò)大。③法律對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越來越周密。這種變遷從法律對一般人格權(quán)內(nèi)涵的不斷擴(kuò)張?bào)w現(xiàn)出來,例如德國以前僅就具體人格權(quán)進(jìn)行保護(hù),后來通過司法判例解釋目的性擴(kuò)張了對一般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并且通過判例不斷擴(kuò)大了非財(cái)產(chǎn)損害的范圍。
2.侵害法人具體人格權(quán)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
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發(fā)展,法人的商號權(quán)、商譽(yù)權(quán)、信用權(quán)、商業(yè)秘密權(quán)等對法人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發(fā)揮著越來越重大的作用,在這些權(quán)利受到侵害時(shí),法人可以請求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
3.侵害法人商號權(quán)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
商號是商品生產(chǎn)者或經(jīng)營者,為了表明不同于他人的特征而在營業(yè)中使用的專屬名稱,即商號主體在商事交易中為法律行為時(shí),用以署名、或讓其代理人使用,與他人進(jìn)行商事交往的名稱。商號維系和反映商事主體的商業(yè)信譽(yù),其本身有著重要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是商事主體的一項(xiàng)重要無形財(cái)產(chǎn)。同時(shí),商號是商事主體在營業(yè)上用于區(qū)別其他商事主體的特定名稱,是其主體資格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因而它具有重要的識別價(jià)值,使商事主體特定化和人格化。商號權(quán)與商事主體的人身是不可分離的,它總是特定的商品生產(chǎn)者或經(jīng)營者聯(lián)系在一起,離開了特定的商品生產(chǎn)者或經(jīng)營者,就無所謂商號權(quán)。所以,商號權(quán)與商標(biāo)權(quán)和專利權(quán)相比更具人格性。在商號的創(chuàng)制過程中,商事主體通常要花費(fèi)相當(dāng)長時(shí)間和巨大的精力去刻意創(chuàng)造一個(gè)能反映其營業(yè)特點(diǎn)和文化理念的商號。所以,在商事主體的商號權(quán)受到他人侵害后,其所遭受的不僅僅是一種財(cái)產(chǎn)上的損害,更重要的是對商號中所包含的商事主體的人格利益的侵害。此時(shí),賦予商事主體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請求權(quán)則是理所當(dāng)然的。
4.侵害法人商譽(yù)權(quán)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
同自然人享有名譽(yù)權(quán)一樣,法人也擁有自己的名譽(yù)權(quán),只不過法人的名譽(yù)權(quán)更多的體現(xiàn)為社會對法人從事經(jīng)營活動的商品信譽(yù)和商業(yè)信譽(yù)的反映和評價(jià),因此有學(xué)者主張對法人應(yīng)當(dāng)采用商譽(yù)權(quán)保護(hù)制度,并采取對法人商譽(yù)的誹謗訴訟制度以及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有關(guān)制度加以保護(hù)。筆者認(rèn)為,對于法人商譽(yù)權(quán)的保護(hù)除了采用上述學(xué)者主張的措施外,還應(yīng)當(dāng)賦予法人以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請求權(quán),因?yàn)樯套u(yù)權(quán)作為法人在市場經(jīng)濟(jì)中享有的商品信譽(yù)和商業(yè)信譽(yù),其形成往往經(jīng)歷了一個(gè)漫長的過程,其中也凝結(jié)了法人及其全體工作人員的大量心血。這時(shí),法人的商譽(yù)權(quán)不僅僅是一種具有財(cái)產(chǎn)內(nèi)容的權(quán)利,而且也是一種具有人身性質(zhì)的權(quán)利,是法人一項(xiàng)重要的人格權(quán),此時(shí)如果有人侵害了法人的商譽(yù)權(quán),使其多年來苦心經(jīng)營的良好商業(yè)信譽(yù)毀于一旦時(shí),很難說此時(shí)法人遭受的僅僅是一種財(cái)產(chǎn)上的損害,所以賦予法人以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請求權(quán)就顯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xiàn):
[1]王兆娜.侵權(quán)法上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制度研究.學(xué)位論文.民商法學(xué).山東大學(xué),2012.
[2]孫宏濤,陰悅.試論法人的非財(cái)產(chǎn)損害賠償[J].《煙臺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3年4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