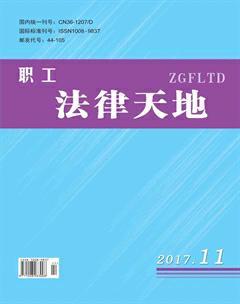論盜竊罪的行為方式
林志釵
摘 要:盜竊罪,一種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到的犯罪形式,一種被許多國家的刑法列為財產犯罪之首的犯罪類型。在我國現行刑法財產犯罪一章中,對盜竊罪的規定次序僅次于搶劫罪,這直接的體現了我國刑法對盜竊罪的重視,從側面上也反映出了盜竊罪在我國發案頻繁。盜竊罪在我國刑法學界也備受關注,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盜竊罪的犯罪形式不斷增加。筆者將借本文對盜竊罪的行為方式進行簡單的探討,希望能對我國的司法事業有所裨益。
關鍵詞:盜竊罪;行為方式;秘密竊取
一、盜竊罪的概念
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是這樣描述盜竊罪的,“盜竊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竊取他人占有的數額較大的財物,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行為。”另外,我國法學界也有學者對盜竊罪做出如下定義:所謂盜竊,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被害人的意志,采取非暴力的平和手段,將他人占有的公私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為。①與通說的定義相比,后者較為注重從盜竊的內涵及行為結構的角度入手,而前者較為注重盜竊罪的外延與犯罪類型。就筆者而言,更加偏向于后者對盜竊罪的定義,因為隨著社會的不斷變化,從外延這一角度對盜竊罪進行定義可能并不周延而導致或有疏漏,所以從犯罪的內涵入手對其作出概括更為適宜。
二、盜竊罪的行為方式
(一)轉移占有必須是通過平和手段
轉移占有的手段無非有兩個,一個是通過平和的手段進行轉移,一個則是通過非平和的手段(也可稱之為暴力手段)進行轉移,而盜竊罪的構成則必須是通過平和的方式來完成占有的轉移。日本著名法學家前田雅英認為,如果行為超出了單純的“為了轉移占有所必需的物理力”,當行為中的暴力與脅迫成分對身體、生命、自由的危險達到一定程度以上時,便不能將該行為認定為竊取。所謂平和手段,是指手段不能對人身具有暴力或者脅迫的性質。當然,非常輕微的暴力可以視為平和手段。例如,某甲在火車上看見坐在對面的某乙睡著了,手里握著手機,于是走到跟前輕輕的用木棍敲打乙的手背,乙出于反射性而松手,甲拿起手機迅速離開,甲的輕微暴力手段可以評價為平和手段,甲構成盜竊罪。
(二)盜竊手段并不要求必須具有秘密性
對于盜竊罪的手段是否要求秘密性,現行刑法并未明確做出具體的規定,只是簡單的陳述為“盜取公私財物”。在相關刑法條文以及司法解釋中,有將盜竊罪與“秘密竊取”聯系在一起的表述,但將該表述究竟是作為成立盜竊罪的一種必要條件,還是作為盜竊罪的常見情形,刑法學界與司法實踐界存在較大分歧。通說對“秘密竊取”的定義如下:指行為人采取隱蔽的、自認為不被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所發現的方法將財物取走的行為。
然而,張明楷教授、周光權教授等學者則對盜竊“秘密竊取說”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盜竊手段并不要求具有秘密性,公開盜竊也可以構成盜竊罪,秘密性只是盜竊罪的常見形式,但常見形式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盜竊罪類型都是這樣,秘密竊取并不是盜竊罪的必要條件。②他們在傳統觀點的基礎之上對盜竊罪進行了重新的定義,并對“竊取”的內涵進行了重新構筑,以平和手段替代秘密竊取,可謂之為“平和手段說”。
在筆者看來,相較于“秘密竊取說”,“平和手段說”可以將秘密竊取與公然竊取這兩種情形均包含在內,能夠較好的實現不放縱犯罪這一目的,具有更強的適用性,有利于更好的維護公平與正義,因此筆者比較認同“平和手段說”。
首先,從犯罪對象來看,搶奪罪的犯罪對象僅包含有體物,而盜竊罪的犯罪對象除了有體物外,還包括無體物與財產性收益。若采取“秘密竊取說”,那么公然竊取他人占有的無體物與財產性收益,則既不能定盜竊罪,也不能定搶奪罪,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若是采取平和手段說,則不存在這一問題,因為行為人無法對無體物與財產性收益使用暴力,從而也就不能構成搶奪罪,但卻因其采取的是平和手段可以對其處以盜竊罪。在這類案件中,平和手段說比秘密竊取說更加能被公眾所能接受。
其次,對盜竊進行文理解釋的話,將盜竊分為秘密竊取與公然盜竊,也是不存在疑問的。在我國古代刑法理論中,盜竊是包括公然盜取和秘密竊取這兩種形式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公眾將公然竊取當做盜竊對待的案例也不少見。筆者認為:“秘密竊取說”作為一種先前的解釋,曾經對我國的法治事業的進步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新形勢的變化與發展,“平和手段說”更加符合時代的需求,法律解釋者應該做出符合時代的解釋結論。
再次,從司法實踐來看,公然平和的盜取他人占有的公私財物的情形并不少見。這類情形既不具有對物和人的強力(或暴力)性質,也不是通過詐騙手段使人們基于錯誤的認識而處分自己所占有的財物,因此對該類行為不宜以搶奪罪、搶劫罪和詐騙罪論處。對于這類行為,應當歸入盜竊罪,否則會有放縱犯罪的可能,將其排除在犯罪之外,很明顯與立法精神相悖。再者說,當今國外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中,大多數國家也并沒有將秘密竊取作為成立盜竊罪的必要條件。
筆者認為,公開竊取說的推廣與應用,不僅符合我國財產性犯罪的理論架構,而且可以彌補傳統盜竊罪在主客觀不一致時采用主觀主義的缺陷,有利于打擊犯罪,能夠更好地將新出現的盜竊犯罪類型覆蓋到整個盜竊罪的體系中來,值得推廣。公然的采取平和手段進行盜竊的行為符合公開盜竊理論,應當定盜竊罪。為了減少在司法實踐中出現因為司法人員對此類行為的認識不同而導致同行為卻不同罪的現象,筆者建議,我國應及時立法將“公然平和取得他人財物”這一行為明確規定為盜竊罪。
三、結語
盜竊罪作為社會生活中最常見的犯罪,與人們的生產及生活息息相關。從古到今,世界各國從未有停止過對盜竊行為的打擊,各國各地區的刑法對盜竊罪的認識也在不斷拓展與深化。隨著社會的發展,盜竊罪的犯罪形式與犯罪類型不斷發生變化、翻樣出新,犯罪對象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展。面對新出現的更加復雜的情形,我們不敢膽怯,有必要對盜竊罪的相關問題作出更加深入到研究。筆者真切的希望自己的一些粗淺的觀點與建議能夠為我國的法治建設盡到一些微薄的力量。
注:
①張明楷.盜竊罪的新課題.政治與法律,2011(8).
②張明楷.刑法學.第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77.
參考文獻:
[1]張明楷.盜竊罪的新課題.政治與法律,2011(8):3.
[2]張明楷.刑法學.第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77.
[3]汪世濤.論“平和手段”下公然取財的行為定性.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11(4)
[4]柏浪濤.刑法攻略(上編).第1版.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206-20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