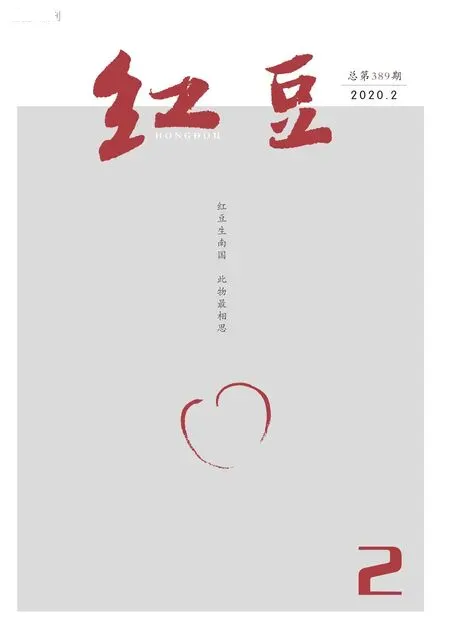一條街上的一百種故事
劉鵬艷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篇好小說,大抵要費這樣的功夫。兩萬四五千字的《午月光》,從一個夏天寫到另一個夏天,且不論它好與不好,這功夫算是夯下了,我對得起我的懶惰與笨拙。在我生活的這座城市,大街小巷如蛛網般密布,我行走了數十年,也還沒有走遍它的每一個角落,但我卻生出這樣的野心,要憑借一條街,寫出所有的悲歡離合。管窺人生而得其全意,是寫作者頗為一致的虛妄念頭吧。憑什么一葉知秋?憑什么俯瞰大地?不過是盲人摸象。然而我想這樣執著地摸下去,未必比發明一款某某神器更可笑些。我們都是有專利的人,創造著屬于自己夢想中的物事。
于是在紙上辟出這條叫銀屏的小街,不必寬闊,不必繁華,卻必定載滿了家長里短的溫暖和物換星移的滄桑。這里,曾于二〇一六年上演過《月城春》的故事,《紅豆》是它的良媒,使很多朋友認識了它;今天的《午月光》,也是發生在這條街上,仍由《紅豆》做媒,介紹給讀者朋友,我非常珍視這段不尋常的緣分,也感謝《紅豆》的支持和厚愛。
寒來暑往,日月更迭,一條街上演一百種故事。這些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帶著尋常人家的煙火氣和三十七攝氏度的體溫。每一次我走過自己虛構出來的這條街,都感覺像是一場溫情的陷落,墜在文字編織的網中,不能自已地被審美的生活所感動。我寫出的是文字,流淌的卻是生活,在那條被日常經驗裹挾然而充滿藝術趣味的街道上,處處都是勃勃的生機:《月城春》里的一對乞兒能夠雍容地面對邊緣人生;《蘇幕遮》里的無賴可以憑借畸形的軀體演繹生存的智慧;《鵲橋仙》里高位截癱的少女擁有最美麗也最憂傷的春夢……這些都是生活的底色,因為披上了文學的外衣,平凡的故事都變成了不平凡的傳奇。如果說銀屏街是一條珠串的話,這些故事就是珠串上的顆顆珍珠。它們在我手中從無到有,我希望每一粒故事的核——那些被不幸揉進體內的沙礫,都能夠有價值地生長,最終珠圓玉潤,熠熠生輝,照亮朋友們的心房。
《午月光》是一個由創傷經驗包裹的倫理故事,寫命運的無常和叵測,也寫生命的疼痛和療愈。中學生冼少白和涂若緹為了療傷,各自劃開了生命的另一道傷口。孩子們的習得性無助,是從父母那里耳濡目染而來的,如果涂若緹沒有打掉那個尚未成形的胎兒,誰將為小生命成長的代價埋單,一如冼少白和涂若緹在成長道路上付出的慘痛代價?這是一個并非特例的惡性循環,每個人都在尋找罪魁,結果罪魁往往成為代際的傳幫帶。我們需要正視的是:就算孩子是父母的影子,然而當父母成為過去,親愛的孩子,你是否有勇氣憑借自己的力量走出陰影,走向陽光?
小姨冼翠是另一種憂傷的表達,她的前半生都祭獻給了虛無的愛情。這個柔弱的小女人渾身散發著溫良的光澤,如美玉雕琢的圣母,卻將自己蠻橫地囚禁在荊棘鋪就的心坎內,始終邁不出幸福的步子。責備她是不道德的,我們尊重生命的多樣性,亦尊重生命多樣性帶來的每一種感性選擇。歸根結底,生活除了雞毛蒜皮,還有磕磕碰碰,那些淤青和傷口,不得不由時間來消化。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傷,陳舊在光陰里,隨著它的纖維化,有人放手了,有人還不甘心,不停地給自己做手術,不愿它安靜地變成心口上的一道增生。結果是,不能放過自己的,往往失去整個世界。我喜歡心理學的一個術語——“悅納”,從表面意思來看,似乎很好理解,就是心懷喜悅地接納;然而落實到具體的對象,卻很不容易做到。做不到心懷喜悅地接納臉上的一粒痦子,做不到心懷喜悅地接納一個有缺點的孩子,當然更加無法心懷喜悅地接納人生當中突兀橫陳的悲劇。《午月光》里的人物,多少都有點擰巴,和現實中的我們相距未遠,不過是對象、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因為擰巴,所以無法悅納,內心與世界充滿了緊張的對抗,連時間也無法消弭,以至于悲劇性似乎都有了某種縱深的宿命感。銀屏街是一個歷時性的舞臺,一系列生活秀在這里自娛自樂地上演。在這條街上,生活即小說,小說即表達,“他們”可能是鄰居,是同學,是朋友,是我們自己,生命里必然經驗的那些傷痛,我們都有,或者最終都會有,如何成全,視乎自身。
再次走在這條街上,綠樹已然成蔭,風景舊曾諳,心境卻大不相同。每一次虛構,都讓我的內心經歷一次風暴,那些向我走來的熟悉的面孔,那些并不陌生的生命體驗,潮涌般沖撞著我情感的堤防,于無聲處滄海橫流。寫作似乎讓我活得更明白,有種歷劫后飛升上仙的快感。但我以為的人生的悟語,也許只是一種誤語。
銀屏街上的悲歡離合,是生活,也是藝術,希望它能夠給您帶去一點心動、一點感動。
責任編輯 李國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