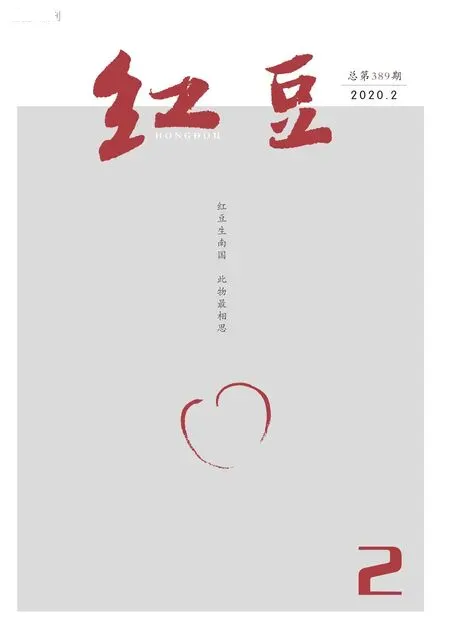劉公微篇小說二題
劉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陜西文學院簽約作家,在《小說選刊》《文藝報》等發表作品300多萬字。多篇獲獎。作品入選中學、大學語文教材及國家權威圖書《中國新文學大系》《百年百部微型小說經典》《微型小說鑒賞辭典》《小小說作家辭典》《當代小小說名家珍藏》等,并被翻譯到加拿大、美國、土耳其等國家。主編有《中國精短小說名家經典》(上下卷)、《陜西省小小說20年精選》等多部。
瀟灑的老寬
老寬是吃皇糧的,一副小眼鏡架在他寬大的臉龐上,很有點滑稽。他認為言多必有失,平時不太說話,給人的印象是,眼鏡片后面充滿智慧。當科員時,早晚去他辦公室,他都在。前年當了科長后,十次去他辦公室,九次半他都不在。一問,科室的人回答,都是到某某單位去了。
老寬以前就一個愛好,打麻將,每次就帶一二十塊錢,不到一圈就繳械投降了,只得眼巴巴地坐在一旁看別人打,過干癮。后來,大家嫌他腰包癟,沒人愿意跟他打了。他也不計較,照樣去,誰內急,憋不住了上趟廁所,他趕緊頂上一把。大家曾笑話他,給他取了個綽號“不敢打”。
沒想到,過了幾年,也就是從前年開始吧,老寬由棋牌旁觀者,一下子變成了參與者。大家幾塊錢的玩耍,被他戲稱為小兒科。起步少于二十元,他不上場。有一次,幾個人提前商量好,給老寬“抬轎子”,三個多小時,老寬掏了三萬多元。這要是在以前,老寬非提刀子跟幾個人拼命不可。這次,老寬只是淡淡一笑,跟沒事兒一樣,此后就再沒人叫他“不敢打”了。
老寬的愛好,從去年開始,增加了不少。唱歌、跳舞、泡腳、桑拿、喝茶等等,樣樣都能來,且大多在上班時間進行。他把這些叫做聯系群眾,與單位溝通,就連省里通知的一般會議,凡是不痛不癢的那些會,他一律安排管轄單位派人替他去。他最贊成的是全市開展創文和創衛活動,這些活動都賦予他的科室一些權力。權力是什么?權力就是資源,權力就是財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吃喝玩樂,經營得風生水起。
在企業上班的老婆看不過去了,說他:“你看其他的科長,兢兢業業的,把工作當工作,哪一個像你,吊兒郎當的,成天不務正業,連班都不坐。”
老寬臉一沉,眼睛一翻:“婆娘家的,懂個屁!科員靠干,科長靠看。看,就是看領導的眼色,看住下屬好好替你工作。那些看似天天坐在辦公室,兢兢業業的,實際上是沒水平。”
“你不要自我感覺良好,到時候別的科長都上‘縣了,你還在原地踏步,你就后悔了。”
老寬不屑地“哼”了一聲:“你敢跟我打賭不?老婆你看著,兩年內,是我原地踏步,還是他們原地踏步。別看我經常不在辦公室,可我匯報、請示工作,比他們哪個都勤快。”
“你看人家孟科長,到哪個科室,都把科室抓得井井有條,年齡比你還小一歲,這次有一個指標的機會,就會是人家。”
“放心吧,領導啥時候都會重用有眼色的聽話人。眼色是什么?眼色就是會看、會干、會撈、會送,把事情做到點子上。記住,有撈才有獲,有禮才會往來。”
老婆辯不過,便偃旗息鼓,提著包上班去了。
老寬“看”的本領,一般人望塵莫及。有首歌里唱,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學問。老寬研究得很深,重點是上看,其他方向也不敢馬虎,考察、測評,方方面面都得想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前不久的縣級干部調整,程序非常嚴格,組織部明察暗訪,個人述職、無記名問卷、個別談話、領導推薦等等,環節一個接一個。不少科長如臨大敵,緊張得坐立不安。而老寬,只是抿嘴一笑,覺得是走走過場的事。他經歷官場多了,掂得清孰輕孰重,知道該做些啥。
上月公示縣級干部提升對象,老寬的名字不但在其中,而且遙遙領先他人,不少人心里不服,但只是存在心里,就連老寬的老婆,都有點迷惑不解。
上周三,老寬走馬上任到一個縣級單位,他老婆給他整了一桌菜,夫妻倆喝得紅光滿面,老寬問:“老婆,打賭我贏了,你服不服?”老婆拱進老寬的懷里,撒著嬌說:“服,老婆不但心服口服,還外帶佩服哩。”
這個老寬,還真是個“人才”。不過,最近風向標有些變化,瀟灑的老寬再不敢溜號了。
最痛恨的就是戰爭
丁一和丁二是親親的弟兄倆。
丁一被抓壯丁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由于天生的視力好,很快成了神槍手,在對付小鬼子那些鏖戰的日子,不少日本兵倒在他的槍下。日本投降后,他的槍口轉向了人民解放軍,特別是在雙方對峙的情況下,他的狙擊步槍有很強的殺傷力。
丁二是十六歲主動報名參加的八路軍。新兵訓練時,領導發現他槍法特別準,就有意培養他為狙擊手。他刻苦訓練,不負眾望,很快在戰場上顯出了神威。平型關戰役中,他的子彈擊斃了一名日本中隊長,榮立一等戰功。解放軍南下時,在一次戰斗中,他所在的部隊與國民黨軍隊都互攻不下,對峙期間,雙方的狙擊手都頻頻出手。
兩天的拼殺,狙擊手之間的較量一刻都沒有停止。最后,對峙的雙方各剩下一名阻擊手。狙擊手的博弈,除了視力和槍法以外,還有智慧和膽量的比拼。
丁一身經百戰,有豐富的作戰經驗。丁二雖說小丁一五歲,但多次戰斗的洗禮,絲毫不亞于丁一。二人借助草木和土堆的掩護,打得難分難解,都想把對方置于死地,但都難以實現。耗到最后,丁一只剩下一發子彈,他明白這顆子彈的重要性。
丁二見對方好一會兒沒有動靜,摸摸槍機,輕輕拉開槍栓窺望,也只剩下了一發子彈。丁二心里清楚,這最后一發子彈意味著什么。
對峙中,天空飄起了小雨,雨蒙蒙的,有霧,雙方的視線都受到了影響。丁二試圖繞到丁一的側面,給丁一致命的打擊。丁一發現了丁二的意圖,躍起往一棵樹后迂回。恰在此時,丁二的槍響了,丁一躍起的身體,像一片秋后的樹葉,在雨中閃了一下,跌落在地。憑經驗,丁二知道丁一中彈了,但是否斃命,不得而知。丁二小心翼翼地匍匐到丁一十多米遠的地方,觀察了幾分鐘,見對方紋絲不動,才慢慢靠過去。當他翻起對方的尸體,發現這個對方就是自己的哥哥丁一時,一下子懵了,隨后跪下號啕大哭:“哥啊!你是有兒子的人,我是一個單身漢,應該死的是我,而不是你啊……”
雨在下,人在哭。
不知過了多久,雨終于停了,丁二抱著丁一的尸體,抽泣得肩膀一聳一聳的,哥哥的鮮血浸染了他一身。
他緩緩站了起來,握著哥哥的槍,對準自己的腿,用力扣動了扳機。
后來,雖經后方醫院全力治療,他的腿還是落下了一瘸一拐的殘疾。
戰后,他要求回到了家鄉,承擔了撫養侄子的一切義務,直到把侄子供到成家立業。
后來,滿頭銀發的丁二,直到六十多歲,才和鄰村的王寡婦搭伙過日子,這輩子也算成家了。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時,有媒體采訪他,他雖已臥床不起,但提起那場戰爭,他立馬老淚縱橫。采訪結束時,他緊緊抓住記者的手,嘴唇翕動了半天,才說:“我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就是戰爭!”
責任編輯 藍雅萍
特邀編輯 張 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