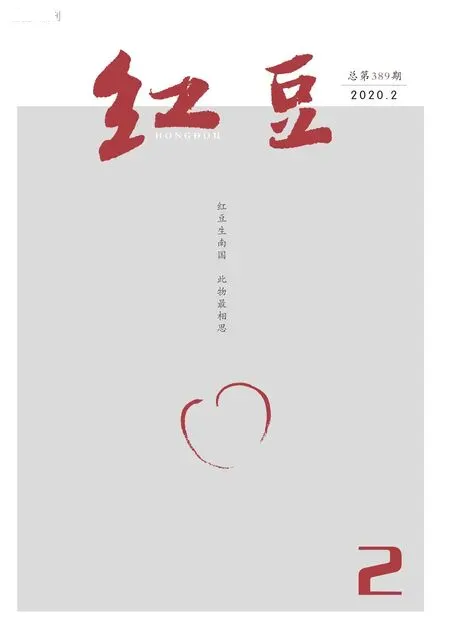魯迅二題
王張應,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安徽金融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在《詩刊》《清明》《莽原》《安徽文學》《飛天》《鴨綠江》《散文選刊》等刊發(fā)表中短篇小說、散文等近200萬字,出版詩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說集多部。
月兒本屬夜晚
魯迅“罵功”非常了得,亦如他文章著名,讓人長了記性。
魯迅開罵,是看對象的。對于青年,尤其對文學青年,即便不快,也不輕易開腔。在青年的眼里,魯迅是民國文壇領袖,也是青年領袖。
有段時間,魯迅對高仰愈這位青年實在忍無可忍,不得不做了他素來不愿意做的事情——對高仰愈開了罵口。高仰愈是一位很有才華,很有闖勁的青年作家,筆名長虹,人稱高長虹,山西盂縣人,小魯迅17歲。高長虹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學讀書時各門功課俱佳,尤其國文和英語突出。后因故逃學在外,一門心思自學文學,博覽群書,練習寫作,從而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1924年9月在太原創(chuàng)辦《狂飆》月刊,名聲大噪,引起了魯迅的注意。
1924年底,高長虹創(chuàng)辦的《狂飆》雜志在太原出到第三期便難以為繼。困境中的高長虹,來北京尋求援助,得到了當時以“贊助真實立憲,提倡愛國精神”為宗旨的《國風日報》的幫助,將《狂飆》以《國風日報》副刊名義在北京繼續(xù)出版。來北京不久,高長虹從《京報》副刊孫伏園處得知,魯迅對《狂飆》評價很好。由于魯迅的好評,郁達夫等魯迅身邊一批知名作家也對《狂飆》十分認可。這讓高長虹十分興奮,他似乎于暗室中從門縫里看到了一絲亮光。高長虹頓時心生感激,決定上門拜訪魯迅。高長虹攜著一股無羈的“狂飆”勁頭,敲開了魯迅的家門,闖進了魯迅的私人領地。后來,高長虹在回憶錄里如此記載:“在一個大風的晚上,我?guī)Я藥追荨犊耧j》,初次去訪魯迅。這次魯迅的精神特別奮發(fā),態(tài)度特別誠懇,言談特別坦率……我走時魯迅謂我可常來談談。”此后一段時間里,高長虹往魯迅家里跑得很勤。正如魯迅后來所形容的,川流不息。
到次年3月,高長虹的《狂飆》終于生機殆盡,再也撐不下去了,只得走向死亡——停刊。4月的一天,魯迅邀了高長虹、向培良、章衣萍等來家里共飲,席間商定創(chuàng)辦《莽原》周刊。合辦《莽原》周刊期間,高長虹已經(jīng)成為魯迅家里的常客。共同的心愿,共同的使命,讓魯迅和高長虹走得很近,關(guān)系特別親密。可是,8月以后,高長虹到魯迅家里的次數(shù)明顯減少。驟然大降溫,總是讓人感覺不對頭,不適應。魯迅那般聰敏的人,對于高長虹的變化,當然有所察覺。只是,魯迅一時還沒弄明白究竟原因何在。
當初,魯迅之所以看上高長虹,是因為他身上那種“狂飆突進”的精神,那股“準備毀壞”的勁頭。魯迅沒想到高長虹那股“飚”勁,有朝一日竟會對準了自己發(fā)作起來。
1925年8月的一天,《民報》上刊出了一則廣告,其中有尊稱魯迅為“中國思想界之權(quán)威”的說法,這讓高長虹很不爽。也許,真的是距離產(chǎn)生美,彼此貼得太近了,則難以發(fā)現(xiàn)原本的美。正如一句民間俗語所說“九華山的菩薩應遠不應近”。報上對于魯迅那種尊崇,讓高長虹覺得過分,他無法接受。那時的高長虹還很“稚嫩”。其實,高長虹一生沒有老道過。他心上根本擱不住事,心里有了什么臉上立刻就有什么。即便嘴上還沒說出,行動上卻先表現(xiàn)出來了。最明顯之處是高長虹疏遠了魯迅,去魯迅家少了。生性敏感、疑心很重的魯迅,不會意識不到。魯迅不動聲色,依舊開口便是“長虹”,心中疙瘩卻已悄悄結(jié)成。
1925年夏天,高長虹和魯迅先后離開北京。魯迅應林語堂之邀,經(jīng)由上海到了廈門大學。高長虹則是先期去了上海,他想“借尸還魂”,讓他的《狂飆》在上海起死回生。《莽原》刊物兩個主要人物都離開北京,編務工作暫由魯迅學生韋素園負責。
韋素園主持《莽原》編務之后,因退稿得罪了高長虹。高長虹對于韋素園的“獨斷專行”非常氣憤,專門發(fā)表了給魯迅的公開信,希望魯迅能夠主持公道,為他說話,孰知魯迅沒有反應。那時的魯迅正處于熱戀之中,人在廈門大學,心卻飛到廣州了,天天伏案給他“廣平兄”寫著柔情蜜意的“兩地書”。對于高長虹的公開信,魯迅沒給予足夠重視,以為不過是長虹和素園鬧點小意見而已。或許,魯迅像大多數(shù)上司那樣,面對下屬紛爭,多少還有點坐山觀虎斗的小小開心呢。
高長虹向來沉不住氣。這回,他心里有了怨,脾氣一上來,不管不顧了,把一腔怨氣全發(fā)泄到文字上。1925年11月7日,高長虹在上海《狂飆》周刊上發(fā)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矛頭直指魯迅,措辭極為尖刻和不遜。魯迅看到后十分生氣,對高長虹恩斷情絕。至此,魯迅與高長虹的關(guān)系,宣告破裂。魯迅在11月15日致許廣平信中寫道:“長虹在《狂飆》五期上盡力攻擊,自稱見過我不下百回……其意蓋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則推廣《狂飆》銷路,其實還是利用,不過方法不同。他們專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著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殺了煮吃,有如此惡毒。”此時,高長虹在魯迅的眼中,已是一個過河拆橋的小人。高長虹接近魯迅純粹為了一己名利,繼而損害魯迅,同樣為了名利。至于名利之外,魯迅對高長虹沒有想到更多。
所以說,《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的發(fā)表,才是導致高魯關(guān)系徹底破裂的真正原因。
在魯迅表示還要對高長虹細看一下時,高長虹又出新招,繼續(xù)表演。他在《新女性》上登出了“狂飆社廣告”,一反前言,尊稱魯迅為“思想界先驅(qū)者”。高長虹此番用意,路人皆知,如此這般反復,是為了取悅魯迅,跟魯迅套近乎,似乎魯迅對他還有使用價值。魯迅實在看不下去了,好像忘記了高長虹是誰,只知道自己面前出現(xiàn)了一個面目猙獰的新敵。魯迅隨即寫了一篇《所謂“思想界先驅(qū)者”魯迅啟事》,發(fā)表在1926年12月10日《莽原》上。在啟事中,魯迅特別聲明:“我也不是‘思想先驅(qū)者。此等名號,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別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嘗高興。”魯迅文章一經(jīng)發(fā)表,向來反響巨大。這則《所謂“思想界先驅(qū)者”魯迅啟事》刊出后,罵聲一片,高長虹應聲而倒,名譽掃地。之前高長虹對魯迅不合情理的攻擊,本已招致許多人不滿,隨后又出爾反爾登出如此自扇耳光的無恥廣告,更令人不齒。從此,文壇中人無不避諱高長虹,遠之如瘟疫。一心從文的高長虹,失去了在民國文壇的立足之地。endprint
魯迅原以為與高長虹“罵戰(zhàn)”可以休矣,彼此相忘罷了。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偏有人向魯迅打“小報告”說,高長虹的攻擊中,隱藏著事關(guān)戀愛之糾紛。魯迅始猶不信,繼而疑慮,后恍然大悟。前些日子,魯迅總覺得高長虹對他態(tài)度陡然變化,莫名其妙,沒有想到竟是如此。高長虹那只巨大的包裹,在魯迅面前層層剝展開來。
高長虹在對魯迅大肆攻擊后,很快在《狂飆》周刊上發(fā)表兩首愛情詩《給——》,其中一首云: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門徒,
月兒我交給他了,
我交給夜去消受。
夜是陰冷黑暗,
月兒逃出在白天,
只剩著今日的形骸,
失卻了當年的風光。
……
夜是陰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陽,
太陽丟開他走了,
從此再未相見。
詩發(fā)表以后,人們一目了然,私下里議論紛紛。唯魯迅蒙在鼓里,他沒有在意這首詩,更不曾想到這詩竟與他有關(guān)。很快,韋素園把外面議論轉(zhuǎn)告了魯迅:高長虹在詩中以太陽自比,指黑夜為魯迅,而月亮就是許廣平。魯迅知道高長虹以《給——》為題的詩寫得早了,也寫得多,未必真如韋素園君所言。他對韋素園的話,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只半信半疑。魯迅說:“若是真的,則太可惡,使我憤怒。我竟一向悶在葫蘆中,以為罵我只因為《莽原》的事。”
不幸,魯迅的懷疑很快得到證實。高長虹在隨后發(fā)表的《時代的命運》中明確說:“我對于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所謂生活上的讓步,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鮮的溫熱進來!》一文中直接向魯迅宣戰(zhàn):“如狂飆社以直報怨,則魯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將身敗名裂矣!”
真相大白后,魯迅倒吸了一口冷氣。隨即寫信告訴許廣平:“那流言,從韋素園的信里才知道的。……長虹的拼命攻擊我是為了一個女性,《狂飆》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這才明白長虹原在害‘單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這里來的原因,他并不是為《莽原》,卻在等月亮。”魯迅給許廣平寫信,恐怕不光告知情況,可能還有一些試探的意思。
平時再慷慨大度的人,一旦遇上“情敵”,面臨愛情堤壩垮塌的危險,仍慷慨大度,估計很難。何況,愛情這陌生的東西,在魯迅身上屬稀有元素。青年時代,魯迅錯過了,直到中年,老天爺才補償于他,魯迅自然無比珍視。對于高長虹,魯迅一改青年導師形象,顧不上紳士不紳士了,拿起他慣于“痛打落水狗”的棍棒,朝著高長虹打下去。魯迅寫出小說《奔月》和一些雜文,對高長虹進行含沙射影的嘲諷和批駁。在雜文《新時代的放債法》中說:“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么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是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到五體投地。他只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nèi)。”針對高長虹所說的“最大的讓步”和“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魯迅做出了冷嘲熱諷的回擊。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魯迅的自信。魯迅自信得近乎霸道,令人生厭。魯迅全然不顧,足見他當時對這件事多么在乎。
魯迅一生中,有過許多次著名罵戰(zhàn),多為政治而罵,為正義而戰(zhàn)。譬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類名罵,國人皆知,曾經(jīng)影響了后來幾代人。唯有與高長虹這場罵戰(zhàn),與政治無關(guān),甚至不關(guān)正義,純粹為愛情而戰(zhàn)。魯迅貌似輕松,堂而皇之說渴仰他的女性召之即來,他對于身邊的“月兒”,還是如獲至寶,無比看重,攢得很緊。他絕不會輕易放手,更不可能拱手相讓。
其實,面對高長虹有關(guān)“月兒”的言辭,魯迅大可不必光火。高長虹想法太過天真,月兒終是月兒,本屬夜晚,不可能與太陽走到一起。魯迅完全可以做得紳士一些、斯文一點,亦如后來梁思成遇見金岳霖那樣。梁思成欲擒故縱,把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權(quán)交給了林徽因,由林徽因自主選擇,且鼓勵愛妻舍梁取金。如此大度,非但沒失去愛妻,反讓林徽因感激涕零,從此死心塌地。
果真如梁思成那般,魯迅還是魯迅嗎?
煙不離手的魯迅
印象中的魯迅,煙不離手。他右手生來用于握筆,左手呢,似乎天生用于持煙。不握筆時,右手也可能用于持煙。左手或者右手,食指與中指之間那條縫隙里,總夾有一根紙煙。煙的一端火光明滅,煙霧輕繞。
如此印象,來自紙上,多因鋪天蓋地的懷念魯迅的文字而起,也有少許源于珍貴的圖畫和相片。予生也晚,無緣親見魯迅先生尊容。
詩人嗜酒,文人好煙,似乎天經(jīng)地義。詩仙李白斗酒詩百篇的佳話,給后代詩人一條跟酒纏綿的充足的理由。民國時期大文豪魯迅酷愛抽煙,似乎向世人昭示,吸煙催生靈感。兩指夾煙,煙霧繚繞之時,最是文思泉涌。有關(guān)魯迅吸煙的情況,乃至具體細節(jié),當時人印象深刻。民國時期以及后來的作家們保存了大量關(guān)于魯迅吸煙的文字。這些文字給人一種感覺,魯迅必須吸煙,否則,他就不是那個大文豪魯迅了。
寫魯迅吸煙,所見文字中,寫得最多的要算郁達夫和蕭紅。這也正常,郁達夫和蕭紅曾經(jīng)頗受魯迅青睞,和魯迅走得很近。從《魯迅日記》上可以看出,郁達夫和蕭紅到魯迅家去得最多,幾乎可以隨時到訪,自由進出魯迅家門。因而有機會深度接近魯迅生活,對魯迅的生活習性了解更多。
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有大段關(guān)于魯迅吸煙的文字。“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支裝包。”郁達夫?qū)︳斞肝鼰熡∠筇貏e深,十分肯定地說魯迅煙癮大,他還知道魯迅哪段時間里愛吸什么牌子的香煙。
蕭紅關(guān)于魯迅吸煙,寫得更多、更詳細。在《回憶魯迅先生》中,蕭紅多次寫到魯迅吸煙細節(jié)。魯迅在家里工作或者休息,乃至接待客人時,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便是吸煙。夜深了,“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闔一闔眼,燃起一支煙來,躺在床邊上,這一支煙還沒有吸完,……魯迅先生站起來,坐到書桌邊,在那綠色的臺燈下開始寫文章了。”開始工作前,魯迅慣于先吸一根煙,提足精神。好像不吸煙便無法專心工作似的。魯迅家里來客很多,在家接待客人,魯迅除了陪客人說話,便是吸煙。客人亦吸煙,他便同客人一起吸,你一支,我一支。客人不吸煙,魯迅也會自顧自地吸著煙。蕭紅說:“魯迅先生陪客人……從下午兩三點鐘起,陪到夜里十二點,魯迅先生都是不斷地吸著煙。”差不多十個小時陪客時間,魯迅都在不停地吸煙,可想而知魯迅每天吸掉多少煙。日積月累,可謂海量。endprint
愛吸煙的人,大概都煙不離身。一逮到空當,便吸起煙來。魯迅便是這樣。有一回,是在夜里,蕭紅同魯迅、周建人兩家人一起去看電影。“過了蘇州河的大橋去等電車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鐘,電車還沒有來,魯迅先生依著沿蘇州河的鐵欄桿坐在橋邊的石圍上了,并且拿出香煙來,裝上煙嘴,悠然地吸著煙。”等車的空隙,魯迅自然不會放過。坐下來,輕輕松松吸上一根香煙,感到十分愜意。甚至,在飯館吃飯過程中,魯迅也少不了吸煙。蕭紅記得,有一次,魯迅在一家飯館里請客,“菜剛上滿了,魯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煙,并且闔一闔眼睛。一吃完了飯……大家都亂鬧了起來……而魯迅先生這時候,坐在躺椅上,闔著眼睛,讓拿在手上紙煙的煙絲,裊裊地上升著。”
魯迅嗜煙如命。直到最后,才不得不節(jié)煙戒煙。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春天,魯迅病重,臥床不起。那時,蕭紅發(fā)現(xiàn),從前的魯迅,“差不多一刻也不停的吸煙,而今幾乎完全放棄了,紙煙聽子不放在床邊,若想吸一支,是請許先生付給的。”
除了郁達夫和蕭紅,還有許多人在回憶魯迅的文章里,留下了有關(guān)魯迅吸煙的文字。
民國時期曾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的浙江天臺人許杰,與魯迅有過一面之緣。在《回憶我和魯迅的一次見面》里說:“他的一只左手,橫過胸前,托在右臂的脅下,那只右手,卻用兩個指頭夾著香煙,不時的往嘴巴上送,又不時的取下來。”許杰描寫魯迅吸煙的動作神態(tài),十分鮮活,極為傳神。
梁實秋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某天,因上門邀請周作人到清華大學演講,在北京八道灣周家大宅院里,誤闖了魯迅書房,意外與魯迅有過一面之交。后來,梁實秋在《魯迅與我》里回憶說:“那天,在周府,等不大功夫,一位高顴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著一根紙煙走了進來……我道明來意之后,他愕然地問:‘你是要會我的老弟吧?我才知道認錯了人。從他老弟口里,我才知道這人便是魯迅先生。”梁實秋與魯迅的會面,僅此一次,還是誤會。多少年后,一提到魯迅,梁實秋總是首先想起了魯迅指縫里“捏著一根紙煙”。
茅盾在《魯迅論》里,引用了許多人寫魯迅的文字,其中不乏寫魯迅吸煙。如引用馬玨《初次見魯迅先生》中的一段話:“一個瘦瘦的人,又老又古板……他手里老拿著煙卷,好像腦筋里時時刻刻在那兒想什么似的。”馬玨是當年北大教授馬幼漁的女兒。與魯迅初次見面時,她才15歲。以少女天真的目光,去看待魯迅手里的煙卷,很自然,馬玨把魯迅吸煙與動腦筋思考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了。
巴金與魯迅見面不多,記憶中長久地保存了魯迅吸煙之神韻。1956年9月,巴金在《秋夜》里寫道:“……右手兩根手指夾著一支香煙。他深深地吸一口煙,向空中噴著煙霧。”把煙深吸進去,隨后,又輕輕地噴吐出來,那情形該是一種有滋有味的享受。個中滋味,恐怕只有愛吸煙會吸煙的人才能體會得到。
好吸煙的魯迅,視香煙為食糧,向來準備充分,身邊不會斷煙。常備兩種香煙,一種昂貴,一種廉價。昂貴的用來待客,廉價的供自己吸食。魯迅待客熱忱,又愛面子,他不委屈客人,也不讓自己丟面子。至于是否委屈了自己,他從來不計較,魯迅自奉一向很低。關(guān)于魯迅備有兩種香煙之事,郁達夫和蕭紅都有很深的印象,留下了詳細文字。
郁達夫說:“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袍里去摸出一支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后再從煙包里抽出一支,而再將煙包塞回袋里去。”
蕭紅說得直白:“魯迅先生備有兩種紙煙,一種價錢貴的,一種便宜的。便宜的是綠聽子,是魯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種是白聽子的,是前門煙,用來招待客人的,白煙聽放在魯迅先生書桌的抽屜里。而綠聽子的永遠放在書桌上,是魯迅先生隨時吸著的。”孬好兩種香煙,平時都放在哪兒,魯迅是如何用的,蕭紅到魯迅家里去得多了,看得清楚,記得準確。
煙不離手的魯迅,有些時候,有些場合,卻堅決不吸煙。
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的一天,魯迅去西山醫(yī)院探望因病住院的韋素園。會面談了很久,韋素園忽然想起了該讓魯迅吸一根煙。韋素園知道魯迅不能長時間不吸煙。魯迅推讓了好幾次,總是搖頭說:“不吸了。”其實,他心里很想吸煙,為照顧病中的韋素園,他才刻意不吸。韋素園再三申明別人吸煙對他無礙,魯迅這才走出病房,走得遠遠的,站在走廊盡頭吸了一支煙。
還有一次,是在民國二十年(1931年)8月,魯迅在上海舉辦一次木刻講習會。參展學員里,不少人同時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在漫長的觀摩講解過程中,魯迅竟然沒吸一口煙。魯迅擔心吸煙產(chǎn)生煙霧會熏壞現(xiàn)場美術(shù)作品,咬咬牙忍住了,沒在展覽現(xiàn)場吸煙。
依現(xiàn)在眼光看,魯迅當年患肺病過早離開人世,除家族遺傳及個人性格因素外,可能還有生活習慣問題。如魯迅愛熬夜,又嗜煙。家族遺傳因素,并不一定導致魯迅不能長壽。魯迅父親短壽,他患肺病,只活了35歲,母親卻活到了80多歲。兩個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一個活了80多歲,一個活了90多歲。倘若魯迅摒棄了某些不良生活習慣,心態(tài)平和一些,說不定,天假以年,魯迅會活得長久一些。
關(guān)于魯迅吸煙,魯迅的朋友、日本籍醫(yī)生須藤五百三說過,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3月,魯迅體重只剩37公斤。他對魯迅說了應該注意的事項,特別指出吸煙的危害。魯迅并不當回事,說香煙和自己無論如何是離不了的。到后來,魯迅終于減少了吸煙,每天只吸15支。但已無濟于事,沒能挽留、延續(xù)魯迅的生命。
在魯迅生命最后幾年里,由于常給海嬰看病,須藤五百三與魯迅交往密切。魯迅信任須藤五百三,亦讓他給自己治病。作為朋友,尤其醫(yī)者,須藤五百三很自責,沒能及早阻止住魯迅吸煙。
魯迅死后,很長一段時間,須藤五百三心中不安。為魯迅吸煙。
責任編輯 韋毓泉
特邀編輯 張 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