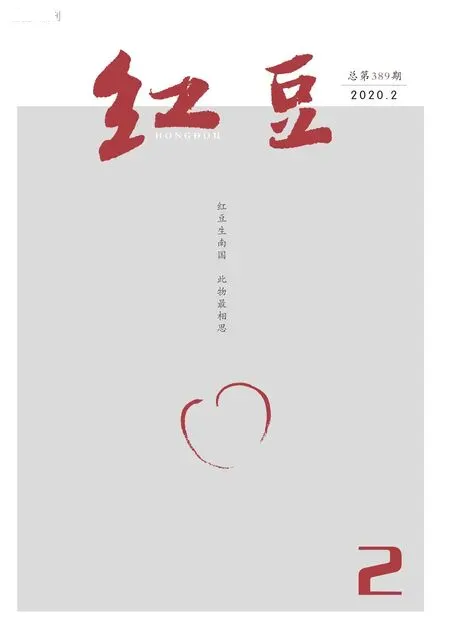我的鄉村紀事
紅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常務副會長,作家、文學評論家。已出版散文、小說、詩歌集10部,散文代表作品有《東渡東渡》《喚聲姐姐叫蕭紅》《女人的荷》等。現供職文化部中國文化報社,主編文藝副刊。
我到鄉政府報到的那天,是1986年的深秋了。
鄉政府所在地是一處古建筑,分前后兩院,一百年前是一張姓祠堂。這姓張的人家祖上在清朝的工部擔任過要職,可能是侍郎那種職務,相當于今天的副部級,主管建筑工程。有人說,張姓祠堂的工料是張(侍郎)在任職時,從給朝廷的某建筑工程中給挪用出來的,也許是清東陵,也許是開灤煤礦。因為沒有明確的記載,也就無法進一步證實,權當以訛傳訛吧。不過,聯想到現實,這種官員假公濟私吃回扣的事也不鮮見。
這都不重要。我到鄉政府擔任的職務是鄉團委副書記,本來說好是來當鄉團委書記的。后來,我從辦公室其他的同事嘴里得知,鄉團委書記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同志兼著,她不僅是鄉團委書記,還兼任黨委辦公室副主任、文化站長、工會干事,之所以要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等轉成城鎮戶口的指標。我的前任,也是鄉團委副書記,他并沒有高升,而是就地免職歸我管。其直接原因是,在幾個月前,他上中學的弟弟跟同學打架吃了虧,回家把他哥叫了去,結果哥哥幫弟弟出了氣,卻把鄉團委副書記給丟了。黨委分管我們的副書記并沒有把這個事情的原委告訴我,是黨委書記在某一天晚上與我一同值班時跟我說的。黨委書記還跟我說,之所以把我從農場調來,就是看中我有幾把刷子,希望我能做好鄉里的宣傳工作。
我們的鄉政府不像其他地區,由區縣政府直接管,而是由農場管轄。農場很有名,名曰雙橋農場,早些時候也叫中古友好人民公社。農場是1948年建的。第一任場長叫李直,傳說當年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他的兒子李銳現在在山西,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等,是個很著名的作家,1969年從楊閘中學畢業后到山西插隊。我在1985年第2期《當代》雜志上曾讀到過他以農場的生活為背景寫的中篇小說《紅房子》。小說中寫的農場東院的紅房子,我曾經在那里工作過一年多。再后來,李銳的名聲越來越大,一度聽說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為此,他還退出了中國作家協會。我一直想跟李銳、蔣韻夫婦聯系,跟他們說說雙橋,聊聊文學。可機緣從未有光臨過。有次打通電話,溝通得不太好,也就作罷。
黨委書記所說的我有幾把刷子,指的是我會寫點文章。1983年中考失敗后,對人生、前途近乎絕望的我,開始學習寫作。在這之前的1976年,我在小學二年級時于三夏收麥時節,曾寫出過“東方升起紅太陽,我們早早起了床。拿起工具上麥場,革命精神大發揚”那樣的戰斗詩,被刊登在學校的三夏戰報上。這大概就屬于我的文學啟蒙吧。我母親斯時在離家附近的農場果園食堂工作。食堂旁邊便是鍋爐房。燒鍋爐的劉師傅愛寫詩,還兼任果園的廣播員。我從小就經常聽劉師傅的廣播,聲音洪亮而有激情。我媽見我整天郁悶,就讓我找劉師傅聊天。我在廣播里聽過劉師傅朗誦過自己創作的詩。我見到劉師傅的時候,他正在鍋爐房的一個角落里用左手寫散文。我看了他的一些詩稿,其中有一首叫《翠柳河》。劉師傅的家距我們的村莊不過五六里路的樣子,我們的北面有一條著名的通惠河。這條河從北京東便門流經通州八里橋的河流,古代是漕運河,現在負責北京東部的排污。從通惠河往南有幾條支渠,我們村西的叫西大渠,劉師傅的家在河西,他們管西大渠叫翠柳河。看來,他們村比我們村有文化,浪漫、抒情得多了。劉師傅四十多歲,身體有些塌軟,說話慢條斯理,跟廣播時的情景一點都不一樣。他在跟我聊天時,隔幾分鐘就往爐膛里扔幾鍬煙煤。去劉師傅那里聊過幾次后,我就將寫的三四首詩歌給他看。劉師傅看過后,說我的起點很高,他輔導不了我。他告訴我,農場機關有幾個熱愛文學的干部經常寫作,他想把我推薦給他們。這樣,我就在很短的時間內,與農場的二十幾位文友相識了。不久,北京市農場局和朝陽區文化館的文學輔導干部先后來農場座談,并向我們這些業余作者約稿。這樣,我在1984年的7月15日,第一次在《北京農場報》副刊上發表了我的小說處女作《回鄉》。編輯很精心,還給配了一幅插圖。同年10月,我又在朝陽區文化館主辦的《芳草地》小報上發表了散文《農場漫步》,由此開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當時,我正在北京雙橋中學畜牧職業高中讀高一。我調到鄉政府時,已經在大大小小的報紙刊物上發表了幾十篇作品,儼然成了農場里的名人。
我沒想到鄉政府的條件很艱苦。辦公室三人一間,我和黨委副書記、辦公室主任一起辦公;晚上值班就住在辦公室,而且要從家帶被褥;午飯永遠是白菜豆腐米飯。更貧窮的是整個鄉政府里連一臺打字機都沒有。黨委讓我編寫簡報,給我的工具就是一支鐵筆、一塊鋼板、一卷蠟紙。就是說,我要學會在蠟紙上刻字,這使我想到古人在竹簡上寫字,想到紅巖烈士辦《挺進報》。說實話,我的字寫得不好,字寫得不好,刻出的字寫得就更不好。即使這樣,黨委領導也沒埋怨我,仍然將印得歪七扭八的簡報發到各單位。多年以后,當鄉政府有了打印機,有了電腦、復印機后,我是多么地羨慕他們啊!十年前,我回父母家,看到家里有一張鄉政府辦的報紙,編輯、版式、印刷很正規,心里有說不出的為現在年輕的一代而欣喜。
機關工作不像工廠車間工作,沒有什么硬性指標,工作完全靠自覺。自1985年農村土地重新分給個人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明顯增強,除了種好自家的田地,更多的年輕人選擇到鄉鎮企業和城市里打工。既然一切向錢看,一切為了生存和發展,誰還在乎共青團工作呢?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開團委會,全鄉26個團支部,只來了兩個團支部書記,還有一個,竟然遲到了兩個小時。我不知道是因為忙,還是前任做了手腳。我并沒有把這個情況向鄉黨委領導匯報,我只想通過我的行動去找到答案。我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分別到單位和家里去找團支部書記談心,有的一連去了三次,也有的邊幫他們家里干農活邊聊工作。這樣,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再開團委會時,26個團支部至少能來20個人了。一年后,我們組織了新團員入團儀式。當國歌奏響的時候,我的兩眼滿含熱淚,黨委書記在講話中一連說了幾個“不容易”。我想,我的淚水不只是因為勞動的艱辛,更多的是對信仰的忠誠。endprint
1987年市場出現疲軟,三角債危機幾乎侵蝕到每個單位。為了增加地區的社會知名度,鄉黨委領導讓我把工作重心轉向對外宣傳上下功夫。說得直白點,就是想辦法給新聞單位、上級宣傳部門投稿,發現典型,報道好人好事。當時《北京日報》、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通訊員名額只給了農場宣傳部孫雨山。朝陽區的通訊員一個是區委宣傳部的郭學棣,另一個是區廣播站的張禮。而要往市里的新聞單位發稿,非得找他們三人不可。
為了發稿,就得和農場、區里、市里的相關人員搞關系。記得我曾經把《北京日報·郊區版》的一個記者專門用121汽車接到鄉政府,請我們鄉黨委書記和他聊了兩個多小時。鄉政府很窮,食堂只做了麻婆豆腐、肉絲炒芹菜、油炸花生米和切了一根蒜腸,二鍋頭酒還是我從合作社商店買的。那個記者回去一個多月,一個字也沒有寫,或許是嫌我們接待得太寒酸了吧。
由于我父親在鄉政府下面一個村里擔任著黨支部書記,鄉政府機關的干部年齡稍大我一些的常以長輩自居。至于各個村上的書記、社長和村委會主任,就不把我當成機關干部了。這樣的狀態有利有弊,好處是人熟,沒有不認識的,到哪里都可以喝水吃飯。不好的一面也是因為人熟,人熟就可以不講理。譬如我到村里收青年活動經費,跟我父親關系好的村領導,剛一張嘴,就表示愿意出。也有的則以各種理由給搪塞了,讓我急不得惱不得,氣不得說不得。
對于宣傳工作,人們的態度也不一樣。就大多數人而言,誰都想出名。尤其到了年底評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時,填寫申報材料都很積極。這時,我的作用就大了,哪個領導見我都笑逐顏開,仿佛他們的榮譽就在我的筆下了。其實,只要按照上級黨委給的指標填上了,百分之百都可獲得。那個年代還沒有公示這一說,報上誰就評上誰。有一個村干部,她是副書記,但每次評先進時都是她。時間長了,正職的書記好像發現了什么,聞出了味道,在某年評先進時,突然找到鄉黨委辦公室,說以往評先進他不怎么關心,結果次次都讓副書記當選或讓副書記替他去領,結果人們以為這個村實際是副書記掌權呢。他這次來的目的,就是要告訴我們,以后再有評先進的事,直接告訴他,不必通知副書記。一年后,副書記調到鄉政府當婦聯干部,想來正副書記已經不和了。
在基層干部中,班子不和是非常令人頭疼的事。不和的原因有多種,既有宗族的,也有利益的,還有男女的,還有權利的,甚至是階級的。我父親在最后搭班子時,選了一個本姓的晚輩做社長,幾乎讓他遺憾終生。我管社長叫二哥,比我父親小個四五歲,早些年在村里種地,改革開放初期,在村里辦了個電鍍廠,后來又承包了螺釘廠。父親之所以選他當社長,主要考慮當時他與村里的承包費、建筑費有許多說不清的問題,村民反映比較大,經過與鄉政府黨委書記磋商,讓二哥當社長,過去他與村上的賬務一筆勾銷,即誰也不欠誰的。由鄉政府財務部門做結論。按說這個事情就這樣糊里糊涂過去了。可幾年后,鄉黨委書記退休,新上來的書記喜歡和二哥等人出入歌廳,一來二去就成了哥們兒。有一天,二哥拿一張六千多元的餐飲發票讓我父親簽字,說前幾天和鄉政府幾個領導吃飯來的。我父親看著發票上的數字有些吃驚,說咱農民干一年活才掙四千塊錢,你們幾個人一頓就吃掉六千多,這也太過分了吧?這字我不能簽。對于父親的話,二哥當然不能接受,他和父親為此吵了起來。意思是,別的村都這樣,有的村一次花一萬多呢。這事情過去時間不長,鄉里年輕的黨委書記便把父親找去談話,核心意思是說我父親年齡大了,思想觀念跟不上形勢,經黨委研究讓他退居二線,享受正職待遇,等到了六十歲,正式辦理退休手續。這個黨委書記,原來在農場的牛場任場長,他在1990年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范,還是我給他寫的材料。現在,他已經變了,我能說些什么呢?
二哥和我父親的恩怨始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候,父親和村里的幾個年輕人政治思想比較活躍。村里二哥的父親和他的叔叔都是地主成分。另外有李氏哥倆,家里解放前在上海開辦了兄弟牌縫紉機,被打成資本家,下放回村。再有幾個歲數大些的農民,解放前夕秘密突擊加入了國民黨,后被查處,定為壞分子。這些人加起來有七八個,在那時顯然是被批斗的對象。聽我父親說,那時候他們確實對這些人進行過批斗。我問過父親,你打過人沒有。父親對天發誓,他從來沒有打過人。不過,他喊口號還是蠻用力的。于是,我對父親說,這仇恐怕要結一輩子了。
二哥當了社長后,開始還信誓旦旦在我面前說,我一定要感謝你父親的提拔之恩。但幾年后,他的復仇心理就開始作怪了。對于在那時候批斗過他父親、叔叔的村民,包括他們的家屬,他都想辦法報復。由于鄉黨委書記成了他的哥們,他就讓會計三番五次地找我父親說要重新查賬,聲言村里欠他多少多少錢。我父親說,關于過去的事情,黨委已經做了結論,是不能更改的。如果非要更改,那要由鄉黨委派人復查。為此,二哥對父親耿耿于懷。有次借著酒勁,還和父親動了手。我很心疼父親,可又不知道這事情怎么去解決,見父親不肯屈就,二哥又找來鄉里村里有一定威望的人做父親的工作,要求一是答應給他返回五萬塊錢,二是推薦他入黨。父親找我商量,我說最好的辦法就是拖。如此,堅持了兩年,最后,鄉里的一個主要領導親自出面,父親才拗不過讓二哥入了黨。父親在被免職退居二線后,二哥并沒有按照鄉里的規定,在經濟上對父親給予正職待遇。父親找過鄉里幾次,鄉里的領導左拖右拖也就不了了之。多年后,村里一位在鄉政府當過主要領導的表哥跟父親聊天時還埋怨父親當初不該讓二哥入黨。父親說,你現在說有什么用,當初你們不是都主張讓他入黨嗎?表哥說,他當時雖然那么說,也是權宜之計,父親如果硬是不發展,誰也沒有辦法。表哥的話我不大相信,以父親的仁厚性格,他根本就做不到。
像我父親跟二哥的這種關系,在農村并不鮮見。記得一年,我陪區廣播站的張禮去一個村采訪。村黨支部書記是個六十多歲的大爺,社長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小伙子,按村里的輩分他們屬叔侄關系。本來,小伙子是老書記的培養對象,先當團支部書記、民兵連長,再當社長,如果不出意外,下一步肯定當黨支部書記。誰料,我和張禮采訪后,張禮回去以我們兩個人署名,寫了一篇《小村里有個種田迷》,主要介紹年輕的社長怎樣靠科學種田的。文章在《北京日報》二版發表后,在當地引起較大反響,正當我春風得意之時,想不到村里的老書記拿著報紙找上門來,質問我為什么只寫了社長,而沒寫他。我說,新聞通訊稿不比總結,要講穿靴戴帽,報紙喜歡直來直去。老書記一聽,義正詞嚴地說,請問還要不要黨的領導?如果沒有黨的領導,他怎么科學種田?我見老書記真生氣了,就給他沏茶,讓他坐在椅子上消氣。我勸他,年輕的社長不管把莊稼種成什么樣,也是您領導得好。再者說,看著年輕人進步,您老不也看著高興不是?我的話似乎起了一點作用,老書記喝了一碗茶后,還是有些悻悻地走了。我沒有想到,就是因為我的這一篇文章,使這對叔侄接了疙瘩,不但年輕的社長沒有順利接班,據說直到老書記去世,他都不肯原諒年輕的社長。這是我的悲哀,還是老書記的悲哀?或許都不是,這應該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哀。
責任編輯 謝 蓉
特邀編輯 張 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