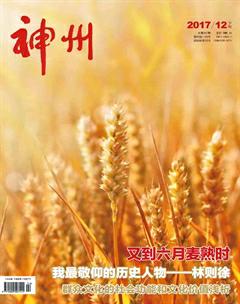又到六月麥熟時

小時候在農村,每一年的麥收季節,我的手總會干燥脫皮,直至現在仍是如此。所以現在每當手開始脫皮的時候,就知道又一年的麥收季節到了。
現如今農村的麥收已經不再是一個多么值得重視的時節了,無非是提前打幾個電話,詢幾個價格,預定好某一天的收割機,到了那天早早的等在地頭上,收割機一到,即便面積再大的麥田,個把小時都能收割完畢,裝袋入倉。但是,在我還是小學生的那個年代,每一年的麥收季節幾乎都要持續上半個月,那段時間里的每一天,全家人都要去麥田里勞作,才能把成熟的麥子收完入倉,所以麥收季節幾乎是華北平原上半年中最忙碌的一個時節。
如果拆分的話,麥收的過程可以分為收割、晾曬、脫粒、再晾曬和入倉這幾個環節。當然最開始的一定會是收割。麥子成熟之后,麥穗逐漸由青色變為金黃,待到麥田足夠成熟之后,選一個天公作美的日子,全家人一起割麥,每個人分管幾個地畦。我現在還清晰的記得用麥稈打結的手法,割下來的麥子需要先打成捆,然后碼放到一起,等待全部收割完畢之后用牛車拉到麥場。這其中收割是個重體力活,雖然我小時候身體單薄,但由于家里男丁缺乏,從小我都跟著大人一起收麥,父親會給我留一些偏小的畦,只是我打的結總是不如大人打的漂亮又整齊。
對割麥印象深刻的另一個原因來自于這一天的午飯,是的,小的時候對吃的印象總是更深。收麥的時間取決于麥田的大小,但即便只有兩三畝,半天也不可能完成,于是母親總會在幾天前就為今天的男丁們準備好充足的干糧,往往是白面烙餅外加腌好的咸雞蛋,還有清涼解暑的綠豆湯。這頓飯常常是坐在麥垛上吃,再加上平時母親舍不得給我們吃的白面烙餅和咸雞蛋今天敞開了吃,所以心中對這一場景的印象記憶深刻,尤其是大餅卷咸雞蛋的味道。
割麥只是完成了把麥子集中到一起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切割,晾曬和脫粒。那個時候我還小,這種技術活我幫不上什么忙,只能是在一邊打打下手,起到傳遞和搬運的作用。這幾天是非常忌諱下雨的,但是每年的這個時節華北平原正是多雨季節,于是記憶中有很多次的麥收季節,都是冒著雨在麥場里蓋塑料布,雨后又狼狽晾曬的情景。
麥子晾曬干燥后有一個重要的步驟叫脫粒。在更早的時候,農民一般都是用牛拖著石磙子在麥場轉圈碾壓,促使干燥的麥粒從麥芒中脫出,后來我大了一些,牛被拖拉機替代,這個時候我常常有機會成為替補拖拉機手開著拖拉機在麥場轉圈。雖然只是在半個足球場那么大的麥場上轉圈,也不能駛向別處,這畢竟是我唯一摸到拖拉機的機會,于是一邊模仿者大人們掛檔松離合踩油門的手法,一邊暗爽,這對于一個還沒上中學的農村娃來說,已是天大的樂趣。
脫粒完成之后的麥子和麥芒混在一起,還必須要完成最后一步:分離,我們叫揚場。揚場更是技術活:首先要找風和日麗的日子,往往是在傍晚,不至于太曬,也必須要有一些風,因為風會促使輕飄飄的麥芒和麥粒分離。揚場往往都是鄰居家的大爺來幫忙做,因為這個過程純靠手法,技術不夠扎實的小伙揚出來的麥粒和麥芒根本無法分離干凈。鄰家大爺頭系白手巾,嘴里叼著煙袋,有節奏的一把一把的揚著,我則坐在旁邊暗自羨慕:什么時候我才能揚的這么好?
揚場之后,麥粒和麥芒徹底分離,再經過晾曬、裝袋和運輸,今年的麥子就算完成了麥收,入了糧倉。雖然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傳統手工收麥的方式效率低,效果差,機械化時代機器收麥高質高效,但這不正是時代和科技發展的必經之路嗎?只是一些技術和手法再也找不到用武之地,留給我們的只剩下記憶中的那一片金燦燦的麥田,和那一段累并快樂著的時光!
作者簡介:張偉周(1977.04—),男,漢族,河北省滄州市人,本科學歷,自由職業者,汽車自媒體作者,研究方向:網絡文學寫作。endprint